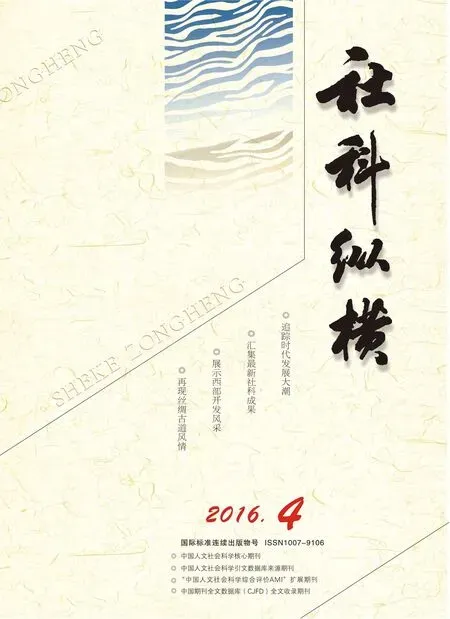社會團體對公共決策的影響
——以“階段性就業”決策歷程中婦聯的作用為例
孫魯毅
·社會學研究·
社會團體對公共決策的影響
——以“階段性就業”決策歷程中婦聯的作用為例
孫魯毅
(廣西民族大學廣西南寧530006)
公共決策是公共管理部門依照法定權限和程序對社會公共事務做出的決定,是公共管理的主要手段和關鍵。隨著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法制化的發展,以社會團體代表的公眾組織在公共決策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在“階段性就業”制度的決策過程中,全國婦聯組織,脫離了體制的束縛,以維護婦女權益為己任,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本文擬通過分析“階段性就業”決策歷程中婦聯的作用,來看社會團體對公共決策影響。
社會團體公共決策婦聯階段性就業
引言
性別平等是一個衡量社會文明和現代化的標準之一,是世界追求的目標。[1]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一直把婦女解放、促進男女平等、維護婦女權益作為一項重要發展任務,并于2012年11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將“男女平等”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改革之初,為推動婦女解放,提高婦女家庭、社會地位,國家大力提倡并鼓勵城鎮婦女走出家門,參加社會工作,促進男女平等。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婦女走向社會參加工作,分擔家庭經濟負擔。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造成大面積工人失業。為緩解就業壓力,社會開展了一系列關于“婦女回家”問題的大討論。隨后,席卷西方發達國家的“階段性就業政策”引起了中國學者、社會和政府相關部門的關注。2000年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決議》明確提出要“建立階段性就業制度”;2001年3月7日,全國政協委員王賢才在九屆四次人大會議上再次提出“婦女回家”的倡議,并提交相關提案。由此,“階段性就業”制度進入政府決策的議程。全國婦聯組織不顧一切阻撓,通過各種方式據理力爭,維護婦女平等和自由就業的權益,最終促成“階段性就業”制度沒有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規劃綱要》的提議。全國婦聯組織在這次的政策決議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一、核心概念界定及相關概述
(一)階段性就業及相關概念界定
按照《“十五”計劃綱要中有關勞動工資的名詞解釋》(中國勞動保障報3月9日版)的界定,“階段性就業”是指勞動者在其職業生涯中,因生育、撫養子女、照顧親屬、放學或參加其它沒有報酬的活動而自愿退出勞動力市場一段較長時間,之后再次就業的一種就業形式。
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數據信息中心主任蔣永萍認為“階段性就業”政策就是專為女性制定的。盡管依據解釋,階段性就業對象包含三種人:一是生育期婦女,二是工作一段時間后又去學習充電、接受培訓的人員,三是因家庭老人、小孩需要照顧而從工作崗位退下來的人員。[2]但綜合來分析,第一類人必定是女性,因為生育專指女性,而實施階段性就業政策后,凡是要生育的女性都將經歷停業階段;第二類人們可以自主選擇;第三類從社會環境分析,其主體也是婦女,但比率較小,因此階段性就業主要針對的是女性,對女性影響最大。也有學者將“婦女階段性就業”稱“M型就業”,它也被視為“婦女回家”論的派生物,指職業婦女婚后或者生育后自動退職回家,從事家務勞動和撫育子女,待孩子長大后再重新就業的模式。[3]
(二)社會團體與婦聯組織
社會團體是指為一定目的而由一定數量的社會成員(包括自然人,法人)所組成的并取得法人資格的社會組織,包括人民群眾團體,社會公益團體和學術研究團體。目前,中國的社會團體大多帶有官方的性質,享受行政或事業編制,行使一部分政府職能,由財政撥款。但也是社會群眾團體的一個分支,代表特定群體的公共利益,如全國作協、文聯、學聯等。
婦聯,全稱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成立于1949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各族女職工、女農民、女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婦女、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婦女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婦女的群眾組織。全國婦聯的基本職能是代表和維護婦女利益,促進男女平等。
(三)社會團體對公共決策的影響
公共決策即公共管理部門依照法律的規定,按照一定的程序對社會公共事務進行決策的一種公共管理行為。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提高公共決策的質量,是現代公共管理對決策部門的共同目標,也是政府治理的核心競爭力。社會團體是特定利益群體的代表,維護利益群體的權益既職責所在,也是團體的利益訴求。
1.社會團體影響公共決策的方式
由于公共決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因此社會團體影響公共決策的方式很多。首先,社會團體可以就某個政策問題向政府陳述意見,提出建議或提案;或者通過社會輿論表達本團體對某個問題的觀點和意見,說服政府;然后,社會團體可以對社會規范價值重新加以界定,利用現有法規、制度規定表明自己的立場。其次,社會團體還可以,在緊急的情況下,向政府施加壓力。不同的政策場合和形式,社會團體影響公共決策的方式會有不同。但主要還是表現為游說、宣傳、抗議、社會動員等。
2.社會團體公共決策的影響
社會團體是政府政策制定中的活動者之一,通過利用自身的資源優勢、權力地位、群眾基礎參與或影響公共決策,表達團體的利益訴求,維護群體的公共利益。但是不同社會團體對公共決策的影響力是有差異的,這取決于團體自身所處的地位、成員多少、聲望大小、財力厚薄、組織強弱、領導力高低、內部凝聚力狀況和運用策略的方式等。[4]社會團體在公共決策中的廣泛參與,對于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保證社會公平正義和促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法制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階段性就業”決策歷程
(一)決策經過
2000年10月12日,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中提出要“建立階段就業制度,發展彈性就業形式”的提法,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2000年12月9日,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中國21世紀人口與發展》白皮書,提出建立階段就業制度,推行靈活的就業形勢。[5]
2001年3月,朱镕基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有關就業的提法是“發展靈活多樣的就業形勢”,沒有“階段性就業制度”。
2001年3月7日,全國政協委員王賢才仍提出“婦女回家”的倡議,并提交提案,再次引發了理論界和婦女界關與婦女就業問題的大討論。
關于“階段性就業”決策最終以九屆四次全國人大正式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沒有采納政策提議結束。
(二)決策淵源
針對婦女就業、婦女回家問題,中國現代歷史上共有4次較大的爭論。
早在20世紀30年代,當時我國正面臨著嚴重的民族危機,有不少婦女也參與到了抗日救亡運動中,女性在戰場、社會、家庭中發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女性的地位迅速提升。但隨后,受國際和國內影響,社會上掀起了關于一陣關于“婦女回家”的爭論。此階段爭論對象以社會學家、文學家、女權運動的倡導者為主,主要論述女性是該回家做賢妻良母還是外出就業。
到了20世紀40年代,發生了第二次“婦女回家”爭論。這一時期,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統區限用、禁用女工的現象愈演愈烈,女性就業不平等問題越來越嚴峻。1940年7月6日,端木露西發表文章《蔚藍中一點黯澹》,再次點燃了關于“婦女回家”的論戰。同年8月12日,中共南方局婦委負責人鄧穎超,在《新華日報》副刊《婦女之路》發表《關于<蔚藍中一點黯澹>的批評》。[6]1941年4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制訂“要婦女多生孩子、少參加政治活動”的婦女運動方針,實際上是肯定了“婦女回家”論。1942年11月20日,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在《解放日報》上發表《論“賢妻良母”與“母職”》一文,站在婦女解放的立場上,既肯定了要女性扮演賢妻良母角色,更加贊揚了婦女走出家門,參與社會工作的行為。[7]
第三次關于“婦女階段性就業”的爭論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1979年,歷年積累下來的就業問題大爆發,城鎮青年大量失業,婦女就業難問題尤為顯著。[8]在這一背景下,國內產生了三次關于“婦女回家”和“階段性就業”的爭論。
在1980年—1985年間,經濟體制轉型,城鎮包分配的就業模式被打破,城鎮女職工大量失業。1983年,《上海經濟》雜志上,關于“婦女退居家庭”的觀點,引起社會關于婦女“回家”與反“回家”的爭論。爭論以反回家的觀點占據優勢。與此同時,有人提出“婦女階段就業”模式。這一階段的爭論最終以胡耀邦同志批示“婦女回家是以消極的方式看待就業問題,是對社會失去信心的表現”[8]而告終。
在1986年—1989年間,我國經濟體制轉型逐步深入,下崗女職工也越來越多。《中國婦女》1988年第1期以《我的出路在哪里?》和《大邱莊“婦女回家”的思索》為發端,展開了有關于婦女就業思索的大討論。這一次的討論基于解決婦女就業問題的目的出發,引起了政府和社會對女性就業、解放模式的探索與反思。
三、婦聯組織的決策參與
我國婦聯組織成立于1949年,其以正式組織的形式參與“婦女階段性就業”的討論和影響“階段性就業”制度決策始于20世紀80年代。
當時,勞工部受社會就業壓力和“婦女回家”言論壓力的影響,決定將婦女回家緩解就業壓力以政策建議的形式寫入向黨中央情勢的報告時,婦聯于1980年8月3日致函中央書記處表明婦聯不贊成“婦女回家”觀點的基本立場;[8]1980年8 月7日,得知中央書記處未采納婦聯意見,擬召開決策討論會議時,婦聯副主席羅瓊在未被邀請時要求并參加了此次會議,參與討論;1989年3月21日,全國政協委員、婦聯書記關濤在全國政協二次會議上呼吁制定《婦女勞動就業法》和《女職工生育金社會統籌法》。
2000年12月24日,全國婦聯針對“十一五計劃建議”,召開“階段就業與婦女就業”座談會;2001年1月15日,《中國婦女報》推出“階段就業是否傷害婦女”的系列討論;2001年2月9日,全國婦聯向中央書記處、國務院遞交了“關于建立階段就業制度的社會反映及我們的建議”的調研報告。
四、婦聯組織在“階段性就業”決策中的作用
婦聯組織,作為8個參加全國政協會議、享受國家財政補貼、行使政府行政權力的社會團體之一,在對待關于婦女權益保護決策時,能夠放下自身的體制束縛,利用資源優勢多通過各種方式為維護婦女群體利益作斗爭,發揮了社會團體在公共決策中的作用。
(一)與主管部門進行高層對話和溝通
面對20世紀80年代社會普遍的就業壓力,勞動部贊同社會上一部分人的主張,希望通過“階段性就業”的方式,緩解就業壓力,并將其作為政策建議寫入向黨中央請示的報告中。1980年8月3日,婦聯為保護婦女平等就業權益,致函給中共中央書記處表明婦聯不贊成“婦女回家”的觀點和立場。隨后,全國婦聯主席、書記處書記羅瓊請示參加勞動部會議得到批準,并闡述婦聯關于“婦女回家”的意見,書記最終同意了婦聯的意見。
2000年,十五要“建立階段就業制度,發展彈性就業形式”的提法,全國婦聯就針對這項規定是否針對女性,會不會導致女性回家等問題約請國家計委的有關領導進行座談,召開“階段就業與婦女就業”座談會,并交換意見,力圖勸說勞動和社會保障不放棄這一項政策倡議。既讓公眾明白了“階段性就業”的實質就是婦女回家,又表明了婦聯組織的態度,促進了廣大婦女的覺醒和維護了婦女的正當權益。
(二)通過人大、政協表明婦聯觀點,施加壓力
作為8個具有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權力的社會團體之一,婦聯組織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權力優勢,在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上表明態度和立場,并通過提案、議案的方式對政府施加影響。2001年3 月4日,在全國政協九屆四次會議上,全國婦聯副主席劉海榮呼吁在國家宏觀政策和整體規劃中體現性別意識,落實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2001年3 月8日,原全國婦聯副主席提出將方案中的“階段性就業制度”改為“階段性就業方式”,保障婦女就業自由的權利;在此期間,全國婦聯常委康泠利用發言的機會,對“階段就業”制度進行詳細分析,得出我國不適宜推行階段性就業制度的方案;3月9日,劉海榮繼續代表婦聯發言,提出要推動婦女兒童事業發展,保障婦女兒童權益。一系列在人大和政協上的發言和表態,進一步強化了婦聯組織對于撤銷“建立階段性就業制度”的決策影響力,給決策部門施加了壓力。
(三)廣泛的社會動員,擴大影響力
20世紀80年代中期,針對就業形勢和女性就業問題,各地涌起了關于“婦女回家”的爭論,引起了相關試點城市的興趣,婦聯發動各級地方組織及試點的相關企業和工人集體反對;在“十五”規劃提出要把“建立階段就業制度,發展彈性就業形式”納入國家制度體系內,全國婦聯廣泛動員婦女階層,反對變相的“婦女階段就業制度”,引發決策層的高度關注,擴大了婦聯代表的女性群體的社會影響力。
(四)調動大眾傳媒的力量,引導公眾輿論
首先,全國婦聯通過《中國婦女》、《中國婦女報》、《婦女研究論叢》等報刊向社會建立反對“婦女階段就業制度”的宣傳,營造輿論氛圍;然后,婦聯又通過組織“女性話題論壇”、開展“階段性就業是否傷害女性”等的系列討論,引起更多輿論的關注;緊接著,全國婦聯副主席顧秀蓮在3月8日又做客新華網,就婦女問題與網友進行討論,支出階段性就業存在的問題,特別是對女性權益的危害。一系列的媒體報道、公眾互動和輿論宣傳將關心婦女權益保護的公眾連接在一起,引導公眾團結一致,最終影響中央政府關于推行“階段性就業”的最終決策。
(五)向黨中央和國務院遞交報告
1988年9月,針對國內“婦女階段就業”的爭論,全國婦聯六大報告提出探索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婦女就業制度,引發政府的關注。20世紀90年代中期,為應對“婦女階段就業制度”進一步進入政策議程,在1996年11月,于廣州等6個城市進行婦女就業意愿調查,1997年3月上交提案,勞動部承諾“三年內不出臺婦女階段就業”的有關政策。[5]“階段性就業”在“十五”規劃中被提到后,2001年2月9日,全國婦聯再次向黨中央和國務院遞交“關于對‘建立階段就業制度的社會反映及我們的建議’”的主報告;2月10日,胡錦濤書記作出批示,贊成婦聯維護婦女權益的舉動。
五、婦聯組織參與“階段性就業”決策的意義
(一)推動了男女平等的發展進程
從“婦女回家”到“婦女階段性就業”,再到“階段性就業”提案的流產,中國婦女運動經歷了一個從興起、逐漸高漲至高潮到緩和,慢慢恢復平靜的過程,與男女平等的目標越來越接近。“婦女回家論”是女性處于絕對弱勢地位時被剝削、束縛的代表思想;而“婦女階段性就業”則是在國家強制力維護下的女性處于平等處境中不被接受的形式平等的體現;“階段性就業”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使用女性一詞,但實則是針對女性并以保護女性為借口的一種侵犯女性自由意志的方式。每一次論題的辯駁及其終結,都提升了社會對于男女平等的重新認識,促進了女性的覺醒和思想的解放。“階段性就業”提案的流產標志了女權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女性平等要的不僅僅是機會平等,更是實質平等。絕對的真正的男女平等不是像對待男性一樣對待女性,還要考慮女性的生理差異及其對家庭的貢獻,這才是當今社會男女平等發展的新主題——如何更好地保護女性,承認和分擔女性的家庭責任。
(二)引起人們對女性健康保護的重視
“階段性就業”的支持者認為現有的就業體制是在把女性當男性使用,如“鐵姑娘”、“女強人”、“女漢子”等等,沒有考慮到男女的生理差異和女性家庭、社會責任雙肩挑的辛苦,女性健康既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又不受重視,這對女性健康是一個很大的威脅。“階段性就業”提案的流產表明女性依靠回家來維持身體健康并沒有得到大家的認可,但是它給當代社會提出了一個警鐘:女性的健康的確處于受威脅的境地,需要加強措施予以保護。
(三)增強人們對家庭勞動的認識,提高女性社會地位
一直以來,在中國都有“女主內,男主外”的角色傳統,女性參與社會工作不僅只是在她們家庭主婦的身份外圍加上了另一個光鮮稱號“職業女性”,更增加了她們的勞動負擔。女性的家庭地位依靠在外工作的經濟收入得到提高,但家庭勞動的價值一直被忽視,甚至被很多人視為理所當然,女性一旦脫離勞動崗位,還要再次面臨收不平等待遇、被男性掌控的局面,這也正是女性反對“階段性就業”的主要原因。繼“階段性就業”制度被終結以后,相繼有不少學者提出要承認女性家庭勞動價值的研究。①家庭勞動的價值得到認可,能夠確保女性家庭和社會地位的穩固性。
(四)促進決策者對婦女權益保護的認識
“階段性就業”政策從提出到終結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博弈過程,這不僅給了全社會一個啟示:男女平等不僅是女性追求的目標,更是社會的一個價值保準,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也不應該侵犯這一基本的界限,也讓政策決策者更清醒的認識到保護婦女權益的重要性。在中國歷史上,女性一直處于弱勢地位,促進決策者對男女平等的重視不僅是中國女權運動的一個成果,也是一個國家平等、和諧發展環境建立的基礎。
(五)提高了婦聯組織等社會團體的決策影響力
在中國,婦聯是為爭取婦女解放而聯合起來的各族婦女的群眾組織,其基本功能是代表、捍衛婦女權益、促進男女平等,亦同時維護少年兒童權益,以及在全國女性中組織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政府、政策的支持。從“婦女回家”到“階段性就業”制度終結,婦聯組織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階段性就業”被提出以后,婦聯及其成員先后通過個人聯系接近政治上層人物、組織調研、公共輿論、大眾傳媒等形式論證“階段性就業”制度的危害并反對其出臺,直至“階段性就業”制度被終結。經過“階段性就業”的決策歷程,婦聯組織在公共決策,特別是關乎婦女權益保護方面,有了更大的影響力。
六、結語
盡管此次關于“階段性就業”制度的決策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婦女就業和權益保護問題,但在一定程度上打壓了倡導“婦女回家”的言論,維護了婦女平等、自由就業的權益,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婦女權益保障的發展進程,促進了全社會對婦女不平等的覺醒,提升了婦聯組織的決策影響力。“階段性就業”政策被提出,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反映了當今婦女的社會地位、發展處境仍存在問題,男女平等的美好設想仍有待社會共同的努力。而它最終沒有通過政策議程的評議以制度的形式出現在公共政策當中,也說明它并不是解決婦女就業問題的有效途徑。男女平等并不僅僅是就業機會的平等,讓女性異化成和男性一樣的人,更不能簡單地以改善婦女身體健康、減輕婦女工作負擔而讓婦女回家,靠男性養家。深植于社會中的“男尊女卑”思想沒有完全消除,解決女性就業歧視的相關法規不健全,保障婦女生育、撫育、健康、養老等保險制度的不完善,女性家務勞動價值的忽略,這一切女性遭遇的不平等問題得不到解決,“男女平等”就無法真正達到。
從這次決策歷程可以看出,隨著民主化、法制化的推進,社會團體在公共決策中的作用、影響越來越大。但不可忽視的是,中國不少社會團體由于隸屬于政府,受體制的束縛,以及自身的權力地位、經濟實力等的限制,發揮的決策影響力有限,導致公共決策受大型利益集團的控制的困境。因此,發揮社會團體在公共決策中的作用,還需要制度的保障,為所有社會團體參與公共決策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中國公共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法制化道路任重而道遠。
注釋:
①如中國地質大學2006年碩士論文.嚴淑敏《女性家務勞動價值的法律保護》;新浪安徽網有關“女性觀點:家庭勞動應該價值化”的報道;2012年3月8日“三八婦女提案:承擔不起的家務勞動”等。
[1]崔紅梅,張蓉,田豐.對婦女階段性就業制度的思考——北京市和臺灣地區婦女在就業人口特點比較[J].中國農業大學(社會科學版),2004(1).
[2]21世紀職場,“階段性就業”是否專指女性?[EB].http: //edu.sina.com.cn2001/01/12-10:00:精品購物指南.
[3]韓廉.社會轉型期全民自覺維護政策公正的范例——世紀之交的“婦女回家”、“階段就業”論爭與“十五”就業政等[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版,2008(6).
[4]陳振明.政策科學——公共政策分析導論(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94.
[5]徐家良.利益表達:社會團體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J].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4(1).
[6]鄧穎超.關于《蔚藍中一點黯澹》的批評[A].蔡暢,鄧穎超,康克清.婦女解放問題文選[C].北京:人民出社,1988.
[7]周恩來.論“賢妻良母”與母職[N].解放日報,1942-11-20.
[8]歐陽和霞.回顧中國現代歷史上“婦女回家”的四次爭論[J].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03(6).
C934
A
1007-9106(2016)04-0048-05
孫魯毅(1978—),男,廣西民族大學助理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民族地區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