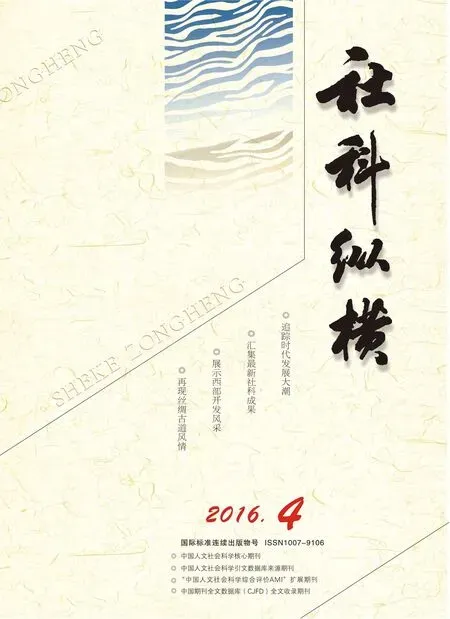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天堂
——論虛構世界的大小
周志高
(九江學院外國語學院 江西 九江 332005;江西師范大學敘事學研究中心 江西 南昌 330027)
·文學研究·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論虛構世界的大小
周志高
(九江學院外國語學院江西九江332005;江西師范大學敘事學研究中心江西南昌330027)
文本是虛構世界的物質載體,是實在有形的,能夠看得見、摸得著的。但是,文本中的虛構世界卻并非如文本本身一樣真實地存在,它是主觀抽象的,是話語的表征和想象力的產物。讀者只有在閱讀文本之后才能感覺到虛構世界的存在,而虛構世界是模糊的、無形的,讀者只有根據邏輯規律和可能世界的標準,依靠想象、推理來判斷虛構世界的大小。虛構世界的大小與文本篇幅有一定的關系,但是文本篇幅并非判斷虛構世界大小的金科玉律,更多的是要依靠文本信息“讀出”虛構世界的大小。虛構世界可以分為同質世界與異質世界兩種,對于同質的虛構世界而言,由于依據的參照系統是相對固定的,判斷其中的虛構世界的大小比判斷異質的虛構世界的大小要簡單些。由于敘述中的虛構世界的有限性,讀者“讀出”的世界往往比文本呈現的世界要大。
虛構世界大小同質異質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掌中有無限,須臾見永恒。”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威廉·布萊克的長詩《天真的預言》中的第一個詩節。這位遠在萬里之遙的英倫島國詩人如同一位道行高深的佛家大師一樣給我們透露了世界的“小”和“大”、“短暫”和“永恒”之間的玄機,顛覆了我們日常對事物、世界大小的看法。佛家認為沙粒微塵雖小,卻可從中見出三千大世界,現代科學將這種觀點稱為宇宙全息論;佛家認為每個人可以修出百千萬個化身,現代科學技術已經可以用人的DNA克隆出百千萬個自我,為這一佛理做出了現代闡釋與證明;最有趣的是科學對物體的最基本組成物質的認識,曾經認為它是分子,而隨著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后來又認為是原子,再后來又認為是夸克等等,這就說明對于世界的認識,即使現代最先進、尖端的科學也是難以窮盡和徹底的,而佛家早在兩千多年前,乃至更早的無量光年前就認為“萬物無自性、無本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出自《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說明了世界存在的根本。佛教和現代科學殊路而同向,向我們揭示現實世界的本相。一顆沙粒微塵居然可以見出三千大世界,而對現實世界的認識,向內而言不斷地細化、微化,由原子變為、質子、中子、夸克,向外而言不斷地擴大、蔓延,由地球擴展到太陽系、銀河系乃至無邊無垠、仍然不斷擴大的宇宙。“小中見大、大亦可小”,現實世界的大小、規模尚且如此難以確定,何況虛構世界呢?
既然稱為虛構世界,世界就有大小之分。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判斷虛構世界的大小呢?虛構世界是文本指涉出來一種世界,因此,判斷虛構世界的大小可以依據文本信息和文本大小,也就是文本中描述的或容易推導出的虛構事態。虛構世界的大小與其中的人物和事件的數量以及時空幅度有密切的關系。敘述中卷入的人物、事件越多,時空幅度越大,虛構世界就顯得越大;反之,敘述中卷入的人物、事件越少,時空幅度越小,虛構世界就顯得越小。可以說,“敘述決定了虛構世界的大小”。[1](P28)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展示的世界何其的宏偉壯闊!神、人共同參與的特洛伊戰爭持續十年之久,將讀者的目光帶到了天上的神仙世界與地上血流成河的慘烈戰爭。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以萬丈雄心來展現世間生活的種種場景,描述廣闊、豐富的宇宙。莫泊桑的《羊脂球》、《項鏈》,契訶夫的《變色龍》、《套中人》,歐·亨利的《麥琪的禮物》、《警察與贊美詩》,魯迅的《故鄉》、《阿Q正傳》、《傷逝》,這些短篇小說則不僅文本篇幅短小,所涉及人物與事件通常比較少,敘述的是生活中的微小片斷,而且所展示的世界也比長篇小說中的小得多,有的僅僅是世間的一個小小的場景。所以說,文本的幅度與其所投射的虛構世界的大小具有很大的關系,這就是“長篇小說為什么‘長’?短篇小說為什么‘短’?”的主要原因吧。
虛構世界的大小由敘述決定,在文本中再現。但文本的幅度并不是決定虛構世界大小的金科玉律,虛構世界的大小還取決于讀者具有洞察力的感知,在“閱讀中的想象、推理與判斷”。讀者對文本中的虛構世界的想象、推理與判斷絕非漫無邊際的,而是根據敘述信息,“以其心目中的可能世界作為參照系統,營造虛構的世界”[1](P29)。我們不能因為文本的幅度而對虛構世界的大小產生偏見,文本的呈現受制于作者對所敘述故事的擴充或濃縮,作者可以將一個短篇小說的篇幅擴充為長篇,也可以將一個長篇小說的篇幅濃縮為短篇。虛構世界的大小關鍵在于讀者以其心中的可能世界為參照系統從文本中讀出。葉圣陶先生的童謠詩《小小的船》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句:
彎彎的月兒小小的船。
小小的船兒兩頭尖。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
只看見閃閃的星星藍藍的天。但它給我們呈現的卻是一個巨大的世界。敘述者“我”將懸掛在浩瀚夜空中的一彎明月比作一艘小船,想象自己“坐在”月亮之上,目光所及之處,盡是閃閃發亮的星星和蔚藍的天空。該詩的文本篇幅很小,它給我們呈現的卻是一個無邊的美麗夜空,激發了多少少年兒童對夜空的無限遐想。這種文本維度與虛構世界大小的對比何其強烈!同樣,美國意象派詩人艾茲拉·龐德的短詩《在一個地鐵站》造成的文本篇幅與虛構世界大小的對比也十分強烈,其中的世界更需要讀者認真領會才能讀出。麥克盧漢在論及媒介時,將媒介分為“熱媒介”和“冷媒介”,熱媒介由于提供豐富的信息,因而對讀者/觀眾的卷入程度低;而“冷媒介”由于提供的信息量少,因而對讀者/觀眾的卷入程度高,需要讀者/觀眾付出更多的思維關注。[2](P35-47)文字文本屬于冷媒介,而文本信息量少的文字文本更是“冷”之又“冷”,因而具有強力的“迷思”。該詩只有短短的兩行:
人群中這些面孔幽靈般顯現,
濕漉漉的黑色枝條上的許多花瓣。
詩的意象鮮明而意義卻十分隱晦,意象的抽象、濃縮與文本的短小增強了敘述張力,延長了讀者的審美時間,增加了理解的難度。讀者只有通過對意象的細細解讀才能判定其中虛構世界的大小。詩作的優美之處在于它的情、意交融產生的審美效果。克羅齊說過,“沒有意象的情感是盲目的情感,沒有情感的意象是空洞的意象。”[3](P35)讀者可以從該詩虛實形象的對照、互映來激發想象力,探索詩意的本質。這兩句詩看似毫無聯系,實際上是對照互映的,要通過“文本間性”才能獲得對它準確的把握。如果在第二句詩前面加上“猶如”、“好像”之類的詞語,讀者就能將第一句詩理解為本體、第二句詩理解為喻體。喻體是本體意義的修辭性表達,因此第二句詩所造成的意象就非常重要了。花瓣可以喻指一切美好的東西,從這兩句詩的文本間性我們看出此處喻指美麗容顏。中國文學中用花來喻指美人、美顏的敘述更多,諸如“人面桃花”、“閉月羞花”、“花容月貌”等等。黑色枝條喻指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的平庸凡常、粗鄙丑陋之輩。但是,該詩若僅表達對美與丑的愛憎傾向、好惡態度,則未免顯得膚淺,畢竟趨美棄丑乃人之常情。該詩持久的魅力所在是以抽象的意象符號攜帶了豐富的感知意義,召喚接收者的深度思考與理解。韶華易逝,美人遲暮,猶如美麗的面孔幽靈般顯現又消失一樣,現實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和美好感覺稍縱即逝,留給人們嗟嘆與惆悵;猶如美景只顯現給留心體察的人們一樣,現實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物需要人們用心去發現;正如花瓣長在粗鄙丑陋的枝條上一樣,現實生活中的美與丑、善與惡何嘗不是對比鮮明卻彼此依存、正畸相生呢?花瓣給人優美、典雅、芬芳、親和之感,濕漉漉的黑色枝條給人丑陋、卑賤、平淡、厭煩之感。兩種符號攜帶的各種相關感知激發了讀者對其命意的探究。這恰如現代社會給人的強烈感覺沖擊,欣喜與失落在瞬間交替。“一個地鐵站”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環境,其意象是現代社會的一個縮影,詩人龐德以高度提煉、概括的“美”、“丑”意象對照來指涉現代社會,表現他對現代社會的直覺感受。由一個地鐵站中的意象聯想到整個現代社會,考驗的是讀者對詩句的充分理解和豐富的想象力,這也是該詩難于理解的主要原因。
虛構敘述在不同程度上“錨定”現實世界,從而與現實世界保持不同的距離,建構不同的虛構世界。讀者不可能拋開文本敘述隨意去重構虛構世界。不同的敘述模式對讀者的閱讀投入和理解能力會有不同的要求,與現實世界“錨定”系數大的虛構敘述對讀者重新建構其中的虛構世界來說要容易得多,而與現實世界“錨定”系數小的虛構敘述對讀者重新建構其中的虛構世界來說就更困難些。但不論哪種敘述,都需要讀者依據特定文本的敘述信息進行能動的反應,根據敘述中提供的建構虛構世界的邏輯規律和“可能”的標準來確定虛構世界的大小。
當適用的邏輯規律與可能的標準相同時,不同的虛構世界之間的大小是可以進行比較的。當讀者讀到柳宗元的《江雪》和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時,一般會以現實世界的時—空維度作為參照系統來想象、比較這兩幅畫面。柳宗元的《江雪》是一首五言絕句: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詩的前兩句對營造其中的虛構世界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千山”、“萬徑”是一個多么廣闊的世界,延綿不斷的山脈、縱橫交錯的道路成了架構這個世界的主要元素;“鳥飛”和“人蹤”賦予了靜態畫面一種動感,更將讀者的想象投射到遠方,讀者的目光似乎跟著鳥兒的翅膀將世界的邊界投射到了天邊;“絕”和“滅”在此是指對“行動”的否定,更加突出了這個偌大的世界的空曠。后兩句的“孤舟”、“獨釣”、“蓑笠翁”以渺小的實物反襯出世界的廣闊寂寥。《清明上河圖》是一幅長卷畫作,寬25.2厘米,長525厘米,絹本設色,采用散點透視構圖法繪制。它是一幅完整的畫作,但是從整個畫面的框架來看,全圖可以“區隔”為三個部分,展開圖,首先看到的是汴京郊外的景物;中段主要描繪的是上土橋及大汴河兩岸的繁忙景象;后段則描繪了汴京市區的繁華喧鬧的街景。該圖生動地反映了中國12世紀北宋時期汴京的城市面貌和當時社會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狀況。從文本幅度來看,《清明上河圖》的文本要比《江雪》的文本大得多,不僅卷長525厘米,而且畫面的內容非常豐富,清明上河圖有城廓、河流、橋梁、船只、房屋、樹木、人物、車輛馬匹等等,坐落有致,疏密有序。但就其所投射的虛構世界的大小來看,只是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汴京城,這比《江雪》中“千山”、“萬徑”所投射的世界就要小得多。
虛構世界根據邏輯規律可以分為可能與不可能兩種世界類型,也可以根據物理規律分成單個域或多個域。馬提納茲·伯納蒂借用哈特曼劃分真實世界的層級模式將虛構世界分為物質層、有機層、思維層和精神層。這些從不同視角對世界的分類有利于深化對虛構世界的認識,但對于認識不同世界的大小規模、特別是用來指導如何比較不同世界之間的大小方面不能發揮很理想的理論效用。斯蒂芬·科爾納提出的將可能世界分為同質世界和異質世界的觀點更有指導意義。[4]同質世界共享相同的范疇結構,它們會受同樣的自然或超自然規律所制約。異質世界具有不同的范疇結構,它們由兩個明顯的分隔的區域組成:自然與超自然范圍或者世俗與神圣的空間。[5](P104-106)
同質世界可以是一個單獨的區域;也可以是兩個以上的獨立的區域,這些區域之間的關系是連續的或是離散的。在單一的同質世界或連續的同質世界里,由于“文本現實世界”[6](P24)處于同樣的時空維度,個體可以自由地穿行于其間,個體之間亦可互動交流,世界的大小規模就比較容易估算,只要依據敘述中人物的行動軌跡就能獲知世界的大致輪廓。在《德伯家的苔絲》中,讀者可以根據苔絲在文本現實世界中的“行走”軌跡,從布蕾谷到新“本家”亞雷·德伯維爾的府上、富潤谷、棱窟槐、直到陽光海濱城市沙堡讀出世界的大小規模。同質、連續的世界是現實主義小說建構虛構世界的主要方式,通過敘述的鋪展,文本現實世界的時空獲得拉伸延長,同時拉伸延長的時空可以更好地承載敘述,使敘述獲得充分展現。離散的同質世界是指世界的各個區域遵循的是相同的邏輯規律但離散的,離散就是不連續,分散、隔離的意思。文本現實世界的各個區域之間相對隔絕開來,它們通常沒有時空或因果上的聯系。對于已知的這個世界來說,被隔絕的那個世界是一個隱秘的世界,它們之間“發著亮光的那道通達之門”幾乎是關閉的,只有獨特的個體在機緣巧合之下的跨世界旅行才能到達那個隱秘的世界,使它進入到讀者的視野之中。對它的敘述可以增強故事的“敘述性”、突出故事的主題,也改變了世界的規模。《格列佛游記》中格列佛在幾次特殊的奇遇中一次次地進入另一個世界,極大地拓展了虛構世界的規模。
異質世界也分為連續的或離散的。連續的異質世界中的二元世界之間具有較強的關系鏈因,連續的異質世界由不對稱的“權力關系”和“通達關系”所支配:“自然世界處于超自然世界的監管之下,超自然世界的居民可以物質形體或特殊偽裝通達到自然世界;自然世界的人類居民相對于他們的超自然之神來說顯得軟弱無力,并且無法通達到伊甸園般的棲息地。”[7]連續的異質世界中的二元世界具有較強的聯系,通達性基本上是單向的,超自然世界與自然世界之間構成一種上下層的關系,超自然世界可以發揮對自然世界的極大影響力,超自然世界與自然世界會發生重疊現象。《荷馬史詩》中由于三位女神的爭強好勝,為了獲得“金蘋果”而導致特洛伊戰爭的十年浩劫,在戰爭中神仙的力量時常參與其中。《西游記》中神仙總會在需要的時候降臨凡間,使超自然世界獲得了如自然世界般的現實存在感,讀者不會覺得超自然世界是虛無飄渺的。世界的規模獲得放大。
離散的異質世界中的二元世界之間的關系是平行的,分散的、隔離的。它們之間因為因果關系或敘述關系而獲得某種聯系。當敘述從一個世界進入到另一個世界之后,先前所敘述的那個世界基本上就從敘述中退場,后來出場的世界成了文本中的主要敘述世界。可以說,先前敘述的那個世界是為后來出場的世界做鋪墊,說明原因,甚至起到“元故事”的作用。兩個平行世界之間似乎有一個神秘的“通道”,使“人物”得以從一個世界進入到另一個世界。瑞恩稱這種敘事為“蟲洞敘事”,特殊的跨世界旅行者如穿越時空隧道一樣,得以從一個世界被轉運到另一個世界。[8](P657)在劉易斯·卡羅爾的《愛麗絲漫游奇境》中小女孩愛麗絲在夢中跟著一只會說話的白兔的腳步來到一個奇幻的世界,開啟了一段奇幻之旅。在此,“入夢”只是敘述的需要,充當了“蟲洞”功能,愛麗絲從現實世界進入奇幻世界并沒有因果關系。而在《水滸傳》中,超自然世界與自然世界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妖魔世界的“敘事元始”對后面敘述的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將的世界提供了起源。之后,妖魔世界退出敘述,后來出現的世界成為敘述的主體。在離散的異質世界里,對后來出現的世界的敘述是敘事的主體部分,讀者主要根據敘事的主體部分重建世界的大小,但又感覺還有一重世界存在,不同的邏輯規律與可能的標準同時存在于異質世界,因此在這種情形下,建構世界的規模大小就更加困難。
虛構世界是不同于現實世界的另一種可能世界,甚至將版圖“侵入”不可能的世界。因此,僅從時空角度難以理解某些虛構的世界。試問,我們怎樣從時空角度理解博爾赫斯《阿萊夫》中的世界呢?這里的世界完全打破了部分與整體的包含關系,空間之間的關系出來了如敘述中的“回旋跨層”[9](P283)現象,A空間包含B空間,同時B空間又包含A空間:
阿萊夫的直徑也許比一英寸稍多,但是大千世界全在其中,真真實實而且毫無縮減。其中每一物體(如,鏡面)都是無限的,因為我從世界的每一個角度清楚地觀察它們。我看見浩瀚的海洋,我看見破曉和黃昏……我從每一個角度每一個方位看阿萊夫,在阿萊夫中我看見地球,在地球中又有阿萊夫,在阿萊夫中又有地球。
這里展示的世界是一個難以想象的世界,完全突破了現實世界中邏輯規律的矛盾律和排中律。對于阿萊夫這個神秘的物體,任何語言對它的描述都顯得蒼白無力,因為它不屬于現今任何存在意義上的“存在”,就連在文本中創造了這個世界的博爾赫斯也表示用語言描述這個世界時的絕望。這樣的世界在中國的宗教思想中卻不少見。如前面所述,佛教中有“微塵亦有三千大世界”的說法。道教洞穴信仰中的“壺”和“洞穴”的世界也是一個超越現實世界時空概念的世界,有著特殊的時空系統,可以隨意地伸縮時間和空間。“壺中天”是“重復套匣”式結構,即壺中天還有“壺”,跳進去之后還有壺中天,而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本身就是壺中世界的一角,壺中世界又被包裹在另一個壺中世界里,可以不斷地循環往復,令人目眩地展現了空間的相對性。[10](P182)在《西游記》中這樣的例子雖不能說俯拾皆是,卻也并不少見。黃河水伯的寶物白玉盂兒精美小巧,平日被藏于衣袖之中,卻能裝下整條黃河之水(第五十一回);觀音菩薩手中托著的一個小小凈瓶竟能“盛下一海之水”;在第三十三回“外道迷本性,元神助本心”中,孫悟空用一個一尺七寸長的大紫金紅葫蘆玩起了“裝天”的把戲,騙過金角大王、銀角大王手下的兩個小妖精細鬼和伶俐蟲,獲取寶貝紫金紅葫蘆和羊脂玉凈瓶。這些“壺中天”空間的神奇特異,顛覆了常規的空間概念,極大地考驗著讀者的想象力,許多讀者也許只能茫然喟嘆。
總的來說,虛構世界的大小是模糊的、相對的,讀者重建的虛構世界通常比文本敘述所再現的世界要大。故事可以延續,但敘述文本有限,作者在創作時必然有所取舍,敘述什么,不敘述什么,這些與敘述文類、作者的取向、作品風格、不同時期的文化等因素有關。多勒策爾依據“飽和功能”來判斷虛構世界的大小,“將敘述的清晰質地、模糊質地和零質地稱為文本密度,將文本密度投射到虛構世界的飽和度:清晰質地建構確定域,模糊質地建構不確定域,零質地建構空白。”[11](P182)這種觀點與中國學者傅修延的觀點具有異曲同工之妙:“敘述像是一束強光,照亮著虛構的世界的某些部分,無論敘述有多長,它照亮的都只能是部分而不可能是全體。讀者可以清晰地看見這些照亮的部分,也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些未被照亮的部分,由是他感覺到了虛構的世界的規模。”[1](P31)讀者通過對虛構世界“未被照亮的部分”或“空白”的填補、想象、推理會大大地擴大虛構世界的大小規模。
[1]傅修延.講故事的奧秘——文學敘述學[M].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
[2]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3]張秉真.克羅齊藝術直覺辨析[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2(3):32-37.
[4]Stephen K..orner.“Individuals in Possible Worlds,”In Logic and Ontology,(ed.)M.K.Munitz.NewYork:N.Y University Press,1973.
[5]張新軍.可能世界敘事學[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1.
[6]Marie-Laure Ryan.Possible Worl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Narrative Theory[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
[7]Lubomir Dolezel Kafka’s Fictional World,Canadian Review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1.1(1984):61-83.
[8]Marie-Laure Ryan.From Parallel University to Possible Worlds:OntologicalPluralism inPhysics,Narratologyand Narrative.Poetics Today 27.4(2006):657.
[9]趙毅衡.廣義敘述學[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3.
[10]連振娟.《西游記》與道教生命文化——以《西游記》中的“洞穴”為視角[J].江西社會科學,2010(12):179-183.
[11]LubomirDolezel.Heterocosmica:FictionandPossible Worlds.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
I04
A
1007-9106(2016)04-0118-05
*本文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課題“敘事中的故事與世界研究”(編號:WGW1418);九江學院校級重點課題“可能世界與虛構敘事研究”(2014SKZD003)的研究成果之一。
*
周志高,九江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江西師范大學敘事學研究中心成員,研究方向為敘事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