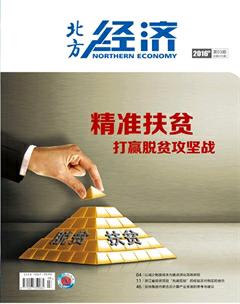國有企業“供給側改革”的階段與著力點
李錦
要使中國國有經濟重新恢復增長動力,必須從供給側發力:
新供給的主體是誰?是提供產品與服務的經濟組織——企業。
新供給的形態是什么?是生產,是實體經濟。
“供需不匹配”是“供給側改革”最基本的背景,“供需匹配”是“供給側改革”最基本的目的。解決“供需不匹配”的落腳點是“去產能”。去產能的主要對象是重工業,包括鋼鐵、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鐵礦石、有色金屬這首當其沖的8大行業。而這些行業的企業多為國有企業。
“供給側改革”的外部動力是政府,內部動力是企業。通過改革來構建“新動力”,通過調整來設計新結構,通過創新來提供新“供給”,這是中國企業對“供給側改革”的回答。
“供給側”不應是一個生澀的熱詞,而是認知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常識性視角。積極擁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成為一種時代共識,應該成為國有企業的一種共識,也是讓中國重新獲得國企改革紅利的必由路徑。
新供給經濟周期與國企“三個一批”的高度吻合
研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具體措施,可以發現,新供給經濟周期與國企改革《指導意見》中的“三個一批”改革(實際上是“四個一批”,因為“創新發展一批”,包含了創新與發展兩個層次),非常吻合。
第一階段,新供給形成階段:當新供給隨著技術進步孕育產生,社會舊有供給和需求結構仍在延續,經濟處在新周期的導入期,經濟潛在增長率開始回升;這正是企業創新階段,與國企改革《指導意見》中的“創新一批”相對應。
第二階段,供給擴張階段:當新供給內容被社會普遍接受,新的需求被新供給開發創造出來,新供給與新需求形成良性促進,經濟進入快速增長階段,經濟增速不斷提高;這正是企業發展階段,與國企改革《指導意見》中的“發展一批”相對應。
第三階段,供給成熟階段:該階段的生產技術進一步普及,供給仍然維持慣性增長,社會資源配置效率開始降低,經濟增速回落;這正是企業兼并階段,與國企改革《指導意見》中的“重組一批”相對應。
第四階段,供給老化階段:老化供給不能創造新的需求,新的供給力量尚未產生,經濟整體將陷入蕭條期。這正是企業清理退出階段,與國企改革《指導意見》中的“清理退出一批”相對應。
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重要的是清理退出一批。鋼鐵、水泥、煤炭、油氣、有色金屬、玻璃等上游產業的利潤下降幅度最大,利潤下降也最明顯。如果扣除這六項,其他行業的利潤變化并不是很大。所以,結構調整很重要的是上游板塊要進行較大力度的結構性調整。
顯然,中國在供給側的改革應該著眼于放松政府管制與干預,鼓勵企業創新、重組與清退。但是,這并非僅僅靠改變某些經濟政策就能實現,而是全面地改革,改變政府部門抓住權力不放的行為習慣,改變國企本身安于現狀、不思改革、總是等著上面催逼的狀態,改變國人的思維方式,講究誠信、遵守法治、公平競爭、勇于創新。
國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消化過剩產能開始
首先是要清退,分類后確定清退的目標,一年初見成效,三到五年完成,即2018年基本完成,要有路線圖、實施圖與時間表。第二要刺激,供給是個手段,消費是目的,不是用投資刺激,而是用供給刺激。第三要兼并重組。第四,將產品銷售到東南亞、亞非拉,加大出口消費的供給。第五是企業自身提高管理水平,轉型升級,增加供給的品種。
把歷史的時針撥回17年前,那一次以紡織業為突破口大規模兼并重組,“去產能”效果立竿見影,但也帶來了就業率下降、內需不足等問題。所以,這一次去產能不能像以前一樣只“破”不“立”,應該由國家來制定標準,定性、定量、定標準、定時完成。應該避免刮“破產風”,多用“騰籠換鳥”的方式消化產能。處置的政策要明確,堅持企業主體、政府推動、市場引導、依法處置,多兼并重組,少破產清算,同時做好職工安置工作。
政府支持國企供給側改革,從減低成本開始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多是作用于微觀,而不是作用于宏觀。企業負擔過重,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為造成的,這也是企業減負多年來成效并不顯著的原因。 一手要去產能,一手是要降成本。微觀主體有活力了,經濟才能有持久的發展動力。對企業即生產者,政府要做好為企業服務的工作,關鍵是幫企業降低成本,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業稅費負擔、社會保險費、財務成本、電力價格、物流成本等,打出一套“組合拳”。
減輕企業負擔,本質是政府自我改革。因為企業成本中一個重要成分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行政性壟斷的堡壘還很堅實,特別是一些地方不是真放權,放下的權又要收回去,或是表面放權背地里收權。
企業另一項重要成本是稅費。行業研究顯示,當前中小企業需要繳納所得稅、增值稅、營業稅、流轉稅等20多種稅費,面向中小企業的行政收費項目更多達五六十類。萬博經濟研究院有關測算表明,中國企業的綜合稅費負擔平均約40%。應根據既定稅負水平對應的公共服務指標,減輕企業稅費負擔存。但企業稅費對應的是財政收入,稅費負擔重來自政府,減稅費需要政府對自己“動刀”,減少各種行政開支。
員工社會保險也是企業的重要負擔。根據目前的社保繳納政策,絕大部分省市的繳納比例都在工資總額的40%以上。在全球181個國家中,我國社保繳費率排名第一。可是,養老基金大量缺口卻是近年來廣受關注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基數定得高,勢必形成一個非常大的基金窟窿。要想填補養老金缺口的同時降低企業社保繳費負擔,政府需要拿出良策。
物流成本是讓企業頭痛的另一個問題。數據顯示,企業物流成本占銷售額的比例,中國為20%-40%,發達國家在9.5%-10%。中國的過路過橋費占運輸成本的34%。路橋業已成為一大暴利行業,利潤水平已超房地產、石油、證券等行業。而路橋收費的背后是政府,在于政府的自利性。降低企業物流成本,政府仍要和自己過不去。
大政府的社會管理模式、不完善的法治狀態、不正確的政企關系,都是造成企業成本高的重要原因。政府要為企業發展創造條件,就得切實轉變執政理念,加快轉型,建設服務型政府。這需要的是決心,決心多大,決定政府能走多遠,企業的負擔能減輕多少。
供給側是一個新處方,這個藥方是否有效,是否管用,關鍵在于政府部門。如果政府部門不放權,制度供給不到位,國有企業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就難以有效進行,政府動力就難以轉化為企業動力,藥效就出不來,供給側改革便是空話。
(作者系中國國資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責任編輯:康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