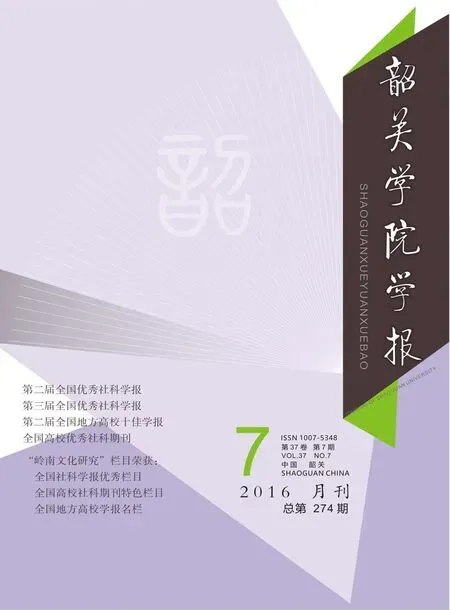后殖民視角下的利瑪竇文化身份與譯介活動
黃莉萍
(韶關學院外語學院,廣東韶關512005)
后殖民視角下的利瑪竇文化身份與譯介活動
黃莉萍
(韶關學院外語學院,廣東韶關512005)
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華期間留下了大量的翻譯著作,撒播中西文化交流的種子。從后殖民視角研究利瑪竇的文化身份與譯介活動,認為權力與譯者主體性是制約其譯介活動的因素;并揭示利瑪竇文化身份的雜合性及協商性對其譯介活動的重要影響。
利瑪竇;后殖民視角;文化身份;譯介活動
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于明清之際來華,先借佛僧的身份與衣著立足傳教,后改弦易轍,采用儒冠儒服,研習中國語文與儒家經典,開創并實施了“學術傳教”的曲線傳教策略,使天主教在中國特殊政治、信仰的歷史環境中得以生存。他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貢獻,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近30年來,國內外學者從人文到科學,從歷史到語言,從藝術到自然等方面對利瑪竇展開不同領域的研究。隨著中外經濟文化交流活動日益活躍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升溫,不少學者采用宗教學、歷史學、政治學、傳播學等理論進行利瑪竇研究[1-3]。就利瑪竇的翻譯活動研究而言,主要是有關利瑪竇的翻譯譯材選擇和策略取向的研究[4-7],此外還涉及術語的翻譯研究[8-9]。后殖民翻譯研究的核心在于剖析翻譯、權力和文化的關系。它以翻譯活動與翻譯文本的產生環境為基礎,揭示翻譯活動背后運作的權力機制,即后殖民翻譯語境中譯者、翻譯活動與譯文受到權力關系的制約,翻譯活動和譯文則可以塑造或解構權力關系。本文以后殖民翻譯理論探討利瑪竇的文化身份與譯介活動,分析制約其譯介活動的因素,并揭示其文化身份對譯介活動的影響。
一、后殖民翻譯理論對利瑪竇譯介活動的啟示
道格拉斯·羅賓遜于1997年提出了“后殖民翻譯研究”這一概念術語[10]。它以整個人類歷史為背景,從政治與地域的統治延伸到文化的控制與反控制,為后殖民翻譯研究打開了更為廣闊的視野。翻譯研究不能脫離翻譯活動制約因素的研究,翻譯活動也必然與譯者及具體文化語境中的權力和操縱等因素相聯系。后殖民翻譯理論中的權力關系成為考察歷史文化互動中利瑪竇翻譯活動的關鍵,而譯者利瑪竇的主體地位和權力則通過后殖民翻譯理論得到充分體現。
(一)權力
權力關系是后殖民翻譯研究的核心內容。布迪厄曾將關于權力的研究進一步深入到語言層面。他認為語言關系總是符號權力關系,權力隱身為各種符號資本,并附著于語言之中[11]。因此,語言交流蘊含著隱藏的權力行為。擁有較多文化的資本操控著擁有較少的文化資本,權力關系就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了。明末清初時期,中國科學技術緩慢地發展,在天文學、數學、物理學和機械工程學等方面大大落后于歐洲。利瑪竇擁有歐洲的幾何學、天文學和地理學等科學知識,并實踐傳播西方自鳴鐘制作、地圖繪制、房屋建筑等技術知識。因而他代表了強勢語言一方,具有較多的文化資本和強大的場域影響力。擁有文化資本較少的中國處于世界文化場域邊緣地位,在場域中占據被動的位置,成為弱勢語言一方。利瑪竇作為強勢語言的一方,可利用其優勢地位操控翻譯行為,積累更多的文化資本,鞏固其中心位置。
(二)譯者主體性
在后殖民語境中,譯者面臨雙重身份的嚴峻考驗:其一,若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只采取本土策略,則難以實現不同文化融合交流的架橋目的,實現文化的多樣性與多元化。其二,若譯者采用異化翻譯的立場,則易于淪為他者發出異質聲音的傳聲筒。后殖民翻譯理論凸顯了譯者主體性的地位和作用,并賦予了譯者更大的權力,能決定原文能否在目的語中傳播和生存下去,使譯者真正成為“主宰”者。不管是對翻譯文本的選擇、理解和詮釋,亦或是翻譯過程中具體翻譯策略的取向和選擇,譯者由始至終都是最具備主觀能動性、最積極活躍的要素。翻譯全過程自然與譯者主體性密切相關。利瑪竇在通過接觸和體驗中國文化的同時,進行文化間的溝通與雜合,又保留自身的文化身份。在協調文化關系與應對文化差異時始終自主地選擇其翻譯策略來體現文化態度,確保傳播文化價值的成功。
(三)后殖民語境下譯者文化身份
張裕禾認為文化身份由以下5種成分構成:(1)價值觀念或價值體系;(2)語言;(3)家庭體制;(4)生活方式;(5)精神世界。作為不同文化之間溝通的橋梁,譯者的主體性深受其個人文化身份的影響,而個人文化身份也會受到兩種或更多不同文化的影響[12]72-73。在《翻譯史研究方法》中,皮姆提出“交互文化”(interculture),闡釋了不同文化間交叉或重疊的觀念和行為、兩種或以上文化的內容兼融[13]。“交互文化”與“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ty)大不相同。“多元文化”是指在某社會或政治單元中能找到多種文化。譯者屬于兩種文化的重疊或交匯部分,因而他們往往被視為交互文化的成員,或者擁有一定程度的交互文化性(interculturality)。譯者自身身份的定位對其翻譯行為產生影響,而其翻譯行為對塑造自身文化身份至關重要。
二、利瑪竇的雙重文化身份與翻譯活動
(一)利瑪竇的雙重文化身份
利瑪竇具有雙重文化身份,這與他早年的成長背景、學習經歷與生活環境密切相關。利瑪竇出生于意大利馬切拉塔的一個沒落貴族家庭,父母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曾就讀于耶穌會羅馬公學院文學院和哲學院,接受了良好的耶穌會人文主義教育。來華后利瑪竇曾多次提及在耶穌會羅馬公學院的學習經歷,并將之稱為哺育自己的“母巢”。他從小就深受家庭與學校教育的熏陶,遠離故鄉來到中國也只是為了傳播天主的“福音”。自1582年起他開始了長達近30年的傳教生涯,主張“慢慢來”的傳教方針,“逐漸同中國社會交往,消除他們對我們的疑心,而后再說大批歸化之事。”[14]利瑪竇發現當時中國以儒家思想和道家學說為主流,其成熟的理論體系和穩固的政治地位使天主教難以在中國立足和傳播。于是他以積極的態度了解和適應中國的民族和文化傳統,并利用自己的雙重身份推動兩種文化的互動和融合。一方面他采取個人之間的直接交流方式,即面對面交談與書信往來,贏得了一批關系密切的朋友,其中一部分最后成為了皈依者;另一方面利用著書立說的方法曲折地傳播天主教義。利瑪竇把自己裝扮成一個道德家、哲學家和學者,通過知識傳播以實現教義傳播。
(二)利瑪竇的翻譯風格
利瑪竇的雙重文化身份使其可以跳出單一文化的束縛,而以更為客觀的角度來審視這兩種文化。利瑪竇來華的目的和動機是為譯介西學力圖獲得中國知識分子的承認和接納,尋求融入當時中國社會的共同語言,以期順利實施“學術傳教”的策略。在這樣的目的和動機驅使下,他在翻譯時考慮的首要要素就是讓譯語讀者喜愛和理解譯文,于是采取了適應譯語讀者(即中國知識分子)內在需求的翻譯方法。因此,在他的11部西學譯著中大多數以數學、天文類為主,順應他們渴望在數學、天文學等學科理論上有所突破的心理需求。在西學譯著的翻譯過程中,利瑪竇極少逐詞逐句的完全直譯原文,而是采用節譯、編譯或譯寫等“變譯”方法。因為變譯能夠更好地順應特定的讀者和具體的交際環境,即順應儒家知識分子的文化傳統,促使知識分子在兩種文化共通與互補的基礎上接納并吸收西方科學文化。例如,他在闡述《二十五言》的西方道德規范時,引進了不少的儒家倫理價值元素,選用一些儒家經典的精辟言論。其中關于“有在我者”與《孟子·盡心上》“求在我者”的論述非常相似,“有不在我者”與“求在外者”也是如出一轍。傳教士的變譯策略主要包括增(釋、評、寫)、減、編、述、縮、并、改等內容。利瑪竇翻譯的寓言The Swollen Fox涉及5種以上變譯策略。該寓言中的對話“Ah,you will have to remain there my friend,until you become such as you were when you crept in,and then you will easily get out”本為直接引語,利瑪竇將之變譯為敘述的間接引語,把另一只過路狐貍的建議改成饑餓的狐貍對雞籠主人恐懼的心理,與之前的“身瘦癯”相呼應,最后譯為:“恐主人見之也,不得已又數日不食,則身瘦癯如初入時,方出矣。”此外,利瑪竇以“雞棲”、“食”、“門”、“隙”改譯原文的bread、meat、hollow、oak、hole。將原文“發現橡樹洞里有面包和肉,于是鉆進洞飽餐一頓”改為“就雞棲竊食,門閉無由入,逡巡間忽睹一隙,僅容其身,饞亟則伏而入”,意為看到別人家里雞籠有食物就鉆門縫偷吃。又如:
(1)原文:A fox,very much famished.
譯文:野狐曠日饑餓,身瘦癯——增(寫)
(2)原文:When he finished,he was so full that he was not able to get out,and began to groan and lament very sadly.
譯文:數日飽飫欲歸,而身已肥,腹干張甚,隙不足容——增(寫),減(復句)
(三)文化身份的雜合性與協商性——利瑪竇翻譯風格成因
利瑪竇的文化身份具有雜合性,是本土文化身份與異域東亞文化身份雙重文化身份的集合體,這就意味著利瑪竇是本土文化與異域東亞文化的交匯或重疊。利瑪竇文化身份的雜合性決定了其在翻譯文本語言時的文化雜陳:重視譯語讀者能否理解與接受原著,兼顧他們對譯語文化的異質性的期待。如在翻譯拉丁文中的“基督教的至上神”Deus時,利瑪竇選用中國史書中意為“上天之主”的“天主”表達一種莊嚴神圣的意思,把權威的觀念和上帝之名合配起來。
利瑪竇的文化身份受到種種權力因素影響,具有協商性的特點。源語、原作者、譯語社會政治條件、譯語讀者等構成了利瑪竇所受影響的權力因素。利瑪竇入華之際,中國社會處于關鍵時期,面臨重大的變革,一些具有責任感與使命感的知識分子深刻反省與批判舊文化傳統領域里的價值觀念。利瑪竇抓住這一契機,選擇了翻譯西方科技著作為突破口,并譯介了《交友論》等道德倫理方面的作品。翻譯首要考慮的是譯文在譯語中的接受問題。利瑪竇順時而動,譯介當時需要的西學知識,是受制于翻譯所處的特定時代和各種權力斗爭協商的結果。他的文化身份是特定社會歷史文化環境下的協商性產物。在明清時期復雜多變的社會文化環境下,利瑪竇選擇了適當的翻譯文本和翻譯策略,其譯著受到中國知識階層的認可,對中西文化的交融做了開創性的探索,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
[1]戚印平,何先月.再論利瑪竇的易服與范禮安的“文化適應政策”[J].浙江大學學報,2013(3):116-124.
[2]曾崢,孫宇鋒.利瑪竇的中西文化交流之理念和價值[J].江西社會科學,2013(9):119-123.
[3]何先月.漢語書寫與禮儀之爭——利瑪竇的書寫技藝在跨語際文化信仰傳播中的作用與后果[J].世界宗教研究,2015(5):134-147.
[4]屠國元,王飛虹.論譯者的譯材選擇與翻譯策略取向——利瑪竇翻譯活動個案研究[J].中國翻譯,2005(2):20-25.
[5]梅曉娟,周曉光.選擇、順應、翻譯——從語言順應論角度看利瑪竇西學譯著的選材和翻譯策略[J].中國翻譯,2008(2):26-29.
[6]朱志瑜.天主實義:利瑪竇天主教詞匯的翻譯策略[J].中國翻譯,2008(6):27-29.
[7]符金宇.“重寫者”利瑪竇——《二十五言》重寫手段與策略分析[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1(1):74-78.
[8]馮天瑜.利瑪竇創譯西洋術語及其引發的文化爭論[J].深圳大學學報,2003(3):98-103.
[9]戚印平.Deus的漢語譯詞以及相關問題的考察[J].世界宗教研究,2003(1):88-97.
[10]Robinson,Douglas.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M].Manchester:St Jerome,1997a.
[11]傅敬民.布迪厄符號權力理論評介[J].上海大學學報,2010(6):104-117.
[12]張裕禾,錢林森.關于文化身份的對話[M]//樂黛云.跨文化對話.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
[13]Pym A.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7.
[14]劉俊余,王玉川,羅漁.利瑪竇書信集[M].臺北:光啟出版社、輔仁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1986.
(責任編輯:明遠)
Matteo Ricci’s Cultural Identity and Translational Activities from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HUANG Li-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 512005,Guangdng,China)
During his stay in China,Italian missionary Matteo Ricci made a large number of translated works,which sows the seed of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al exchange.This paper explores Matteo Ricci’s cultural identity and translational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concludes that power and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re the restraints on Matteo Ricci’s translational activities and reveals how hybridity and negotiability of his cultural identity greatly influence his translational activities.
Matteo Ricci;post-colonial;cultural identity;translational activities
H059
A
1007-5348(2016)07-0049-03
2016-04-13
2015年韶關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韶州時期利瑪竇的文化身份與翻譯活動研究”(Q2015001)
黃莉萍(1982-),女,廣東陽山人,韶關學院外語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文學與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