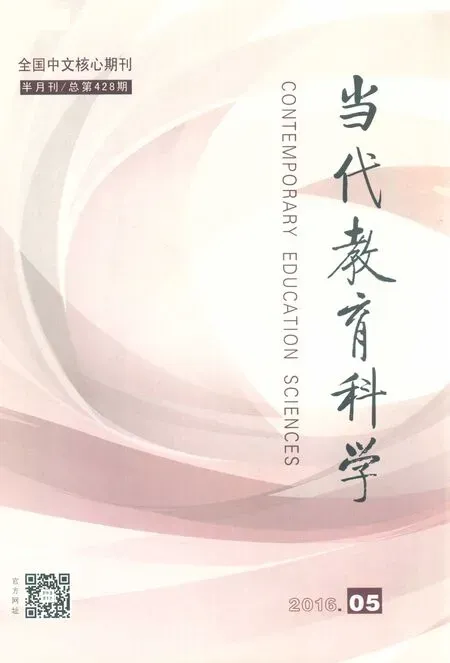從抵制到賦權:論西方媒介素養教育價值取向的歷史演變*
●吳文濤 張舒予
從抵制到賦權:論西方媒介素養教育價值取向的歷史演變*
●吳文濤 張舒予
媒介素養教育的價值取向是教育的組織者基于自身需要和對媒介價值的認識,在開展教育活動時的價值傾向。分析媒介素養教育的價值取向時,應把握其內涵的三個基本要義:教育組織者的自身需要;教育組織者對于媒介價值的認識;開展教育活動時組織者的行為傾向。西方的媒介素養教育發展歷程可劃分為印刷時代、電子時代、數字時代,其價值取向先后經歷了“階層化取向”、“人本化取向”及“民主化取向”的演變。
媒介素養教育;價值取向;階層化;人本化;民主化
就教育的價值問題而言,有一點是毋容置疑的,媒介素養教育作為人類的一種社會實踐活動,是具有其特殊價值的,本質上蘊含著教育主體的價值取向。本文試著站在價值哲學層面,從歷史學的角度,對西方媒介素養教育價值問題進行深入分析,著重探討西方社會媒介素養教育價值取向的歷史演變,期望能為當前我國媒介素養教育特別是教育實踐提供一種參照的視角。
關于價值取向的內涵,目前學界尚無統一的界定,現有研究中主要有三種代表性觀點:一是“標準論”,即價值取向就是價值標準,如有學者指出價值取向是指一個人所信奉的,而且對其行為有影響的價值標準。[1]二是“選擇論”,即價值取向就是某種價值選擇,如有學者認為價值取向是在價值選擇過程中決定采取的方向。價值取向是人們按照自行的價值觀念,對不同價值目標所作出的行為方向的選擇。[2]三是“傾向論”,即價值取向是某種價值傾向。所謂價值取向,是指主體在價值選擇和決策過程中的一定的傾向性。[3]價值取向就是指主體基于自身的需要與對客體的認識,采取一定行為的價值傾向。[4]應該說,以上界定各有其合理性與適用性,本文正是基于“傾向論”的觀點進行論述。具體而言,對于價值取向的認識,必須把握三個基本要義:一是主體的自身需要;二是客體的價值認識;三是行為的價值傾向。以此觀之,媒介素養教育的價值取向就是指教育主體,即媒介素養教育的組織者基于自身需要和對媒介價值的認識,在開展教育活動時的價值傾向。分析媒介素養教育的價值取向時,關鍵在于明晰其內涵的三個基本要義:一是教育組織者的自身需要;二是教育組織者對于媒介價值的認識;三是教育組織者開展教育活動時的行為傾向。
任何主體都是處于一定社會歷史背景下的主體,其價值取向與所處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背景密不可分。隨著社會的變遷,價值取向作為一種社會意識,體現為一種對社會存在的反映,也會相應地發生改變。[5]因此,倘若要準確分析西方媒介素養教育的價值取向,必須先對其發展歷程做合理劃分。回顧歷史,西方的媒介素養教育始終與媒介的形態特征密不可分,其發展歷程依據媒介形態的演化過程(印刷媒介、電子媒介、數字媒介)可劃分為印刷時代階段、電子時代階段以及數字時代階段。下文的探討正是基于此類劃分進行的。
一、批判與抵制:印刷時代媒介素養教育的階層化取向
20世紀30至50年代,印刷術的革新使得英國大眾報業飛速發展,各類報紙層出不窮,其中,最令在英國精英學派擔心的莫過于通俗化報紙的出現。精英階層視其為“低劣”的大眾媒介,認為其所傳播的通俗內容與蘊含的價值意識對于精英階層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形成了極大的沖擊。1933年,學者利維斯(F.R.Leavis)和他的學生湯普森(Denys Thompson)在媒介素養教育的開山之作《文化和環境:培養批判意識》極力強調大眾媒介的負面效應,認為這會影響普通民眾尤其是青少年的傳統文化理念和價值觀念。在利維斯及其追隨者們看來,大眾媒介及其傳播的內容,全是一種商業化、低俗化的文化,不能與傳統的精英文化相提并論,“那些在學校剛剛接受文化品味教育的年輕人,在校外卻陷入賺取最廉價感情的競爭中,電影、報紙以及各種形式的出版物和追求商業利潤的媒介故事,所有這些都只是迎合低級趣味,灌輸這樣一種觀念:用最少的精力,獲取最直接的快感。”[6]同一時期的法蘭克福派的學者們也是精英階層的代表,他們對待大眾媒介的態度與利維斯們不謀而合。在他們看來,大眾媒介的制造者為了獲取最大可能的商業利潤常常過分宣傳媒介的感官欲望和刺激,致使人們會沉迷失在媒介提供的美好的但又不存在的世界中。正是在對大眾媒介深刻批判的背景下,利維斯在其著作中系統闡述了媒介素養教育應如何開展,并在此基礎上針對學校的媒介素養教學提出一系列建議。例如,他建議教學中的課堂習題應針對不同形式的大眾媒介的危害進行設計,其隱含意圖就是教授民眾站在精英階層的立場批判與抵制大眾媒介。[7]
在此背景下,印刷時代的媒介素養教育價值取向的三大基本要義大體上呈現特征為:一是教育組織者的自身需要集中體現為保護精英階層的文化領地。有學者認為早期的媒介素養教育帶有強烈的“保護主義”色彩。然而,我們要認清的是,這種“保護主義”表面上聲稱要保護大眾不受媒介所傳播的低俗化的內容的影響,實質上是在批判與抵制大眾媒介的基礎上實現對精英文化的保護,是一種利己的、狹隘的自我保護主義;二是對于媒介價值的認識表現為媒介的負價值被放大,正價值被忽視。在主體與客體的價值關系中,價值可表現為正價值與負價值,客體對于主體的正效應,就是正價值;客體對于主體的負效應,就是負價值。[8]印刷時代的媒介素養教育過分夸大了媒介的負價值,媒介被貼上了“低劣”、“低水平的滿足”、“文化墮落”等一系列負面的標簽。精英學者們沉醉于對大眾媒介的一味批判,完全忽視了媒介在的積極價值,即媒介對于人的正價值;三是開展媒介教育活動時忽視大眾的話語權。這一時期,媒介素養教育中精英文化的高級與大眾媒介的低俗自然地轉化成教育主體和被教育客體的關系。在這樣一個新興的教育實踐中,社會民眾還沒來得及去做出自己的判斷就已經被安排的“井然有序”,他們的話語權被扼殺,自主選擇的權利蕩然無存。
印刷時代的媒介素養教育最初是為滿足精英階層保護自身的需要,其價值取向具有強烈的階層化傾向。這里所說的階層化傾向是指其精英階層作為教育的組織者與實施者,在媒介素養教育中秉承利己主義思想,一味地維護精英階級的文化利益,過分放大大眾媒介的負面效應,給大眾媒介貼上錯誤的標簽,忽視社會民眾自主選擇的權利。此種取向的媒介素養教育,究其實質,實為精英階級擔心自己的文化領地被大眾的媒介文化所占領,因而采取的是反對媒介的教育。
二、理性與甄辨:電子時代媒介素養教育的人本化取向
20世紀60年代初,隨著電子技術的日趨完善,以電視為首的電子媒介開始成為媒介舞臺的主角,人類社會從繁榮的印刷時代逐步走向成熟的電子時代。伴隨電子媒介對人類社會影響的加劇,媒介素養教育出現了一次關鍵的轉向,這次轉向與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崛起息息相關。
文化研究學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就明確指出:“對于文化這個概念,困難之處在于我們不得不持續地擴展它的意義,直到它幾乎等同于我們的整個日常生活。”[9]在出生工薪階層的威廉斯看來,文化作為日常生活的全部,不僅包括上流階層的精英文化,還應包括工薪階層的大眾文化。這種觀點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引發人們重新審視大眾文化與承載大眾文化的電子媒介。電子時代的媒介素養教育開始由印刷時代的反媒介走向對媒介的理性認識。這一時期的媒介素養教育雖仍舊強調大眾媒介的負面效應,但同時肯定其有促進大眾身心發展的作用。因此,媒介素養教育的核心任務應是教授民眾如何甄辨大眾媒介所傳播內容的好壞,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文化研究的后期代表人物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1973年發表文章 《電視話語的編碼與解碼》,提出了著名的“編碼-解碼”理論。他把傳播過程分為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再生產四個階段,視其為一個結構性的整體,以之取代了傳統大眾傳播研究的發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線性模式。[10]“編碼-解碼”理論強調傳播過程中受眾的地位,認為受眾與傳者是平等的關系。受眾的“解碼”會因人而異,其重要性等同于傳者的“編碼”。受此理論影響,媒介素養教育理念進一步轉變,從最初認同大眾文化的價值到后期開始強調大眾的主體性地位,保證大眾的主體性利益。
相比較印刷時代,電子時代的媒介素養教育價值取向的基本要義已有所轉變:首先,教育組織者的自身需要體現為強調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平等價值。早期的英國文化研究學派肯定大眾媒介所蘊含的大眾文化的價值,認為其與精英文化具有同等地位,大眾文化中也有對民眾有益的作品,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次,媒介的價值得到理性的認識。學校的媒介素養教育開始倡導對于媒介所傳播內容的區分教育,即什么是正價值,什么是負價值。對于價值的質可以有兩個層次的理解:一是正與負,二是正什么與負什么。[11]這一時期的媒介素養教育已經客觀地認識到媒介的正價值與負價值,并由對于媒介的價值的質的一般層次(即正與負)轉變為更深的層次(即正什么與負什么)的認識;再者,教育活動中開始注意到大眾的主觀能動性。主觀能動性的內涵主要有兩點:第一,對于客觀事物的能動認識;第二,對于客觀事物的能動改造。[12]依霍爾分析,受眾能夠“解碼”媒介所傳播的內容,這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分配-消費”,這是大眾能動的認識媒介內容;其二是“再生產”,這是大眾能動的改造媒介內容。這一時期媒介素養教育的主旨在于培養大眾主動意識,使得大眾在理性認識的基礎上學會甄辨媒介及其傳播內容的正價值與負價值。
通過以上對于電子時代的媒介素養教育價值取向的分析,我們發現,這一時期的媒介素養教育已經具有初步的人本化傾向。這種人本化傾向部分程度上也得到了同期發展到鼎盛時期的西方人本化教育思想的佐證。人本化教育強調教育應以人的“主觀性”為出發點,它強調人的主體性與個體性,強調人在困境中的自由和主動。[13]同樣,人本化傾向的媒介素養教育強調要培養受眾的內在分析、思辨和批判的能力,以使其在面對紛繁復雜、良莠不齊的媒介內容時,能有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辨別出大眾媒介中的“正”與“負”,做出符合其自身需要的判斷與理解。
三、融合與賦權:數字時代媒介素養教育的民主化取向
20世紀80年代后期,計算機與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數字媒介成為引領時代浪潮的主力軍。曾經的印刷媒介與電子媒介非但風光不再,反而開始以其自身的數字化向數字媒介轉型。越來越多的事物被打上數字的烙印,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使用數字媒介。從電子媒介到數字媒介,媒介傳播由單向傳播變為雙向傳播,人的個性與主動性在其中得到進一步顯現,這一點在媒介素養教育界對于媒介素養內涵界定的轉變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
媒介學者羅伯特·卡比(Robert kubey)曾經坦率的指出:“美國在媒介教育這一重要領域里屬于第三世界國家。”[14]然而,到了數字時代,美國媒介素養教育取得了跨越式進步,走在了世界的前列。1992年,美國媒體素養研究中心對于媒介素養的定義就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可,定義指出“媒介素養是21世紀的教育之路,它提供了一個框架,用來使用、分析、評估、創制訊息,不拘媒介形式……從印刷到影視到電腦網絡,民眾的媒介素養是基礎,在于了解媒介的社會角色,并擁有民主社會公民所需的質疑和自我表達的基本能力。”[15]2005年,該研究中心再次提出了媒介素養的五條核心概念,其中就強調:媒介被組織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利益或權利。[16]201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媒介與信息素養”的概念,它被定義為一整套的能力,它賦權于公民……以便于參與和從事個人的、職業的、社會的活動。[17]“民主”、“權利”、“賦權”……成為數字時代媒介的新標簽。
數字時代的媒介素養教育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各國深入開展,其價值取向也呈現出新的特征:第一,教育組織者的自身需要與大眾需要相融合。從電子媒介到數字媒介,最核心的轉變是從以往的以傳播者為中心轉向以受眾為中心。在媒介傳播過程中,大眾開始扮演著“演員”與“觀眾”雙重角色。媒介素養教育的組織者們逐漸意識到他們的需要與大眾的需要已經融為一體,難以區分,因而他們開始“鼓勵發展一種更加開放的、民主的教學方法”;[18]第二,媒介的價值得到進一步發揮。數字時代的大眾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媒介消費者,而是主動的媒介建構者。大眾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媒介中,通過創作媒介內容、增強媒介交往、傳播媒介信息等方式,創造出的一種自由、平等與共享的數字媒介文化樣式。當媒介的價值隨著其數字化的進程被進一步發揮后,相應的媒介素養教育也從傳統的教授轉向新型的引導,引導大眾去充分發揮媒介的正價值而非負價值,從而更好地參與到媒介傳播中;第三,教育活動中強調民眾的權利與利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曾強調,數字時代的媒介素養教育“可以幫助人們更好的享受其基本人權,它向公民提供了得以充分尋求和享受此項基本人權的能力,它是數字世界的一項基本人權,促進著各個國家的社會包容性……有了這項權利公民不僅可以了解信息的生產,更能了解信息的定位,并最終享受信息資源以參與到社會的各項活動中去。”[19]
綜上分析,在數字時代,媒介素養教育已經呈現出鮮明的民主化傾向。這種民主化傾向在實際的教育活動中表現在諸多方面:一是關系的民主化。數字時代的媒介素養教育開始重塑施教者與受教者的關系。施教者不再是絕對的權威,他們只是受教者認識媒介過程中的引路人與輔助者;受教者也不再是毫無“抗體”,他們不僅具備“免疫”的能力,而且能夠自己去重新建構媒介。二是活動的民主化。“媒介素養教育更多的是通過對話而不是通過論說來展開自己的調查研究。”“對話”這一形式成為西方學者最為推崇的媒介素養教育教學方式。[20]三是評價的民主化。媒介素養教育開始強調對于受教者的“發展性評價”以及受教者的“自我評價”,評價方式的改變不但反映了教育理念的轉變,也體現出教育活動中受教者地位的提升。
總的說來,西方的媒介素養教育的價值取向先后經歷了“階層化取向”、“人本化取向”與“民主化取向”的演變,而這種變遷的背后是人們對大眾媒介的認識與態度。每一種社會現象的出現必然有其背后的社會原因,每一種價值取向都是社會意識的集中反映。從“階層化取向”到“人本化取向”,再到“民主化取向”,反映的是大眾從被動安排到主動參與的轉變,彰顯的是從虛偽的“他人保護主義”到真實的“自我保護主義”的飛躍,體現的是從反媒介的教育到真正的媒介素養教育的進步。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認清媒介素養教育的價值取向的同時,還應了解兩點:第一,媒介素養教育的價值取向具有歷史必然性。在社會文化變遷的過程,無論是印刷時代的精英階層以保護大眾之名來維護階級利益,還是電子時代的工人階級為大眾文化的價值正名,抑或是數字時代媒介民主的來臨,這都是歷史發展必然出現的結果,也是媒介素養教育必然經歷的歷史階段。第二,媒介素養教育的價值取向的演變是一種新陳代謝的過程,每一時期都不是一味的否定前一時期,而是對前者的“揚棄”基礎上融入符合時代要求的積極元素,形成更符合社會發展方向的媒介素養教育價值取向。直至今天,早期的“保護主義”仍對今后的媒介素養教育提出警示,保護社會大眾尤其是青少年不受媒介所傳播的負面內容的腐蝕,仍然是媒介素養教育的最基本的目標之一。放眼未來,媒介技術的發展會達到一個更新的高度,對大眾媒介的研究也將成為西方社會的一個重要領域,而媒介素養教育也會在沿著“民主化”的路徑縱深變革。
[1]汝信.社會科學新詞典[M].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401.
[2]徐玲.價值取向本質之探究[J].探索,2000,(02).
[3]李德順.價值學大辭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46.
[4]袁貴仁.價值學引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350.
[5]易顯飛.技術創新價值取向的歷史演變研究[M].沈陽:東北大學出版社,2009.47-48.
[6]F·R·Leavis and Denys Thompson.Culture and Environment [M].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33.23.
[7]大衛·帕金翰,宋小衛.英國的媒介素養教育:超越保護主義[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0,(02).
[8]王玉樑.價值哲學新探[M].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40.
[9]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256.
[10]蔡騏,謝瑩.文化研究視野中的傳媒研究[J].國際新聞界,2004,(03).
[11]劉永富.價值哲學的新視野[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45.
[12]百度百科:主觀能動性[EB/OL].http://www.baike.com/wiki/.
[13]胡繼淵.淺述西方人本化教育思想及其借鑒[J].外國中小學教育,2002,(02).
[14]陳國明,J·Z·愛門森.美國的媒介素養教育(上)[J].中國傳媒報告,2008,(01).
[15]周典芳,陳國明.媒介素養概論[M].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213.
[16]宮淑紅,張潔.媒介素養教育理論與實踐[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29.
[17][19]吳文濤,張舒予.“媒介與信息素養”的多視角解讀[J].新聞戰線,2015,(02).
[18][20]宋小衛.西方學者論媒介素養教育[J].國際新聞界,2000,(04).
吳文濤/安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講師,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
張舒予/南京師范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從共享到共生:基于專題學習網站的知識建構轉型研究”(12YJA880161)、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資助項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馮永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