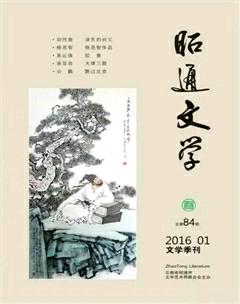鄉(xiāng)村才是我的歸宿
沈洋
我是一個農(nóng)民的兒子,來自云南昭通大山包山區(qū),一個直到十二歲才獨(dú)立走出過大山的孩子,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山里人。說來慚愧,這次參加《萬物生》的研討會,我第三次來到北京,第一次,是2012年,來北京參加我的小說改編的電影《包裹》全國首映禮,這是快四十歲的我第一次來到首都;第二次是2015年8月,有幸參加中國文聯(lián)文藝研修院第九期中青年文藝人才(編劇)高級研修班培訓(xùn);第三次就是來參加《萬物生》的研討會,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以如此隆重的方式進(jìn)京,會有這么多全國頂尖級的文學(xué)評論家、期刊編輯和專家老師們親臨現(xiàn)代文學(xué)館,為我的文學(xué)成長點(diǎn)燈、指路。因此,我非常感動、非常幸運(yùn)、非常幸福。但同時,我又感到非常慚愧,因為我的小說還沒有寫好,功力還遠(yuǎn)遠(yuǎn)不足,工夫還下得不夠,藝術(shù)水準(zhǔn)還很差,辜負(fù)了各位專家老師的期望。因此,我特別感謝在百忙之中,撥冗出席研討會的各位領(lǐng)導(dǎo)、各位專家老師和朋友。
因為文學(xué),我從一名鄉(xiāng)村教師一步步從大山里走出來,成長為今天一名執(zhí)著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業(yè)余寫作者,成為一名文藝工作者,倍感榮幸。但當(dāng)從豆腐塊文章見諸報端雜志到后來多部中短篇小說在文學(xué)期刊發(fā)表,再到出了幾本書還拍了電影,自己也身居小城,過著人模人樣的日子之后,我才發(fā)現(xiàn),多年的機(jī)關(guān)工作早已讓自己與曾經(jīng)熟悉的土地格格不入,自己也變得畏難、怕吃苦、怕深入、怕麻煩了,甚至已經(jīng)變得麻木。我深知,對于一個作家而言,麻木才是最可怕的絕癥。
于是,我選擇了回到鄉(xiāng)村。從2009年開始,我就以個人名義,深入全國文明村三甲村體驗生活,2012年,又正式被組織部任命為永豐鎮(zhèn)新農(nóng)村建設(shè)工作隊隊長、鎮(zhèn)黨委掛職副書記、三甲村黨總支常務(wù)書記,一直干到2014年初。近六年來,我把三甲村當(dāng)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xiāng),開著一輛破舊的面包車,有時騎單車或步行,走村竄戶,遍訪農(nóng)家,成了三甲村的一個編外村民,成了一名泥腿子村干部,成了村民的鄰居和朋友。在永豐鎮(zhèn)和三甲村掛職期間,我?guī)ьI(lǐng)我的工作隊員為鎮(zhèn)村爭取了500余萬元的資金和項目,實(shí)施了“文化十個一工程”和“廉政文化十個一活動”,還組織三千多村民自編自導(dǎo)自演了一部農(nóng)民群眾自己的電影《我和三甲有個約定》,并獲得了全國和省的一些獎項。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之所以選擇到三甲村去掛職體驗生活,是因為我想在這個昭通已經(jīng)率先富裕起來的有昭通第一村之稱和全國文明村之稱的村莊里,試圖去探尋在新農(nóng)村建設(shè)中,當(dāng)農(nóng)民群眾解決了物質(zhì)層面的需求之后,下一步他們需要什么,各級黨委、政府和干部應(yīng)該為他們做些什么,他們自己又該干些什么?是文化的提升、是傳統(tǒng)道德的重塑、還是新時期農(nóng)民群眾對精神自由、對幸福指數(shù)的深層次提升?這些,都是我想去實(shí)踐并探尋的答案。因此,我是帶著深厚感情去駐村工作的,并身體力行地開展了一系列文化和道德建設(shè)的實(shí)踐活動,想以三甲村為實(shí)驗田,去真誠傾聽鄉(xiāng)親們的心事和脈動,去真切感受他們生活的酸甜苦辣,去零距離感知他們的人情世故,去體味他們對于未來生活的期許和向往。在之前體驗生活的五年時間,我不敢動筆寫下小說的任何一個字,生怕寫不好、寫不深、寫不透。
2014年10月15日,習(xí)近平總書記組織召開了文藝工作座談會并作了重要講話,“追求真善美是文藝的永恒價值”、“人民是文藝創(chuàng)作的源頭活水,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dǎo)向”等精辟論段,為我這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指明了方向,使我更加堅定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理想。我試圖以昭通蘋果產(chǎn)業(yè)改造提升為背景,以掛職干部文雅琪深入鶴鎮(zhèn)開展群眾工作為主線,融入當(dāng)前農(nóng)村普遍存在的種種復(fù)雜問題和尖銳矛盾,去展開當(dāng)前農(nóng)村發(fā)展的真實(shí)面貌,去打開一扇認(rèn)識新時期農(nóng)村現(xiàn)狀的窗口。但由于自己功力不夠,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小說《萬物生》的創(chuàng)作中,還有很多的問題和不足,還有很多的遺憾。
幸運(yùn)的是,在《萬物生》的研討會上,各位專家老師對我的不成熟的小說作品給予了精準(zhǔn)的點(diǎn)評,既鼓勵了我,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小說存在的不足和問題,讓我有醍醐灌頂之感,突然間豁然開朗,深受啟發(fā)。這不僅對于修改完善修訂這部小說有利,更對我今后的創(chuàng)作有利,讓我十分感動。
我來自鄉(xiāng)村,鄉(xiāng)村是我的衣胞之地,永遠(yuǎn)給予我健康的食物、水分和空氣,給予我精神動力,給予我創(chuàng)作源泉,鄉(xiāng)村才是我的歸宿,我會萬分珍惜各位專家老師的中肯批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努力提高自己的創(chuàng)作水平,力爭創(chuàng)作出更好的小說作品。
作者系昭通市文聯(lián)副主席,《萬物生》作者。
【責(zé)任編輯 吳明標(biā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