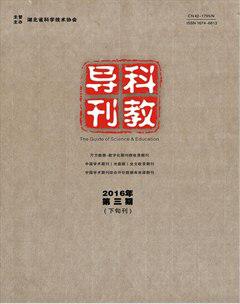朱熹“小學”教育思想及實踐
趙遲
摘 要 朱熹是南宋最富盛名的大教育家,他長期從事教育活動,并精心編撰了多種教材,其中,蒙學教材的編寫便是其教育實踐活動的表現之一。自隆興二年至淳熙十四年,朱熹先后編寫了三本蒙學教材,即《訓蒙絕句》(1164年,五卷)、《童蒙須知》(1186年,一卷)、《小學》(1187年,一卷),并在日常教育活動中加以使用。朱熹的“小學”教育及蒙學教材編寫,對儒家學說大眾化和文化重心下移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關鍵詞 朱熹 蒙學教材 “小學”教育
中圖分類號:G629.2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j.cnki.kjdkx.2016.03.072
自古以來,教育的社會價值在我國就一直被反復強調,被譽為我國最早的教育學專著《學記》開篇即指出“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在書中,作者描述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學制系統和各階段的學習目標:“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可見,從教育的社會價值出發,教育是非常受重視的,作為兒童接受教育之端的啟蒙教育,其基礎作用更是被反復強調。《周易·蒙卦》有“蒙以養正,圣之功也”之說;在商周時期,有了為貴族子弟設立的小學,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伴隨著私學的產生,民間兒童啟蒙教育機構相繼出現,及漢代漸趨成熟,此后,蒙學獲得了極大的發展,至宋代又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宋代學制基本上沿襲前代,自三次興學后,完備的官學教育體系才基本建立起來。在中央,接受“小學”教育是需要一定條件的:“凡諸王屬尊者,立小學于其宮。其子孫,自八歲至十四歲皆入學,日誦二十字。”地方“小學”在興學后也應聲而起。蒙學教材作為傳播文化的重要載體,自周代開始,至宋代,獲得了極大發展。
1 蒙學教材
蒙學教材的發展史可以追溯到三代。最早的蒙學教材是周宣王時的《史籀篇》。到了秦代,蒙學教材有李斯的《倉頡篇》、趙高的《歷篇》、胡毋敬的《博學篇》,這三種教材都是以識字寫字為主,是對《史籀篇》的發展。漢代,閭里書師將上述三種教材編為一集,取名《倉頡篇》;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作《急就篇》;李長作《元尚篇》;楊雄續寫《倉頡》,取名《訓纂篇》;賈魴作《滂喜篇》;蔡邕作《勸學篇》等。其中,以《急就篇》流傳最廣,影響最大。魏晉南北朝時期,有多種蒙學教材出現,如:束皙作《發蒙記》,顧愷之作《啟蒙記》,周興嗣作《千字文》,此外,還有《雜字指》、《俗語難字》、《雜字要》等,這些雜字書對后世的影響很大。唐代的蒙學教材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前編寫,當時仍在使用的,如《急就篇》 、《開蒙要訓》、《千字文》等;另一類是當時新編寫的:有抄寫名言諺語,向學童進行識字教育和封建教育的,以《太公家訓》為代表;有將典故編成韻語,供學童識字和學習歷史知識的《兔園策》和《蒙求》;有供學童諷誦的當代詩歌選本《文場秀句》;有供學童臨時查閱的字書和常識問答,以《雜抄》和《俗務要名林》為代表;還有專供蒙童用的習字教材。到了宋代,蒙學教材不僅編寫質量提升,而且內容類型增多,甚而出現了專門為女子編寫的蒙學讀物。
2 朱熹的“小學”教育思想和他的蒙學教材
2.1 朱熹的“小學”教育思想
人性論是朱熹教育思想的邏輯起點,他從“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區別與聯系來說明人性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關系。所謂“天命之性”,是“專指理而言”,它是稟受“天理”而成的,所以渾厚至善,完美無缺;而所謂“氣質之性”,“則理與氣雜而言之”。由于“氣”有清明、渾濁的區別,所以“氣質之性”有善有惡。如果所稟之“氣”是“極清且純者”,那么“氣與理一”,“理”在“清氣”中,就好比寶珠在清水里,光澤透徹明亮;而如果所稟之“氣”是渾濁的,則“理”在“濁氣”中,就好比寶珠在濁水里,看不到寶珠的光澤。“天命之性”是“理”之全體,健順五常,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而“氣質之性”是“天命之性”通過人的具體生理、心理結構及其特點而表現出來的具體人性。因此,朱熹認為,“天命之性”人人皆同,“氣質之性”則因人而異。
朱熹從他的人性論出發,認為教育的作用在于“變化氣質以復性”。他說:“古之圣王設為學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性。”又“性”即“理”,“理”包括仁、義、禮、智、信,教育的目的即在于恢復以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即“明人倫”。
朱熹的教育思想充滿了濃重的儒家氣息和強烈的倫理道德色彩,不管是“小學”教育,還是“大學”教育,都體現了以“理學”為支配點的傾向。朱熹將教育階段劃分為“小學”教育階段和“大學”教育階段,前者以8~15歲為時間段,后者以15歲及以后為時間段。為著“存天理,滅人欲”的終極目標,結合“小學”教育階段兒童的心理特征,朱熹提出以“教事”為主的思想,他在《小學書題》中說道,“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又在《大學章句序》中說道,“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 ,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這些內容都是為著培養兒童的倫理道德服務的,因而契合了朱熹的“理學”觀。在實踐中,朱熹參與編寫蒙學教材,將其“小學”教育思想以固定的形式加以傳播。
2.2 朱熹的蒙學教材
朱熹的蒙學教材充分反映了他的以“教事”為主的思想,具有濃厚的講求倫理道德的氣息。《訓蒙絕句》又稱《訓蒙詩》,有詩98首,用七言寫成,編于隆興二年(1164年),其名目采用的大都是《四書》中的詞組成語句,如《就有道而正焉》、《十五志學》、《樂亦在其中》等,極具韻律,讀來瑯瑯上口。《童蒙須知》編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全書一卷,衣服冠履第一,語言步趨第二,灑掃涓潔第三,讀書寫文第四,雜細事宜第五。該書篇幅簡短,但內容涉及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不僅包舉廣泛,又非常切近兒童,對他們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很有教育意義,比如帽子、衣服、鞋襪要收拾整潔,對如何洗臉漱口、如何寫字也有說明,要早起晚睡,對長上要恭敬有禮等。《小學》一書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重新編撰完畢,共有六卷,朱熹作序說,“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于幼稚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捍格不勝之患也”。可以說,《小學》是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總結。全書分內篇和外篇,內篇有《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外篇有《嘉言》、《善行》。內篇是全書的主干,《立教》闡述先王所以教人之法;《明倫》說明五倫的關系;《敬身》講解孩童修養身心的重要和相應的規矩;《稽古》記載古代先圣前賢的崇高德行。外篇兩篇,記載值得我們效法的言行。
2.3 朱熹重視“小學”教育及蒙學教材的原因
青少年時期的朱熹,隨父母輾轉多地而接受了傳統教育,為他后來的學問成就打下了堅實基礎。朱父說,“爾去事齋居,操持好在初。故鄉無厚業,舊篋有殘書。夜寢燈遲滅,晨興發早梳。詩囊應令滿,酒盞固宜疏。募羈寧似犬,龍化本由魚。鼎薦緣中實,鐘鳴應體虛。洞洞春天發,悠悠白日除。成家全賴汝,逝此莫躊躇。”可見,朱父對朱熹的影響之深。朱熹從事教育活動多年,具有十分豐富的實踐經驗。關于兒童教育,朱熹也非常留意,并在多地設立私塾以教子孫。為了進行系統總結,朱熹編《小學》等蒙學教材以闡發其“小學”教育思想,對規范兒童的倫理道德行為起到了制約作用。
宋代商品經濟獲得了極大發展,無論是就規模還是水平而言,都遙遙領先于當時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①經濟的發展促使思想文化的繁榮,對于市民階層而言,他們普遍要求獲得文化知識。文化重心的下移,催生了民間私塾和蒙學教材的發展。但同時也有弊端顯現,朱熹有感于當時學校教育和科舉的弊端,大聲疾呼重建倫理道德的重要性,他說,“古昔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
3 評價
全祖望對朱熹及其思想這樣評價:“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這個評價是相當高的,它表明了朱熹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僅就編寫蒙學教材而言,他的影響也是舉足輕重的。蒙學教材是推動儒家學說大眾化的重要推力,朱熹本人親自編寫蒙學教材,不僅提高了蒙學教材質量,而且在蒙學教材中也灌注他一貫主張的教化思想,由此,倫理化的儒家學說更是在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地存活下來。
注釋
① 葛金芳.兩宋社會經濟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12.
參考文獻
[1] 蔡方鹿.朱熹與中國文化[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10.
[2] 袁征.宋代教育[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1.12.
[3] 顏佳琪.中國古代蒙學教材的發展狀況及其特點[J].遼寧教育研究,2001.9:25-26.
[4] 任新宇.中國古代蒙學教材研究[D].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