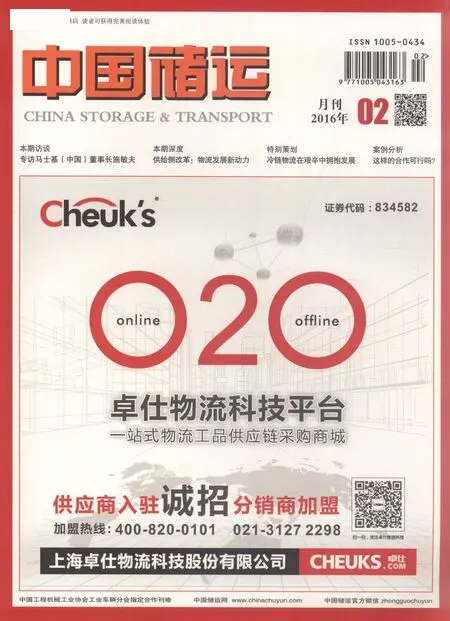薦讀《經濟人的末日》
文/李煒光
?
薦讀《經濟人的末日》
文/李煒光
去年年末的時候,我繼續受邀擔任新京報2015年好書評選活動的評委。這次我推薦的是彼得·德魯克的《經濟人的末日》。經全體評委投票評選,本書最終獲得了經濟類好書的第一名。
這本書于1939年在美國出版,那一年剛剛開過慕尼黑會議。就是那個由英國首相張伯倫、法國總理達拉第、納粹德國元首希特勒和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共同簽署協議,割讓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臺德領土給德國的四國首腦會議。
當時的歐洲,力圖體現自由平等價值的社會及政治秩序面臨崩潰,而興盛一時的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實踐也未能向世人證明其具有實現平等的可能性,這成為“大眾逃向極權主義絕望熾焰的主因”。在這個過程中,歐洲向往自由的“文明基礎概念”被徹底動搖,政治局勢危險至極。德魯克說,本書的寫作目的,就是“希望能強化人們維護自由的意志,抵御為支持極權主義而拋棄自由后所產生的威脅”,進而指出其所依據的信念是:在“歐洲傳統與極權主義革命的基本原則之間,毫無妥協的余地”。
本書把極權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和社會現象來解釋,探討其躍居政治與軍事支配地位的內在動力,得出極權主義起源于“人民追求平等”的結論。這是個至今看來依然驚世駭俗的觀點。作者以大量事實證明,法西斯主義就是靠滿足群眾“平等”訴求上臺的,在其政治運作中也始終嚴酷地追求這一目標——借消滅猶太人的名義打擊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在“國防經濟”中基本實現充分就業的目標;通過征收資本稅和企業稅剝奪中上階層使其收入水平向低下階層靠攏。德魯克指出,“納粹主義想以社會平等為手段,彌補勞工階級長久以來受到的經濟不平等”;“法西斯運用有機理論的目的,則是要創造出一種非關經濟的社會重要性、社會地位與社會功能的平等,一次平衡各階級在經濟上的不平等。”
“經濟人”的概念來自于斯密經濟學,意為“以最大經濟利益為他的行動依據,也總是知道該怎么做”。但這一概念無力滿足既要求自由也要求平等的歐洲人,所以“經濟人的末日”實際指的是資本主義信念的崩潰,不再有人相信“經濟自由”能造福人類。作者強調,群眾的絕望終于引來了極權主義。惡魔只需承諾實施一種全新的秩序,便贏得了廣泛的支持,實際上它所做的是掏空了人們以往享有的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留下的只是變了味的計劃管理和民主選舉而已。極權主義企圖以種種“非經濟手段”創造歷史,讓經濟發展中遭遇不平等的大眾在這個非經濟的社會中獲得平等,其結果是整個國家被推向極權主義深淵。人民交出了自由,得到了鎖鏈。
德魯克告訴我們一個足以令世界為之顫抖不已的道理:造成極權統治的并不是獨裁者本身,而是你我這些普通大眾。只是讓某一個獨裁者對極權統治的惡果承擔罪責,是對極權主義產生根源的無知。德魯克討厭當時的所謂“革命”,認為“絕大部分不過是權力斗爭而已”,指出新的極權主義才是真正的革命,其目的在于推翻某些比經濟體制還要基本的東西:價值觀、信仰和基本的道德觀等。
他認為,“只有當經濟平等不再被視為社會最重要的事情,新領域中的自由平等也成為新秩序的承諾時,經濟平等才可能實現。”他還頗具預見性地提出,有關生產和分配關系的社會及經濟體制(即資本主義),不但會繼續存在,還極可能在未來證明其帶動經濟發展的能力。
在敦刻爾克大撤退和法國淪陷之后,率先決定與納粹德國作戰的英國選擇《經濟人的末日》作為必讀書籍,分發給每一位即將成為英國軍官的年輕人。丘吉爾擔任英國首相前夕曾寫了一篇書評,稱這本書是“唯一一本了解并解釋兩次大戰間世界形勢的書”。本書的副標題與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相同,但前者的視角和方法是政治和社會的,專注于分析國家的政治結構及其運作過程,后者則是哲學的和觀念史的。阿倫特所短,正是德魯克所長。
今日閱讀此書,并無過時之感,反覺意味悠長。正如作者在1969年版序言中所說的:當今社會正迅速成為“知識社會”和“世界社會”,但這個新社會的根源,仍然穩固地植根于《經濟人的末日》所闡釋的經濟與社會之中。

形影不離梅 逢春
德魯克問道:極權主義有無可能卷土重來,再次壓垮我們?這是一個真實的問題,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他自問自答:在這一條路的盡頭,只可能出現另一個希特勒,另一個毒氣室和集中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