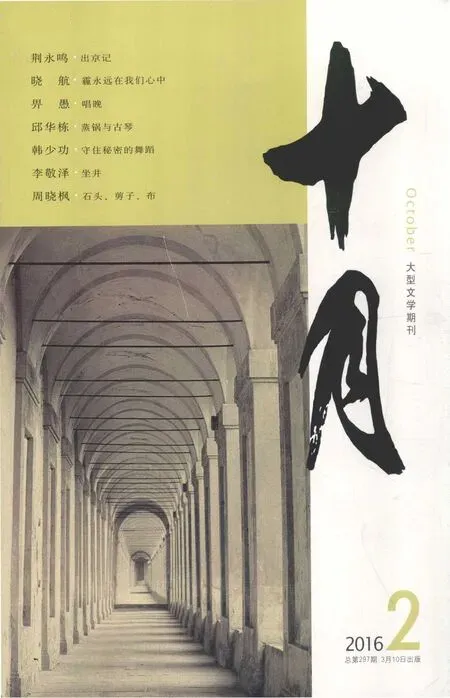坐井
李敬澤
這個冬天,它讓我想起當年的五國城。世界的極邊,莊子的大魚所居。很冷,冷到了地老天荒。
這片雪原上后來有個女子,叫肖紅,她寫了一本《呼蘭河傳》。呼蘭河應該就是五國城外的那條河。在那本書里,她很少提到冬天,她喜歡的是夏天、秋天、春天,是生長,不是寂滅。
而在我的記憶中,五國城是永恒的冬天。我一度確信我會死于此地,然后被凍成一個硬邦邦的家伙,不知歷了幾世幾劫,再被挖出來。我知道,在清朝他們就這么干過,當然他們挖出來的不是我,他們本來想挖出徽宗皇帝,結果挖出了一個女人,還有一幅畫。清昭樁《嘯亭雜錄》記載:“乾隆中,副都統綽克托筑城,掘得宋徽宗所畫鷹軸,用紫檀匣盛,瘞千余年,墨跡如新”。昭梿不曾提到的是,女人的臉上覆蓋著透明的冰,而那女人正在冰下笑。但愿那是巧笑倩兮的笑。反正據說好幾個家伙在此之后就以種種方法瘋了、死掉了。
我已經記不起徽宗皇帝臨死前的表情了。在后人的想象中,老頭兒應是以淚洗面,他們說他被金人囚禁在深黑的井底,坐井觀天,他是哭死、苦死、凍死的。他們才真是井底之蛙啊,在最后的歲月里,官家——在宋代,我們把皇帝稱為官家,他依然是一個健壯的男人,他依然有力量讓他的女人懷孕,他仍是我們這個人數日漸減少的被流放的朝廷的王。那日,大雪初霽,他在雪地里走了很遠,他走得很快,即使行于積雪,他的步態也絕不粘滯,就像他的字,我一直在臨摹他的字,那線條是多么挺拔迅捷,我感覺我已經無法挺到終點,快!他嚴厲地喝道,要快!你抖什么!你手里又不是刀!現在,他忽然站住了,抬手一指:看!
——白茫茫一片,前方是平緩的坡地,坡地盡頭佇立著烏黑的森林,比野豬還黑。猛烈的陽光直射在大片雪地上,而他的眼睛熱烈地閃動:
起風了。
現在,我仍然能夠記起那一幕,那片陽光照射下覆雪的坡地,寂靜如宇宙洪荒,但是,起風了。你其實不知道那是風,你只是看到你的腳踏破貞靜的雪,細小的粉塵倉皇地在雪上拂動,奔赴而去,漸漸飛揚,在陽光中旋轉,直到騰空而起,如一只威嚴的、芒羽閃爍的巨鳥。
他沉重的袍襟在風中輕擺,他頑劣地笑了,笑得像汴京街頭的一個潑皮:
這風是咱們兩個惹起來的。
轉過頭去,他望著風去的方向,望著南方:
它就一直這么刮下去,千里萬里,挾著塵土、草屑,還有無數人的唾沫星子,越來越大,越來越臟,刮到汴梁,過了江,刮到臨安,這風撩起了西湖上女子的衣帶……
我永遠不能忘記他的臉,遙望的、痛楚的、怨憤的、自我憐憫的、狹邪的臉。很久之后,我在酒桌上認識了五國城的一個女子,她豐碩、喧鬧,她的酒量遠遠勝過李清照。此前我已久聞其名,該女子曾以第四野戰軍橫掃千軍的氣概喝翻了一個團的臺灣文人,海峽對岸從此聞風膽落。
現在,女子端一只酒碗,目光灼灼:
干了?
那什么,我怯怯地囁嚅:
你們可以為他立個塑像。
她一下子虎目圓睜:
立像,為什么?他又不是毛主席!
可他好歹也是一朝天子,他死在這兒,老頭兒很可憐,他到死都想著回去。
她笑了:
他回去不回去中國人都活到現在了,來,干了再說!
好吧,她也許是對的。我有時也覺得他是可笑的,你擺出那副姿勢給誰看呢?你是天的兒子,在這天邊北溟,徹骨的寒涼還不能讓你安靜下來,你仍不知天地無情,天地無親,那你就在那里,站著吧。
你是誰?
我是一個說謊者。
那一年,我見到維特根斯坦的一個學生。不是劍橋的,是奧地利山區特拉滕巴赫小學的學生,他已經是一個樸實的工人,健壯、肚子碩大,不是你們所熟知的那種精悍的法西斯,而是穩穩地把握著自己有限世界的勞動者。他喝著啤酒,向我說起此事。當年的維特根斯坦老師,他們根本不知道他是一個哲學家,其實即使知道了他們也還是不知道哲學家是干什么的,維老師只是一個維也納富人,有錢,據說非常有錢,人稱維半城,人是好人,但有點怪,當然有錢的人都有點怪。這位維老師,他甚至不喜歡女人,甘愿來到這偏僻的山區,教窮人的孩子讀書。
他都教了什么?
哦,他抱著啤酒杯艱難地想,終于想起來了:
哈!說謊者!一個人,告訴你,我是一個說謊者。這時,你是信不信呢?你如果信了,他的話就是真的,可如果他的話是真的,他在說這話時就不是說謊者,所以,他要真是一個說謊者,他就不應該說我是一個說謊者!
他一口氣說完,捧起啤酒杯咕咚喝了一大口,然后孩子般得意地看著我,似乎等待著老師的表揚。
我想我驚愕的表情已經使他足夠滿足。他垂下眼,忽然嘆了口氣,說:
那時我就知道,他這輩子都不會快活,一個人天天想這種事怎么會快活。所以,我只要告訴自己,這杯啤酒是真的,就這么簡單!
是的,如何做出一個真的陳述,這是無解的邏輯疑難,維特根斯坦把自己放進了這口井里。而僅僅是在井口窺探這個問題就已經讓人感到蝕骨的疲倦。
那一年,維特根斯坦剛從維也納來到特拉滕巴赫,一周后,他給他的朋友羅素——以后他們會翻臉的——寫了一封信,“不久以前,我陷入可怕的沮喪之中,而且厭倦生活。但是現在,我略微覺得有希望了。”
事后看來,這封信中只有一點是確切無疑的,維特根斯坦寫道:這大概是特拉滕巴赫的學校教師第一次給北京的哲學教授寫信。這真是一個邏輯哲學家的謹慎的玩笑,實際上,我確信,這是這個星球上第一次有人從特拉滕巴赫向北京寫信。當時羅素正在北京,正在一群潔凈的、體面的、在后世的想象中如同諸神的中國人的簇擁下高談闊論,我注視著他像個粗壯的金兵一樣吃掉一枚汁水四溢的烤羊寶,同時談論著中國文化的特性,那時我忽然想到,很多中國人日后將只是通過另外一個中國人的轉述和引用想起他,此人名叫王小波,但我估計,王小波對他此刻關于中國的高論一個字都不能贊同。
還有一個人名叫梁鴻,她現在也被一個維特根斯坦的、也是羅素式的問題困擾著。這個問題就是:框子里的命題是假的
這是說謊者悖論的另一種表述。絕頂聰明的曹雪芹對此有過絕妙的概括:假作真時真亦假。
現在,在北京一個嘈雜的集市上——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集市,只不過賣的是書。我和梁鴻坐在低矮的沙發上,面對著來來去去的人,由她的新作《神圣家族》談起,談到書中的吳鎮,城鎮化和縣域治理,她的故鄉,小鎮的孤獨和荒誕,特拉滕巴赫的孤獨或福克納的荒誕……
我感到她很累,我也很累。這同樣是荒誕的:對著一群過客,談論喪失和衰敗。梁鴻是河南人,我甚至在她臉上看到了金人的影子,在1126年,靖康元年,一切取決于跑得快和沒跑掉,徽宗皇帝,他和他治下最卑微的農夫一樣,沒跑掉不是身體不好,是舍不下壇壇罐罐。結果,他失去了故鄉,在極北之地,站在蕭紅和遲子建的地盤上,他站成了一塊望鄉石,而在他的目光盡頭,梁鴻也正在慨嘆故鄉的淪喪。——也許這并不是她的真實意思,但是,鑒于我們大家都認為她應該是這個意思,否則沒法聊天,所以,她正在很累地談論故鄉。
梁鴻的故鄉、徽宗皇帝的故鄉,他們所思的是同一片土地和河流,但卻肯定不是同一個故鄉,就像走過土地的不會是同一雙腳。我們皆為過客。這片中原大地,兩千年來被無情的暴力反反復復地清洗,“白茫茫大地真干凈”,曹雪芹看到了骨子里,看到了最潔白也看到了最黑暗,一代一代人把腳印留在雪地上,然后,等風再起,等雪再下。
也就是說,如果梁鴻想象一個永恒的故鄉,她還必須想象永恒的失落。當你在這片土地上從靖康元年走到2016年,你就知道,無數人的故鄉已一去不返。
故鄉是你的故鄉,是你走過這片土地的那雙鞋,梵高的鞋、海德格爾的鞋、你的鞋,反正不會是他人的鞋。
所以,我很累。正如維特根斯坦很累,他在《邏輯哲學論》里說:“幸福者的世界不同于不幸者的世界”,而他在特拉滕巴赫似乎忘記了他的真理,這個大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為自己是托爾斯泰,正如托爾斯泰以為自己是農民,然后他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狂熱性所支配,結果在特拉滕巴赫待了一年后,小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動搖就暴露無遺,在給羅素的另一封信中,他寫道:
“仍然待在特拉滕巴赫,像以往那樣,被丑惡和卑賤包圍著。我知道,在任何地方,社會底層的人都沒什么用處,但是,這里的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無用,更沒有責任感。”
這時的羅素已從北京回到英國,而令人意外的是,維特根斯坦在發表了這等喪心病狂的反動牢騷之后繼續在奧地利的山區待了七年。在這七年里,他和孩子們相處尚好,而和孩子的父母格格不入。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維特根斯坦公開表示,是的,我有錢,但是我不想要那無聊的錢,然后,據他的傳記作者巴特利說,“建立自己的背景以后,維特根斯坦開始對鄉民期待用錢購買的東西表現漠視,至少漠不關心”。他過著一種“虛飾的貧窮生活”,很多年后,他在維也納帶領裝修隊,為他姐姐建造盤踞整個街區的壯麗大宅,而在這里,在特拉滕巴赫,他卻執意住著又小又破的房子,就在棕鹿酒館隔壁的樓上,當鄉民們在酒館里喝酒快活,大聲喧嘩時,哲學家怒不可遏,沖出來大喊大叫。
我不是在指責維特根斯坦虛偽,我可見識過太多貨真價實的虛偽。維特根斯坦的問題是,他真誠地陷在自己的鞋子里或者井里,如果好好學習馬克思,他就不會“對鄉民期待用錢購買的東西表現漠視”,因為,在他的倫理學、美學和邏輯哲學的底部,還有經濟學,還有人類生活得以運行的堅硬條件和限度,以及在這限度內的人性。在談論他的裝修工程時,他說過:“所有的偉大藝術里面都有一頭野獸:馴服的,……我為特雷格爾建造的房子,產生于極其敏感的耳朵和良好的風度,是偉大理智(或文化)等的表現。但是竭力涌入曠野的原始生活,野性生活——這很缺乏,所以,你可以說這不健康。”
在曠野八年之后,維特根斯坦依然沒能找到那頭馴服的野獸。
梁鴻呢,她也力圖馴服野獸,但她甚至不能確定那頭野獸是否還在。現在,她滿面疲倦地表示:當然,《神圣家族》不是非虛構作品,可能是介于虛構和非虛構之間,如果你稱這本是小說也可以。
也就是說,這里有一個框子:
但框子是空白,至少是曖昧的含混。梁鴻,這位女史,她寫下了十幾萬字,然后,她發現她不能用一個真或假的陳述把框子填滿。
她是一個反過來的維特根斯坦,是一個反過來又調過去的維特根斯坦,一個長大的腳穿不上昔日的鞋的旅人,一個不能確定何者為假也不能確定何者為真而又對此執念不已的陳述者。
寒風吹徹頭顱。是的是頭顱不是腦袋,腦袋是溫暖的,屬于整全的生命,而頭顱,它可以被提在手里,可以投擲出去,可以在地上滾動,可以堅硬、冰冷,作金石之聲。
我站在北京的街頭,冒著五國城的寒風,在等馮唐,滿懷惡毒而甜蜜的期待。這廝一直以為他是這個世界的情人,而世界終于對著他解開了褲襠,現在讓我看看他受驚的臉。
但似乎沒有什么受驚的跡象。喝過幾杯小酒,我的腦袋開始疼,一根筋從右側頭頂直貫枕部,以一種傻逼式的執拗和歡快跳動不休。
疼的痛苦像未知的海
糾纏著我的生活
疼的歡樂像自由的鳥
飛舞在一樹樹的花開
——然后,醉眼朦朧之際,我告訴馮唐,我會用瘦金體給他寫一個扇面,就寫他或泰戈爾那首惹下麻煩的詩,他可以用這把扇子為他那個飛奔的腦袋降溫,以便永遠記住,詩應該是美好的。
那天晚上,在書案前,提筆沉吟,我寫下的卻是那首詞:
宴山亭,北行見杏花
歲剪冰綃,輕疊數重,淡著胭脂勻注。新樣靚妝,艷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問院落凄涼,幾番春暮?
憑寄離恨重重,者雙燕何曾,會認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里有時曾去,無據,和夢里也新來不做。
官家寫完了,瘦金只合官家寫,近千年來,此一體少有人仿,于非闇徒得其表,啟功折戟沉沙,黯然銷了王氣。而官家,筆落處便是鼓瑟吹笙、銀燭煒煌,便一張粗紙也登時金粉熠熠。
官家好字!
官家抬筆一指:
說詩!哪個讓你說字!
好詩!黍離麥秀,哀而不傷,盡得風人之致。
官家很滿意。
但出得門來,我必須解開褲襠,頂著寒風撒一泡熱尿:
你個無可救藥的封建統治階級的敗類!你正被金人像狗一樣牽著一路北去,你的身后,華夏正在沉淪,你的宮殿、你的珍寶,無數的書、無數的畫正在烈焰中焚燒,你的無數臣民正輾轉于溝壑,正在受苦,正在無助地死去,金國的大兵正在你的眼皮底下睡你的女人!
你就不能罵一句我操你姥姥嗎?你該像個真正的老炮兒噴出你的血來,而不是在這兒而剪冰綃、勻胭脂,在這兒做夢和思量!
你是多么優雅啊。你身在荒野,你就在人家的褲襠里茍活著,可你的筆下永遠不會有野獸,你有良好的風度,但你的耳朵是瞎的,你甚至聽不見自己的心跳。
就在昨夜,我站在營帳外,聽見我的君王你在啜泣,你在夢中驚叫和狂叫,在你的夢中,在最深黑的地方,發生了什么?發生了風雪山神廟?發生了怒殺閻婆惜?發生了大鬧飛云浦?發生了一個罪人的懺悔或一個圣人的自責?
也許什么都不曾發生,因為你就是你的主人,你就是你的奴隸。但也許一切都發生了,你心中藏著一個反賊、一頭狂暴野獸,但是,你不能提起筆,只要提起你的筆,筆就會徑自寫去,那優雅微妙的語言就會掠過所有深黑和沉默之地,把你帶到院落凄涼、離恨別愁。
那是被詛咒的語言,在提筆時,你身上附著李后主的陰魂,這被你的祖上用牽機藥毒死的詩人,他讓你在每一片杏花、梅花和桃花和狗尾巴花上看見眼波橫和眼兒媚,讓你身體里綿延著煙雨迷離的江南,你苦苦遙望的江南,你畢生不曾去過的江南。
一尊磁甕。白釉,土色斑駁,狀如立枕,中腰處一口突出,形似喇叭。
猜,這干什么用的?
酒甕?
他指了指那朵喇叭:
這又不是水龍頭,能裝酒嗎?
在下不才,委實不知。
我料你也不知。這便是“地聽”——
哦,地聽。
唐杜佑《通典》中《守拒法》有云:“地聽,于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罌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聰耳者于井中托罌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
但這一尊磁甕并非尋常之罌,應是專為地聽而制,此是宋遼之物,聲納技術已有改良,但它的用法應該仍依唐法。
在深井中,蒙著薄牛皮的喇叭緊貼著井壁,聰耳者附耳于甕頂。
腳步聲,馬蹄聲,大樹傾倒之聲……
我喜歡這井底。回到靖康元年,我愿落在汴梁城內的這口井中,看著井口繁星,看著人馬星座緩緩移過,然后,我的耳朵緊貼甕頂,漸漸地,遠處的聲音、地底的聲音、黑暗最深處的聲音透過薄薄的牛皮,被收納進空虛的甕中,在甕頂回蕩。
我能聽見秋蟄的鳴叫,聽見靜夜里一根樹枝的搖曳,一只狐貍踏碎了一粒露珠。
我能聽見飲泣、嘆息,聽見屠夫被血驚醒,聽見維特根斯坦都難以聽見的聲息,聽見沉默,聽見筆在紙上寫下流利的字跡,聽見紙在火焰中卷曲,聽見我的心和他人之心無語的驚悸,聽見語言所不及的地方、那世界和人心盡頭的荒涼和恐懼……
我摘下我的頭顱,緩緩地,把它放進冰冷的井底。
責任編輯 季亞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