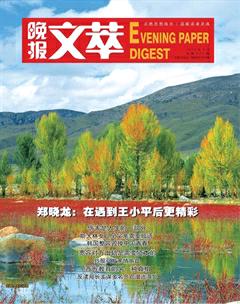民國大師嘲諷前輩
諶旭彬
學(xué)者張中行于20世紀(jì)30年代在北大求學(xué),據(jù)他回憶,當(dāng)時(shí)師長及校方很寬容來自學(xué)生的質(zhì)疑和批評。一次,青年教師俞平伯講蔡邕的詩,其中有“枯桑知天風(fēng),海水知天寒”兩句,俞平伯說“知就是不知”。一個(gè)同學(xué)站起來,問他這樣講有根據(jù)嗎?俞平伯就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出六七種古書中的例子。提問的同學(xué)說“對”,這才坐下。
還有一次,在關(guān)于佛學(xué)問題的討論會上,胡適正講得津津有味,一個(gè)同學(xué)氣沖沖地站起來讓他不要講了:“你說的都是外行話。”胡適說自己在這方面確實(shí)很不行,“不過,讓我講完可以嗎?”在場的入都說,當(dāng)然要講完——因?yàn)檫@是北大的傳統(tǒng):堅(jiān)持己見,也容許別人堅(jiān)持己見。
又一次,對某學(xué)術(shù)問題,某教授和某同學(xué)意見相反,互不相讓。到期末考試時(shí),考題正好就是這個(gè)學(xué)術(shù)問題。這位同學(xué)寫了自己的見解,教授自然判他不及格。按規(guī)定,補(bǔ)考分?jǐn)?shù)要打九折后記入學(xué)分冊,也就是補(bǔ)考得67分才算及格。補(bǔ)考時(shí)'教授又出了那道題,那位同學(xué)也又寫了自己的見解,結(jié)果只得了60分,還要補(bǔ)考。雙方仍不讓步,又是60分。但這次校方算學(xué)生及格,因?yàn)橐?guī)定只說補(bǔ)考打九折,沒有說再補(bǔ)考還要打九折。這位教授違背了北大精神,學(xué)生則維護(hù)了北大精神,于是北大維護(hù)了學(xué)生。
(志成摘自《百家講壇·紅版》2015年12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