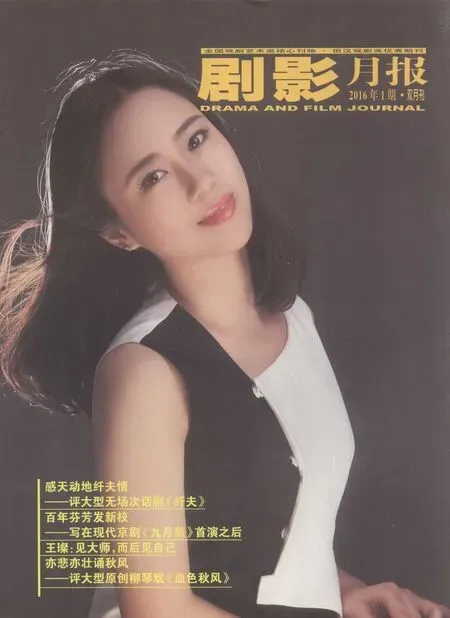說“弓”——淺論二胡右手技巧
■劉文天
?
說“弓”——淺論二胡右手技巧
■劉文天
二胡藝術是弓的藝術,這是我這幾年在舞臺上表演二胡時越來越深的感悟和體會。在任何一首二胡曲中,上至浩瀚磅礴之氣勢,下到強弱疾徐之神韻,無一不是通過弓的豐富變化而得以充實和體現。弓的多變和靈活運用在很大程度上會拓寬,展衍音樂內容的表現范圍。例如在我演奏的《新賽馬》樂曲里,我用超強的快弓演奏連續半音的上行模進,樂曲以激越的音調活靈活現地在聽眾面前展現了一幅萬馬奔騰,相互競賽的歡騰場面。那氣勢、那速度讓人激動,催人奮進,即使是不懂音樂的人,也會被那疾風般的節奏強烈地感染,怦然心動、拍案叫絕。這就是快弓給人傳達的藝術效果。而我在演奏《風神》樂曲時,我在快速律動的伴奏音樂中,讓長弓慢慢展開,使一段優美的旋律扶搖直上,樂音似乎飄忽在無盡蒼穹的云海里,隨著我形體賦予的動感舞姿,讓聽眾產生一種騰云駕霧的特殊的意象。風在宇宙之間飄忽不定,它溫柔時象一個含情脈脈的美麗女孩攙起你的手在曠野中愉悅地奔跑,讓你的心充滿悸動;威嚴時又象一個氣宇軒昂的帝王,不可一世地在天上人間主宰著所有的一切,讓你仰慕、讓你敬畏。這種意象是模糊的、多變的,它引發人的無限遐想,人們根據自己的知識和閱歷,隨著二胡樂曲不斷地向前推進,想象的翅膀騰飛而起,隨著樂音的力度變化,向前伸展、伸展……
傳聲達情、形神兼備。這是現代二胡發展的必然。在形式上由坐姿改為站姿,以至發展為邊拉邊舞邊唱,這就是內容賦予形式的一種深刻的變化,也是當今人們在聽覺和視覺完美統一下的一種企求。但是,無論是哪一種形式,萬變不離其宗,那就是“二胡是用弓拉出來的”。這一個簡單樸素的說法,道破了二胡在最初層次上的關鍵原理,即:磨擦發音。用擦上松香的馬尾弓毛磨擦發出音響。因此,運弓也就是發音的動力,運弓用力的大小,弓速的快慢,直接影響著二胡的表現力。本文從運弓的技巧說開去,探討在各種不同的樂曲和場景下,如何使右手的運弓技巧得以充分的發揮,更好地讓樂曲的內容展示給所眾,這就是“弓”的目的所在。
弓的控制點是右手持弓的大拇指與食指交接處,它握住弓桿,使弓桿平、直、穩地運行,而中指和無名指則是控制弓毛的強、弱及運行方向。演奏外弦時,用中指第一關節處向外頂出,演奏內弦時,用中指和無名指的第一節指面同時合力向里勾住弓毛。運弓的基本要領是:肩部、大臂、肘部、小臂及手指的各部位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既是獨立的又是有內在的密切聯系。不管是拉外弦還是內弦,必須控制弓桿和弓毛的平衡穩定,其中弓毛應貼近琴桿,演奏時力點集中,方向一致,力度均衡,這樣弓的運行暢通無阻,音色、音質都會達到良好的效果。
二胡弓法繁多,變化細微,但總體而言,主要分為四大類,即長弓、短弓、頓弓、跳弓。
長弓:是從弓根到弓尖,也稱全弓。長弓的演奏,從弓根到弓尖,音量要保持均勻,弓速要防止忽快忽慢。從右手的力度控制上來說并不完全一致,從弓根到弓尖,運弓的力度是逐漸增加的,右手越遠離琴筒用力則越大,形成“”型。相反從弓尖到弓根,運弓的力度就逐漸減少,右手越靠近琴筒則用力就越需減少,形成“”型。這種運弓是有意識的加強力量的控制,否則就會造成拉弓強、推弓弱,弓根部強、弓尖部弱的毛病。演奏長弓時,肩部、大臂、肘部、小臂、手腕及手指都要有緊密的配合,充分調動每個部位的轉動作用,以達到弓子在右臂科學力量的支配下,弓毛與琴弦成90°作垂直振動。以此形成一個良好的摩擦接觸,使弓子與琴弦得到充分的振動,從而發出飽滿、純凈的樂音。匈牙利小提琴演奏家卡樂·布萊什曾說過:“運弓技術比左手技巧更為復雜,因為后者手指和琴弦直接接觸而右手則需通過弓桿和弓毛與琴弦的接觸……”由此可見,運弓技術并非簡單,需要通過長時間的嚴格訓練才能真正掌握。
長弓的力度運用及控制是二胡音色和音質的關鍵。推拉力量不均,換弓時雜音頻出;拉長弓時力量浮淺,弓尖部軟弱無力,這都是運弓的力度運用及控制不甚理想所造成的。那么這一問題如何解決呢?通過我自身的練習和演出實踐認識到:二胡運弓的力度主要來自正確的持弓與右臂部的有機配合所生產的力源。你的運弓要想隨心所欲,流暢自然,首先就得有正確的持弓,正確的持弓主要是把握好握弓的三個力點:一是右手大拇指與食指持弓的交接控制點;二是右手中指第一指關節處向外頂出的外力點;三是中指及無名指的第一指面同時合力向里勾住弓毛運行的內力點,這三點是演奏時用來控制力源的主要調節點。只有在三個力點的基點上充分的調動整個右臂部的運弓的積極性,力量才能通過總樞紐的大臂帶動肘部、小臂直達手指的三個力點,使臂部的力量順利的輸送到琴弓及琴弦上,此時右臂的運弓輕松自如、暢通無阻,二胡的音色和音質也松弛流暢、圓潤柔和。
了解了運弓的力源和長弓的運弓技巧,在演奏某一個樂曲或某一個樂段時,在研究弓法的時候,首先要考慮作曲者的意圖。比如二胡曲《月夜》,樂曲中寫長氣息的樂句很多,這是劉天華先生的擅長,但他在樂曲中表現的是一種寧靜的、清瑩的那種環境和氛圍。因此,我們在運弓時要強調弓速的平穩、連續和流暢,切不可在每個音上都要漸強、漸弱俗稱“大肚子弓”。而樂曲《二泉映月》的運弓同樣是長弓為主,但在演奏長于四分音符時,弓的用力輕重有變化,有起有伏,給人以頓挫感,有人稱它為“浪弓”,這里強調的是波浪式的起伏感。樂曲《長城隨想》的第一樂章關山行中的二胡主題,第一個音就是優美而抒情的長音,這一長音的出現,在樂隊“金聲玉振”的古老交響音樂伴奏中,讓人仿佛看到了長城在云霧之中若隱若現的奇偉現象。這一弓,我從心里敬佩地稱它為天下第一弓,因為這一弓的奏出,不僅是對古老雄偉的長城的歌唱,更由于它在連續不斷的展開中又揉進了古琴和京胡的音韻,使獨奏主題的音韻更加突出和動人,以立體式的磅礴的氣勢和熱情贊頌了中國人世世代代為之驕傲的古老長城。
短弓:只用弓子的某一小段或更少一點。它在長弓中可偶爾出現,在快弓中更為多見。它常常是與長弓對比而言。比如說《二泉映月》中的是這一種弓法,它介于快弓和頓弓之間。

它的運弓方法是右手臂明顯地向內靠攏,右手腕的力度適中擺動幅度不易過大,它奏出的音響效果是:發音優美、典雅、純凈,猶如浮云柳絮般令人神往。
快弓是短弓的一種,快弓的好壞涉及到兩手的技術。奏快弓時右手會遇到弓向、力度、里外換弦等方面問題,左手會碰到換把、指序、保留指等方面問題。正確的快弓要求出音飽滿、干凈,極富顆粒性。運弓的手腕動作小而有力,手腕關節放松而又靈活,甩動敏捷,弓毛貼弦,兩手配合緊密,弓段要均勻。
頓弓:用弓極少,發音短促有力,每音之間必須斷開,頓弓有單頓和連頓之分。具體演奏時,首先應將弓毛貼緊弦上,手腕在出音時的動作迅速有力,每一音均需停頓,出音果斷,不拖泥帶水,音質結實飽滿。其中手腕的屈伸動作起主導作用,頂著弓毛的中指、無名指起輔助作用。頓弓的力度是靠手腕的放松和中指、無名指的靈巧托奏結合而成,這兩個環節少一不可。
跳弓,是利用弓毛手腕部的彈力使弓毛彈跳點控制琴弦而發出短促、清脆、明快的聲音。跳弓的類型很多,如拋弓。它是跳弓的一種,大多是用來再現歡快跳躍的情緒。《賽馬》《奔馳在千里草原上》《戰馬奔騰》等不少樂段都多次應用此弓。演奏拋弓時,要注意持弓的松緊變換,提弓時持弓要緊,而往下落(拋)弓撞擊琴弦之后,持弓立即相對放松。同時,要控制好小臂的旋動動作。拋弓一般在外弦演奏比較方便,內弦比較有難度,但如長期反復練習,仍然可達到與外弦同樣的效果。
以上說“弓”,只說了平常我們在演奏中使用的一些常見弓法,這些弓法必須根據樂曲所表現的內容來制定具體的弓法。至于實踐中如何掌握火候,我引用二胡藝術家張銳的幾句話來結束此文:“
持弓不能持太緊,
太緊不會有彈性,
持弓時緊時而松,
松緊之間可‘丟弓’。
‘丟弓’并非弓離手,
‘丟弓’只為手放松,
‘丟弓’手需套住弓,
丟弓’又為巧持弓。
巧持弓,藝無窮,
天籟之音躍蒼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