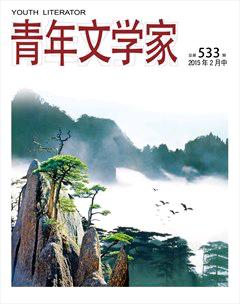“P+的+N”結構中“的”字隱現現象探析
摘 ?要:對于領屬結構中“的”字的隱現規律很多專家學者都做了相關的論述,Haiman提出:領屬關系從不可渡讓到可渡讓是一個連續統.,朱德熙從句法方面進行了解釋,崔西亮試圖從偏項和正項之間的領屬關系是否可以改變來解釋,張敏用距離相似性原則來解釋。但是他們的觀點并未完全消除筆者心中的疑惑,因此試圖在先賢研究的基礎上從句法、語義、認知、文化、社會學等五個方面對“P+的+N”結構中“的”字隱現現象進行分析。
關鍵詞:“P+的+N”“的”字隱現 ?句法 語義 認知 文化 社會學
作者簡介:楊曉宇,女,出生年月:1986年出生,民族:漢,籍貫:黑龍江省鐵力市人,學歷:碩士學歷。工作單位:廣東海洋大學寸金學院,主要研究方向:第二語言教學。
[中圖分類號]:H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05--01
一、“P+的+N”結構的界定
客觀世界中存在物與物之間領有或隸屬的關系,如“鼻子”可以被人具有也可以被牛、馬具有。也就是說,具有或擁有“鼻子”的人、動物處于領有地位,而“鼻子”處于隸屬地位。這種客觀的物與物之間的領屬關系反映到語言中,就形成了表領屬關系的語法結構。本文主要探討的“P+的+N”結構屬于代詞性領屬結構。
二、“P+的+N”結構的組成成分
“P+的+N”結構由兩個語義成分領事和屬事組成。領事是領有者;屬事是被領有者。如“她的手”中,“她”是領事,“手”是屬事。本文把領事標記為P,屬事標記為N。代詞性領屬結構的語義蘊涵式可記作:P領有N或N隸屬于P。
三、代詞性領屬結構的句法形式
漢語中代詞性領屬結構的句法形式主要有下面幾種格式
(1)“P+的+N” ? (2)“P+N”
(3)N+屬于+P ? ?(4)N+是+P+的
(5)N+為+P+所有
其中(1)和(2)是現代漢語表代詞性領屬結構的基本格式。
四、“P+的+N”結構違背相似性原則的分析
Haiman曾經指出:領屬關系從不可渡讓到可渡讓是一個連續統。[1]不可渡讓性從大到小的排序是:身體部位>親屬關系>擁有關系,世界上其他語言似乎都在遵循這個規律,而漢語似有違背。如:
(1)我的眼睛(√)我眼睛(×)
(2)我的爸爸(√)我爸爸(√)
從不可渡讓的程度來說,身體部位應該比親屬關系更具有不可渡讓性,那么為什么(2)中可以省略“的”而(1)中不可以呢?王姝在《漢語領屬構造的可讓渡梯度》一文中,通過大量的數據分析證實可否讓渡是影響漢語領屬構造的一個因素,但它不是一個涇渭分明的強制性編碼原則,領屬構造的次類之間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差異。那么究竟都有哪些因素影響“P+的+N”結構中“的”的隱現,本文將試著予以探討。
五、“P+的+N”結構中“的”字隱現現象及其原因的探討
(一)句法方面
朱德熙指出:人稱代詞做領屬性定語,如果中心語是表示親屬稱謂的名詞,通常不用“的”字,例如“我哥哥”,“他父親”。如果中心語是一般名詞,單說的時候要用“的”字。[2]但是“老板”是一般名詞,我們可以說“我們的老板”,也可以說“我們老板”,因此從句法方面并不能完全解釋“P+的+N”結構中“的”字隱現現象。
(二)語義方面
崔西亮認為人稱代詞做定語的結構中“的”字的隱現,取決于偏項和正項之間的領屬關系是否可以改變,不可改變的,其中的“的”字可以隱去,反之則不能隱去。如:“我”和“父親”之間的關系是不可以改變的,所以可以說“我父親”。“我”和“書”的關系是可以改變的,所以不可以說“我書”。但是張敏指出“我”和“手”之間的關系是不可改變的,但是獨立指稱時我們卻不能說“我手”。
(三)認知方面
張敏試圖用距離相似性原則來解釋,認為偏項和正項之間概念較近的,“的”可以省略。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1.首要條件是能否對應某個具體的專名。例如,“我父親”和“我們老板”可以分別對應“張三”或“李四”,因而可以成立。“我手”、“我書”不能對應某個具體的專名,因而不能成立。2.偏項和正項之間的關系是雙向領屬。例如,“我”可以領有“父親”,“父親”也可以領有“我”,它們之間是雙向領屬,因此可以說“我父親”。但是張文遇到的問題是“他學生”和“他們學生”都可以對應某一專名,內部也都有雙向領屬關系,然而前者獨立指稱可以成立,而后者獨立指稱時合格度則較低。因此,距離相似性原則也不能完全解釋“P+的+N”結構中“的”字隱現現象。
沈陽、陸儉明用典型性原則來解釋“P+的+N”結構中“的”字隱現現象:既可以說“他的父親”,也可以說“他父親”,原因就在于“他”和“父親”的領屬關系比較典型或比較緊密。反之就只能說“他的衣服”,不大能說“他衣服”,原因也就在于“他”和“衣服”的領屬關系不太典型或不夠緊密。[3]
(四)社會學方面
從社會學方面來說,中國社會是一個關系社會,相對于身體部位和一般物品來說,中國人似乎對人際關系傾注更多的心力。這種心理認知從某種層面上也反映在了語言中,那么“我爸爸”比“我眼睛”、“我書”更具有獨立指稱性的現象也就可以理解了。
六、結語
“P+的+N”結構中“的”字隱現現象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本文著重從句法、語義、認知、文化、社會學五個方面對“P+的+N”結構中“的”字隱現現象給予分析,這些因素在不同情況下它們所起的作用不盡相同,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參考文獻:
[1] Haiman, 1985b. Diagrammatic iconicity in stem- inflection relations. 11- 47.
[2] 朱德熙:《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3] 沈陽,陸儉明:《漢語和漢語研究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