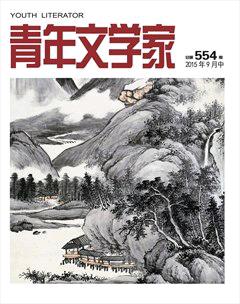想像“中國”
陳若谷
摘 要:中國一直致力于實現國家形象的重建和掌握文化發言權,由此生發一系列的話語推進。文化價值也許是我們可以借助的一個立足點,但是此一價值體現在文學文化實踐中仍舊相當模糊和曖昧,我們仍然面臨著難以獨立訴說自己和面對國際消費圖景沖擊的尷尬和無奈。
關鍵詞:全球化;中國;消費化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26-13-02
全球化的文化沖突和交匯是建立在文化主體的基礎上,湯因比為解釋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產生、發展提出“挑戰與回應”的理論。每個民族的文化就是該民族對其所生成環境所作的挑戰的一種回應[1]。長久以來,世界(幾乎特指西方)和中國關系框架就是走進與疏離,我們曾經抗拒的是一種西方秩序,而如今追求的也是那些所謂普適性原則,其源頭實則來源于西方自身的特殊或主體性。
20世紀末以來,我們憑借舉國體制一次一次地向世界呈現了新中國不容忽視的經濟政治實力。甚至在認同“becoming yellow”的前提下制造了諸多黃種人的光榮。尋找中國在全球化進程的特殊位置,是中國話語中最強勁的聲音。如安東尼?吉登斯指出的那樣,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意識更多地是在面對外部侵入力量的高壓和現代性逼迫之下形成的。這種民族國家意識完全在文化想象中得以推進。那么,我們不得不問,作為一個后發現代型國家,中國何時建立起過自身的主體性?是逐漸增加民族認同的今天,還是在久遠的前現代社會?考察這個問題固然需要宏大的歷史眼光,我們暫時只著眼于眼下的文化實踐。
近30年,文化界一直著力于重述中國經驗,尋找本土文化策略,乃至描述中國夢。我們經歷過“尋根”,經歷了“國學熱”,也正在經歷對于“斷裂”說的質疑和對傳統文化“延續性”的證明。
然而,中國要把本身的普遍性再一次敘述出來,首先要經過一個內部的“去特殊化”,要讓那種普遍性的價值能為別人認同。這并不是說,面對全球化和種種普遍性價值論述,我們必須為自己找到一種特殊性;恰恰相反,它要求我們介入和參與對普遍性問題的討論和界定中去,最終為當代中國內在的普遍性價值找到理論上的表述。而這一次,我們找到的文化背景是,消費。
如果說“文化的經濟化”指的是資本的徹底性,更多地帶有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色彩,那么“經濟的文化化”則揭示的是商品生產的當代特征。馬爾庫塞已經在《單向度的人》中揭示過此變化趨勢,杰姆遜則表述得更集中:“在這種意義上,經濟變成了一個文化問題……現在我們必須補充的是,今天的物化也是一種美學化——商品現在也以‘審美的方式消費。”[2]“消費”不再是一種次要的和附帶的行為,它本身就成了人生的重要目的。生產和勞動已經被視為消費的條件,而不是生存的目的。消費的主導性不僅僅合法化了對于物質的追求,而且將文化的消費也合法化了。
在這樣的進程之中,全球化帶來的深刻的文化后果業已徹底改變了中國文化想象的走向。中等收入人群由于掌握了話語的權力,他們對于生活和價值的想象影響了“我們”這個整體的文化表達。“中產階級文學又以特殊的形象符號描繪了中產階級時代的價值觀念、思想感受和心理情緒。它已經走出了‘理論預設和‘文學想象的階段,變成了一個文學閱讀的事實。”[3]
電影《小時代》里對上海的勾畫是通過弄堂女孩林蕭一次次的仰望完成的,她仰望的對象有好朋友顧里,她一次次地為朋友們提供物質與智力上的援助;還有老板宮洺,他具有非凡的品味和巨大的財富,而他父親的公司是美國駐中國的三大跨國企業之一。林蕭則家境一般,甚至連宮洺一只水杯的價錢都無力支付。林蕭不再是可以經歷痛苦和磨難后獲得成長的女孩,她只是一個在國際化大都市中,在一群新貴的夾縫中求生存的青年而已。《小時代》展現的是所謂上流社會的生存景況,也是城市消費圖景的一個側影。用福柯知識考古學的觀念看來,展現的對象不是那么重要,而在于這場上海都市“秀”產生的背景。郭敬明完全就是我們時代的勵志故事,無論是他個人的世俗化成功,還是他為飲食男女勾勒的優渥生活,都是每個人渴望觸摸的美好圖景。郭敬明身上的各種現象當然可以被轄制在大眾文化的圖譜中加以分析和批判,說他只是消費時代運時而動的弄潮兒。但更具有深意的是,他自己在采訪中直言不諱:公眾選擇《小時代》,不選擇賈樟柯,是民族文化審美問題。這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本土想象之無效而世界消費想象大行其道。
上海,關于它的文化書寫充斥著霓虹、洋場、舞廳,其實本世紀起最早的上海就是通過“懷舊”來建立自己的歷史意識的,并且一步一步走向今天的“世界主義”,這種“世界主義”正好是全球化語境的現代中國的新象征。李歐梵指出:“西方旅行者給她的一個流行稱渭是‘東方巴黎。撇開這個名稱的‘東方主義含義,所謂‘東方巴黎還是證實了上海的國際意義。”[4]這種歷史意識正是試圖將所謂上海的“世界主義”直接接上全球化的強烈的沖動,一種新的歷史觀在全球化時代突然伴隨著全球資本的降臨而合法化了。他們似乎通過這樣的歷史意識將自己的歷史成功地轉化為全球化時代的消費品。
也正是上述前提下,閻連科的《日光流年》如同一個惡托邦,生生將全球化給民族文化的美好允諾擊穿。三姓村獨立于現代社會,默默潛藏在耙耬山脈深處,因為痼疾對于生命的壓抑,村民們執著地走在求生存的道路上,他們前仆后繼鑿渠引水。然而,他們最后得知的真相是,日夜思念的靈隱河早已變成了城市的下水道——城市的生活用水和商業用水早已將其污染。引進這條臟水河,不僅不可能治病,還斬斷了幾代三姓村人的希冀。
全球化的“市場”概念更多地表述了“解放”的涵義,它意味著一種公正和自由,“某些時候,市場的權力關系以及產生的利潤可能得到民族國家的認可與分享——前者并未形成瓦解后者的威脅。如同德里克觀察到的那樣,一些第三世界的民族國家并沒有對跨國資本表示敵意,相反,它們更樂于為全球主義的來臨提供方便。”[5]但是當真正的國際大市場近在眼前地向我們敞開胸懷,“世界是平的”的美好景象倏忽消失不見了。全球化的一些預設,很難一跨腳就可以將其踏平。比如有一個經典的“民族”概念是這樣被創造出來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卻不知這說法本身已經包含一個價值等級差異:因為有“世界”的最終所指,所以“民族”才有存在的價值。此外,民族的價值在這個時代又是如何呈現的呢?湘西印象、大理印象、烏鎮印象……一系列的富有地域特色的旅游策劃最后都在用旅游帶來的財政收入進行評比,剩下貧瘠的“印象”二字供人揣測。
我們始終無法繞過這樣的疑問:全球化的書寫為第三世界國家留下了什么余地和空間?關于第三世界的文化特征,杰姆遜提出了“民族寓言”的說法。他所關注的“民族寓言”之中包含了第一世界文化的價值觀所忽略的內涵:“這些文化在許多顯著的地方處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國主義進行的生死搏斗之中”。他們的作品之中,“關于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沖擊的寓言。”[6]展示個體的命運和現代化的都市不難,而在全球化消費主義的圖景下涵括“中國”作為一個主體的價值立場則是失敗的。我們才反省說要“從中國發現歷史”,才擺脫了中西二元對立的自我他者化眼光,就又一次陷入了“消費主義”的泥淖。在這個固定的“結構”之中,我們不禁要問,我們的文學表達和文化實踐中,“中國”在哪兒呢?的確,他已經變得難以想像,所以我們只有返身“歷史”——這正是當下許多作家與導演的選擇。
杜威.佛克馬說:“文學閱讀將使我們克服文化障礙,它使我們變成具有參與意識的觀察者”[7]在這個意義上,文化想象通常是我們確立自身的必經步驟,也說明正是在問題中蘊含著解決的動力。
注釋:
[1][英]湯因比.歷史研究(上)[M]. 曹未風,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王逢振,譯.全球化和政治策略[J].江西社會科學.2004,(3):193.
[3]程光煒.中產階級時代的文學[J]. 花城,2002,(6):198.
[4][美]李歐梵.上海摩登[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319-351.
[5]南帆.全球化與想象的可能[J].文學評論,2000,(2):98.
[6]弗雷德里克.杰姆遜《處于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載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234-235.
[7][荷]杜威 佛克馬.王寧,譯.走向新世界主義[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8,(6):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