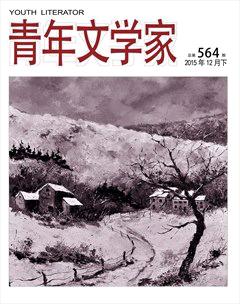人性的沉淪與救贖:試論《九三年》與《雙城記》的主題
摘 要:《雙城記》和《九三年》分別是狄更斯和雨果晚期的作品,兩位作家以法國(guó)大革命時(shí)期激烈殘酷的革命斗爭(zhēng)為背景,對(duì)極端環(huán)境下人性的復(fù)雜性予以剖析,刻畫(huà)了朗特納克、郭文、馬內(nèi)特、卡頓等一系列鮮明的人物形象,借由他們從人性的沉淪走向救贖的命運(yùn),發(fā)出了人道主義的吶喊,表達(dá)了對(duì)至純至真的人性的呼喚和贊美。
關(guān)鍵詞:《九三年》;《雙城記》;人性;救贖;人道主義
作者簡(jiǎn)介:杜丹,女,1990年7月出生,畢業(yè)于南京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目前為陜西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比較文學(xué)與世界文學(xué)專(zhuān)業(yè)在讀碩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lèi)號(hào)]:I1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139(2015)-36-0-05
《九三年》和《雙城記》分別是雨果和狄更斯以法國(guó)大革命為背景創(chuàng)作的小說(shuō)。兩部作品生動(dòng)地表現(xiàn)了黑暗的貴族統(tǒng)治和受迫害的下層人民之間的尖銳沖突,揭示出法國(guó)大革命爆發(fā)的歷史根源,表達(dá)了他們對(duì)歷史的反思;另一方面兩部作品從人道主義立場(chǎng)出發(fā),反對(duì)大革命過(guò)程中過(guò)度的暴力和血腥,前者強(qiáng)調(diào)無(wú)階級(jí)的人道主義,把人道主義看做人類(lèi)最高的理想;后者則以愛(ài)與溫情、無(wú)私奉獻(xiàn)為核心,提出階級(jí)調(diào)和的主張。作家把自身對(duì)于人性的思考貫穿在人物的命運(yùn)中,使筆下的人物在極端的復(fù)雜的環(huán)境下面對(duì)人性的拷問(wèn),作出艱難的選擇,從人性的沉淪中走向救贖,最終回歸到人道主義精神的道路上。
一
雨果和狄更斯對(duì)法國(guó)大革命擁有相同的基本態(tài)度。在小說(shuō)中,他們都深入描寫(xiě)到黑暗的貴族統(tǒng)治和受迫害的下層人民之間尖銳的沖突,表達(dá)出對(duì)下層人民的深切同情,肯定法國(guó)大革命爆發(fā)的歷史必然性。
1793年是法國(guó)革命與國(guó)內(nèi)外反革命勢(shì)力斗爭(zhēng)最嚴(yán)峻的一年。法國(guó)保王黨巢穴——旺岱省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叛亂,這年六月建立起的雅各賓派專(zhuān)政采取有力措施,實(shí)施紅色恐怖政權(quán),于七月派軍隊(duì)鎮(zhèn)壓叛亂,《九三年》正是以這一歷史時(shí)期為背景展開(kāi)敘述。
作品一開(kāi)始便肯定了人民革命的正義性。在一片陰森的樹(shù)林里共和軍正在搜索敵軍,林子深處有一個(gè)奇怪的女人,她穿著單薄,袒露半邊乳房,擁著三個(gè)年幼的孩子傻傻地坐在樹(shù)下。很快農(nóng)婦被發(fā)現(xiàn)了,在與幾個(gè)軍人對(duì)話時(shí)我們知曉了她極其凄慘的經(jīng)歷:她的丈夫戰(zhàn)死,因?yàn)轭I(lǐng)主需要他作戰(zhàn);她的父親因?yàn)楂C了一只兔子變成殘廢,還要感激爵爺開(kāi)恩賞他一百棍子而沒(méi)有判死刑;她的公公為謀生計(jì)販私鹽被絞死,只因?yàn)槭菄?guó)王的命令;她的祖父被關(guān)到船上做苦工,只因?yàn)槭莻€(gè)新教徒;而這婦女還有三個(gè)嗷嗷待哺的孩子,她只能帶著他們?cè)趹?zhàn)火紛飛中逃難。人們同情這個(gè)女人更仇視造成這一切的罪魁禍?zhǔn)住F族和國(guó)王,腐朽的社會(huì),黑暗的政權(quán)。農(nóng)婦的形象折射出法國(guó)社會(huì)的黑暗現(xiàn)狀,人民長(zhǎng)期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貴族統(tǒng)治的專(zhuān)橫無(wú)道,過(guò)于深重的苦難終將使人民奮起反抗,人民進(jìn)行革命是正義的,是必然的。
與雨果所持的基本態(tài)度一致,狄更斯也認(rèn)為法國(guó)大革命是一場(chǎng)無(wú)法避免的革命運(yùn)動(dòng)。在《雙城記》里,作家以巴黎和倫敦為主要場(chǎng)景,著重表現(xiàn)了法國(guó)社會(huì)的黑暗統(tǒng)治和人民深重災(zāi)難的多個(gè)側(cè)面:貴族的典型代表埃弗雷蒙德侯爵張揚(yáng)跋扈,他的馬車(chē)撞死無(wú)辜的小孩,他卻無(wú)動(dòng)于衷,揚(yáng)長(zhǎng)而去;他年輕時(shí)霸占農(nóng)家婦女,為達(dá)目的逼死她全家;了解事情經(jīng)過(guò)的馬內(nèi)特醫(yī)生為伸張正義寫(xiě)信揭發(fā)他的罪行,不料信被侯爵截獲,馬內(nèi)特因此被囚禁在巴士底獄十八年;德法日夫人是當(dāng)年慘死的農(nóng)婦的妹妹,她將仇恨暗藏在心里,把貴族多年來(lái)的暴行一一編織記錄起來(lái),等待著復(fù)仇的機(jī)會(huì);與德伐日太太類(lèi)似的廣大工人農(nóng)民也都早已對(duì)貴族統(tǒng)治到了忍無(wú)可忍的境地,他們每日都懷著滿腔仇恨,緊咬著牙關(guān),只等待一個(gè)爆發(fā)的時(shí)刻。山雨欲來(lái)風(fēng)滿樓,復(fù)仇之花已經(jīng)在階級(jí)仇恨的溫床上悄然發(fā)芽,貴族的專(zhuān)制荒淫和人民飽受的苦難為大革命找到了合理性和必然性。
二
但是雨果和狄更斯都是人道主義者,在肯定人民反抗黑暗統(tǒng)治的同時(shí),他們也看到了大革命的殘酷和暴力,革命的勝利不是人道主義的勝利,相反,以暴制暴帶來(lái)的是新一場(chǎng)血雨腥風(fēng)。作家把目光轉(zhuǎn)向在極端的斗爭(zhēng)環(huán)境中暴露出的人性弱點(diǎn),使得筆下的人物們充滿矛盾性,他們的命運(yùn)軌跡正是人性中善的一面和惡的一面的交戰(zhàn)。
雨果在《九三年》中塑造了朗特納克這個(gè)集惡與善于一身的形象。叛黨領(lǐng)導(dǎo)人——親王朗特納克在旺岱執(zhí)行秘密任務(wù)時(shí)被革命黨抓獲,但是他卻在緊要關(guān)頭放棄絕佳的逃跑機(jī)會(huì),不顧生命危險(xiǎn)在大火中沖回碉堡救下三個(gè)命在旦夕的孩子。雨果在小說(shuō)中并沒(méi)有詳細(xì)描寫(xiě)朗特納克之前是一個(gè)怎樣的人,但是通過(guò)小說(shuō)中人物出場(chǎng)時(shí)蕭殺陰冷的環(huán)境描寫(xiě),以及寥寥幾筆革命者對(duì)這個(gè)叛黨頭子的深?lèi)和唇^,讀者不難在潛文本中為朗特納克安上狠毒,冷酷等等貶義的標(biāo)簽。雨果將這樣的人物置于生死面前,著墨于他在極端環(huán)境下的抉擇,他做了與自己的身份和一貫作風(fēng)大相徑庭的決定,放棄逃生而救孩子。那一刻“魔鬼身上的上帝”[1]蘇醒了,孩子的純真喚醒了朗特納克人性中善的力量,使一個(gè)心狠手辣的人做出了舍己救人的壯舉。在昏暗的地牢中,孩子純潔的心靈凈化了朗特納克心中的惡,這一場(chǎng)大火仿佛燒毀了人間的罪惡,使朗特納克浴火重生,從人性的沉淪走向被孩子救贖和自我救贖的路程。
作家接著把一個(gè)難題拋給小說(shuō)的主人公即革命者郭文,應(yīng)不應(yīng)該殺朗特納克?郭文在沉思:
“人們?cè)鯓愚k呢?”
“接受他的頭顱。”
“朗特納克侯爵要在別人的生命和他自己的生命之間做一個(gè)選擇,在這個(gè)莊嚴(yán)的選擇中,他選擇了自己的死亡。”[2]
于是郭文很快對(duì)革命產(chǎn)生了懷疑:
“對(duì)于英雄的行為,這是怎么樣的一種報(bào)酬啊!用一種野蠻的手段去回答一種慷慨的行為!革命居然也有這種弱點(diǎn)!”
“正當(dāng)這個(gè)充滿著成見(jiàn)和奴役思想的人突然轉(zhuǎn)變,回到人道主義圈子里來(lái)的時(shí)候,那些為了解放和自由而戰(zhàn)斗的人們卻仍然繼續(xù)內(nèi)戰(zhàn),仍然維持流血和兄弟自相殘殺的常規(guī)!”[3]
他的這番激烈的內(nèi)心斗爭(zhēng)表明:郭文是一個(gè)戰(zhàn)士,但更是一個(gè)人道主義者。他覺(jué)得革命的方式不應(yīng)該是野蠻的,殘暴的,革命不是為了抹殺人性,而是為了建立一個(gè)充滿愛(ài)和自由的國(guó)家。最本真的人性是美與善的化身,卻常常被世俗的斗爭(zhēng)深深掩埋,往往經(jīng)歷了最嚴(yán)峻的考驗(yàn)才得以重現(xiàn)。雨果就是要一次又一次在生死關(guān)頭拷問(wèn)人性,讓人物作出選擇。郭文不愿礙于革命者的身份,違背內(nèi)心,處決這個(gè)舍己救人的英雄,在革命與人道主義之間,他選擇了人道主義,最終放走了朗特納克,甘心用自己的頭顱換取侯爵的生命,人性的偉大在這一刻彰顯。小說(shuō)中的另一位革命者西穆?tīng)柕鞘枪男r(shí)候的家庭教師,對(duì)他有著深厚的感情,但是為了維護(hù)革命“絕不放過(guò),絕不寬恕”的鐵紀(jì),他選擇了絕對(duì)的革命道路,卻又在郭文死后悲痛萬(wàn)分,開(kāi)槍自殺。他的矛盾和痛苦最終通過(guò)死得到了救贖。小說(shuō)中反復(fù)提到“在絕對(duì)的革命之上還有絕對(duì)正確的人道主義”[4],在這里正確的人道主義也就是指革命不能違背天理、人性,如果為了反抗非人道的統(tǒng)治而使用非人道的革命手段,革命就不再具有正義性,就會(huì)淪為被人道精神討伐的對(duì)象。“丑惡的人類(lèi)法律不得不在永恒的美麗面前現(xiàn)出原形”[5],只有人性的美與善才是永恒的美麗,三個(gè)人物在生死面前的選擇凸顯出一條真理:用人性中善的一面來(lái)化解罪惡,恕字,才是人類(lèi)最美好的字眼。
同樣的,狄更斯在《雙城記》中也表達(dá)了贊美人性和人道主義精神的主題。 “如用相似的大錘,再次把人性砸變形,它就會(huì)扭曲成同樣歪曲的形象。如再次中下肆意掠奪和壓迫的種子,物從其類(lèi),也必然結(jié)出同樣的惡果。”[6]受黑暗統(tǒng)治的人民值得同情,但是失去理性的狂暴已經(jīng)扭曲了他們本來(lái)的面目,復(fù)仇太過(guò)狂熱,被勝利者煽動(dòng),變成了階級(jí)報(bào)復(fù)的偏激情緒,革命變成濫施暴力,人性被踐踏。
小說(shuō)中描寫(xiě)道那個(gè)年月,沒(méi)有法律和公正可言。法官審犯人只憑一條原則:凡是和貴族沾上一點(diǎn)邊的都要被處死。陪審席上坐著的是一群狂熱分子,他們有的喝得爛醉,有的昏昏欲睡,只有聽(tīng)到要給犯人判死刑的時(shí)候才會(huì)亢奮起來(lái)。窮苦的縫工本該屬于這場(chǎng)革命中獲利的一方,但是卻被安上搞陰謀的罪名判處死刑。達(dá)奈雖然是埃弗雷蒙德侯爵的侄子,但早就脫離家族在英國(guó)自力更生,并沒(méi)有做過(guò)任何壞事,是一個(gè)待人友好,正直的青年,卻連審問(wèn)都不用就抓進(jìn)監(jiān)獄。 狄更斯在這里重點(diǎn)描寫(xiě)了德法日一家與馬內(nèi)特一家的糾葛。對(duì)于在監(jiān)獄關(guān)押十八年后終獲重生的馬內(nèi)特而言,女兒露西是他唯一的寄托,看到達(dá)奈和露西有情人終成眷屬,他感到無(wú)比的幸福。可是“復(fù)仇女神”德法日太太一直像一團(tuán)陰影籠罩在這個(gè)多災(zāi)多難的家庭上空,她始終不肯放過(guò)達(dá)奈,定要將他致死才罷休,甚至對(duì)于無(wú)辜的露西也要趕盡殺絕。為了凸顯她的喪心病狂,小說(shuō)中描寫(xiě)了德伐日太太獨(dú)特的趣味即“看殺頭”:她毫無(wú)同情心,絕對(duì)不會(huì)錯(cuò)過(guò)任何一場(chǎng)砍頭的“盛宴”,總是坐在砍頭的臺(tái)子下面一邊編織一邊“欣賞”,看到殺人流血的畫(huà)面無(wú)比興奮,享受著復(fù)仇的快感,又把更惡毒的復(fù)仇詭計(jì)編織進(jìn)新作中。以德伐日為代表的下層人民對(duì)貴族抱有深仇大恨,日漸喪失了人之為人最基本的同情心、愛(ài)心、悲憫之心,他們從反抗走向人性的沉淪,陷入了更深的泥沼。
三
雨果在創(chuàng)作《九三年》時(shí),剛剛經(jīng)歷了流亡生涯回到闊別已久的祖國(guó),但是等待作家的是普法戰(zhàn)爭(zhēng)的悲慘禍端和巴黎公社成員的浴血奮斗,這給以作家直接的刺激。作為一個(gè)徹底的人道主義者,雨果只能在某種程度上認(rèn)可革命,但隨著革命斗爭(zhēng)逐漸殘酷激烈,他開(kāi)始無(wú)法接受革命的嚴(yán)峻現(xiàn)實(shí)。雨果把人道主義看作是人類(lèi)最高的信仰,“在絕對(duì)的革命之上還有絕對(duì)正確的人道主義。”[7]在此基礎(chǔ)上他提出的人道主義觀點(diǎn)是超階級(jí)的,無(wú)論是貴族朗特納克還是革命者郭文,西穆?tīng)柕牵麄冏罱K都超出了自身的階級(jí)立場(chǎng),歸于無(wú)階級(jí)的人道主義的圈子。小說(shuō)這樣描寫(xiě)到朗特納克侯爵救出三個(gè)小孩時(shí)的情景:那一刻“魔鬼身上的上帝”[8]蘇醒了,爵爺?shù)男蜗箢D時(shí)變得高大起來(lái),“他用一瞥高傲的眼光,使他面前的幾個(gè)工兵讓開(kāi)路來(lái)”[9],雖然侯爵叫著“國(guó)王萬(wàn)歲”,共和軍叫著“共和國(guó)萬(wàn)歲”,但是“你愛(ài)叫什么就叫什么,你高興說(shuō)什么廢話就說(shuō)什么廢話,你就是善良的上帝。”[10]在雨果看來(lái)無(wú)論是叛軍還是革命黨,只要是作出人道主義義舉的都是偉大的人,人道主義既可以征服叛軍也可以征服革命黨,甚至能在那一刻,使彼此忘記自身的階級(jí)身份,共同接受人道主義的救贖。
雨果所強(qiáng)調(diào)的超階級(jí)的人道主義能通過(guò)乞丐泰爾馬克得到充分表現(xiàn)。泰爾馬克的形象一直備受爭(zhēng)議,有人認(rèn)為他無(wú)知地放走了親王,導(dǎo)致后來(lái)一系列慘劇的發(fā)生,他代表了當(dāng)時(shí)法國(guó)農(nóng)村的愚昧和落后,正是這些人給貴族的統(tǒng)治和反撲提供了契機(jī)。然而當(dāng)我們回顧小說(shuō)內(nèi)容時(shí),雨果描寫(xiě)到作為乞丐的泰爾馬克救親王是為了報(bào)答一飯之恩,并不是無(wú)知或愚蠢,一個(gè)乞丐尚且知道滴水之恩涌泉相報(bào)的道理。
乞丐和親王接下來(lái)的對(duì)話意味深長(zhǎng):
“為什么救我?”
“這個(gè)人比我還窮,我有權(quán)呼吸,而他連這也沒(méi)有。”
“我們現(xiàn)在是兄弟了,老爺,我乞討面包,你乞討生命。我們是兩個(gè)乞丐。”[11]
在雨果眼中一個(gè)身份卑賤的人有權(quán)利站在崇高的人道主義立場(chǎng)對(duì)所有人一視同仁,憐憫所有受苦受難的人,不因他是革命軍或是保王黨另眼看待,僅僅是作為一個(gè)人對(duì)另一個(gè)人的人道主義關(guān)懷,在人道主義面前,一個(gè)乞丐和一個(gè)親王是平等的,是兄弟。
小說(shuō)還描寫(xiě)到乞丐送走親王時(shí)鄭重其事的一番話:
“我是在救您,但我有一個(gè)條件”,
“您來(lái)這里不是為了作惡。”[12]
乞丐救人是有原則的,這原則不是根據(jù)政治身份而劃分,而是根據(jù)為惡還是為善的人道主義。當(dāng)他發(fā)現(xiàn)村落被燒毀,對(duì)放走爵爺一事追悔莫及,也不是因?yàn)楹蠡诜抛吡艘粋€(gè)貴族叛黨,而是后悔放走了一個(gè)做下惡事的人。雨果堅(jiān)持認(rèn)為,在人道主義面前,只有超階級(jí)的善和惡,不因政治立場(chǎng)減輕或加重人的罪行。在人道主義面前,約定俗成的法律,政治立場(chǎng),邏輯判斷上的對(duì)與錯(cuò)都變得模糊不見(jiàn),都是渺小的,只有人道主義精神是宇宙間最高的準(zhǔn)則,正如乞丐對(duì)親王所在做那樣,人人都應(yīng)該踐行“強(qiáng)者對(duì)弱者,安全的人對(duì)遇難的人應(yīng)盡的保護(hù)和救助責(zé)任”。[13]
與雨果強(qiáng)調(diào)超階級(jí)的人道主義不同,狄更斯的人道主義旨?xì)w于兩個(gè)方面:一是反對(duì)冷漠的金錢(qián)社會(huì),喚醒以溫情與愛(ài)為核心的人道力量;二是反對(duì)當(dāng)時(shí)自私自利的社會(huì)詬病,推崇自我犧牲,自我奉獻(xiàn)的精神。筆者認(rèn)為這與作家所處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和個(gè)人經(jīng)歷都有一定關(guān)系。
《雙城記》創(chuàng)作的年代,英國(guó)經(jīng)歷了工業(yè)革命,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高度發(fā)達(dá),成為“世界工廠”。“那是英國(guó)歷史上最繁榮的時(shí)代,也是最黑暗的時(shí)代,英國(guó)是世界上最發(fā)達(dá)的國(guó)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貧民窟。”[14]巨大的貧富差距帶來(lái)尖銳的沖突,終于在十九世紀(jì)三十年代爆發(fā)了轟轟烈烈的憲章運(yùn)動(dòng),在十年間經(jīng)歷了三次高潮。但是,與雨果的創(chuàng)作動(dòng)機(jī)不同,狄更斯在創(chuàng)作小說(shuō)時(shí),憲章運(yùn)動(dòng)已被鎮(zhèn)壓,他并不像雨果那樣直接面對(duì)革命斗爭(zhēng)的殘酷和血腥,作家更能切身體會(huì)到的是英國(guó)人在資本主義工業(yè)文明的侵染下如何唯利是圖,人們自私冷漠,心腸堅(jiān)硬,精于算計(jì),就連親情愛(ài)情都被打上金錢(qián)的烙印。另一方面作者自身家庭環(huán)境所帶來(lái)的成長(zhǎng)經(jīng)歷以及個(gè)人愛(ài)情經(jīng)歷對(duì)其創(chuàng)作也有一定影響:兒時(shí),狄更斯勤奮好學(xué),總是一個(gè)人靜靜地坐在閣樓里或樹(shù)下看書(shū),在瘦弱的身體里包裹著的是一顆有著強(qiáng)烈自尊,對(duì)知識(shí)充滿熱望的心。但是他的父親不久后便因?yàn)榍穫魂P(guān)進(jìn)負(fù)債人監(jiān)獄,因?yàn)槿バ蛷S做工可以每星期給家里掙七個(gè)便士,母親執(zhí)意要他退學(xué)去。為了七個(gè)便士母親便抹殺了他受教育的機(jī)會(huì),家里的親戚也沒(méi)有一個(gè)愿意幫忙,甚至沒(méi)有人站出來(lái)說(shuō)一兩句憐愛(ài)的話。對(duì)此,狄更斯的心里是怨恨的是失望的。青年時(shí),狄更斯做過(guò)法律機(jī)構(gòu)的記錄員,記者等工作,接觸到社會(huì)陰暗的方方面面,參與了無(wú)數(shù)離婚案件和財(cái)產(chǎn)案件,目睹人們?yōu)榱藸?zhēng)奪財(cái)產(chǎn)變得無(wú)情無(wú)義。這使狄更斯對(duì)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冷漠無(wú)情有一種深切體會(huì)。因此,“對(duì)人與人之間溫情的缺失感一生都滲在狄更斯的骨子里”,[15]人性的自私,親情的淡漠,社會(huì)的利己主義風(fēng)氣都成為他批判的對(duì)象,與之相對(duì)的,愛(ài)與溫情,自我犧牲和無(wú)私奉獻(xiàn)則備受作家推崇。
《雙城記》中馬內(nèi)特醫(yī)生在監(jiān)獄里度過(guò)了十八年,失去人身自由,整日無(wú)事可做只能面對(duì)著監(jiān)獄的墻,為了保留最后一絲神智,他主動(dòng)要求在牢房里做鞋,終日不停地縫鞋成了漫漫長(zhǎng)日里唯一可干的事;由于長(zhǎng)期無(wú)人交流,醫(yī)生幾乎喪失了正常說(shuō)話的能力;多年來(lái)住在暗無(wú)天日的地方使原本健康的身體變得孱弱不堪。那對(duì)醫(yī)生來(lái)說(shuō)是一段生不如死的日子,埃弗雷蒙德侯爵就是造成這一切的罪魁禍?zhǔn)住5菫榱伺畠旱男腋at(yī)生卻能默默承受心靈的壓力和痛苦,明知達(dá)奈就是仇人的侄子卻依然同意他和愛(ài)女結(jié)婚,這是偉大的父愛(ài),是童年的狄更斯渴望而不可得的感情。善良的洛里先生同情朋友的遭遇,盡心盡職責(zé)地替朋友守護(hù)唯一的女兒露西,不離不棄;當(dāng)?shù)弥R內(nèi)特醫(yī)生獲釋的消息,匆忙從倫敦感到巴黎接回老友,對(duì)神志不清的病弱的馬內(nèi)特悉心照顧;當(dāng)革命黨抓住達(dá)奈,繼而要對(duì)馬內(nèi)特和他的女兒下毒手時(shí),又不顧危險(xiǎn)幫助馬內(nèi)特一家從巴黎逃出來(lái)。這是友情的真摯和無(wú)私。卡頓對(duì)露西的愛(ài)情不求回報(bào),為了成全女方的幸福甘愿代替情敵赴死,慷慨從容,這是為了他人為了愛(ài)而自我犧牲。像卡頓和洛里這樣的人正是作家那個(gè)時(shí)代急需的人,他們身上充滿人道主義的閃光,具有崇高的品格和溫暖人心的力量。“狄更斯要成為召喚人們回到歡笑和愛(ài)中的明燈。”[16]他通過(guò)塑造馬內(nèi)特醫(yī)生,卡頓,洛里先生等形象,試圖打破資本主義工業(yè)文明的堅(jiān)冰,在讀者心中喚醒以無(wú)私奉獻(xiàn)和愛(ài)與溫情為核心的人道主義精神的復(fù)歸。
四
除了人道主義精神內(nèi)涵的側(cè)重不同外,雨果和狄更斯在探尋社會(huì)的出路時(shí)持有不同的觀點(diǎn)。
雨果把人道主義看做人類(lèi)的最高信仰,堅(jiān)信“在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絕對(duì)正確的人道主義”[17],他認(rèn)為“這場(chǎng)斗爭(zhēng)的戰(zhàn)場(chǎng)是一個(gè)人的良心”[18],暴力并不能解決問(wèn)題,要用一個(gè)善的靈魂才能撼動(dòng)另一個(gè)靈魂,最終走向人道主義,“才能夠把我們從人性的黑暗、狹隘和蒙昧中解救出來(lái)。”[19]人道主義是人類(lèi)唯一正確的出路。在這個(gè)原則的支配下小說(shuō)情節(jié)有多處違背現(xiàn)實(shí)的刻意安排,如心狠手辣的叛黨頭目朗特納克可以在危機(jī)的時(shí)刻突然受到人道主義的感召發(fā)生轉(zhuǎn)變,郭文為了奉行最高的人道原則可以不顧自己的政治立場(chǎng)放走朗特納克。更甚至隨著革命的發(fā)展,雨果的人道主義理想與革命發(fā)生了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使他對(duì)整場(chǎng)革命的正義性都產(chǎn)生了懷疑,深深陷入了革命和人道的矛盾之中,在小說(shuō)結(jié)尾處通過(guò)郭文之死發(fā)出抗議的呼聲,以人人互助互愛(ài)的人道主義王國(guó)為最高理想,對(duì)革命黨丹東等三巨頭組成的紅色專(zhuān)政進(jìn)行了一番指控。雨果在《九三年》中這樣寫(xiě)道:
“我們所需要的”,馬拉突然叫道:“是一個(gè)獨(dú)裁者。羅伯斯庇爾,你知道我希望有一個(gè)獨(dú)裁者。”
羅伯斯庇爾抬起頭:“我知道,馬拉,不是你就是我。”
“不是我就是你!”馬拉說(shuō)。
丹東在齒縫里咕嚕說(shuō):“獨(dú)裁,試試看!”
馬拉:“……丹東,我同意你這一點(diǎn);羅伯斯庇爾,這一點(diǎn)我向你讓步。好,那么,結(jié)論是:獨(dú)裁。讓我們采取獨(dú)裁的辦法。我們?nèi)齻€(gè)人代表革命。我們是塞卑爾的三個(gè)頭(看守地獄大門(mén)的三頭怪犬)。”[20]
從作者描寫(xiě)的這段對(duì)話可以看出,雨果意識(shí)到這場(chǎng)革命已經(jīng)變質(zhì),當(dāng)平民沖在最前面為革命流血犧牲的時(shí)候,馬拉,羅庇斯比爾,丹東三大巨頭正坐在巴黎窗明幾凈的屋宇里,為建立新的專(zhuān)制政權(quán)開(kāi)討論會(huì)。筆者認(rèn)為,在雨果看來(lái)革命發(fā)展到最后對(duì)誰(shuí)都沒(méi)有好處,革命黨推翻了貴族的專(zhuān)制統(tǒng)治又建立起一個(gè)新的專(zhuān)制政權(quán),實(shí)行紅色恐怖主義,前后兩者都不符合作家最高的人道主義信仰。激烈的對(duì)抗,使新事物不免走向偏激,以致新事物在取得勝利后,也難以走向健康的發(fā)展,而背離了它的本意,甚至使舊事物得以卷土重來(lái)。所以雨果通過(guò)郭文的口喊道“我更愛(ài)的是,一個(gè)理想的共和國(guó)”[21],是奉行人道主義的王國(guó),作家關(guān)心的是新的國(guó)家“有沒(méi)有盡忠,犧牲,克己,恩恩相報(bào)和仁愛(ài)的地位呢?”[22]而不是這個(gè)國(guó)家最終是共和軍的還是保王黨的。一個(gè)奉行絕對(duì)的人道主義的王國(guó)才是人類(lèi)社會(huì)真正的出路。只有絕對(duì)的人道主義——斬?cái)嗔撕薜摹?超越了利害關(guān)系的神圣之愛(ài),即使對(duì)罪人、對(duì)“兇手” 也懷有深深同情和憐憫的愛(ài),才能拯救我們的社會(huì)。
作為一個(gè)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家,首先狄更斯沒(méi)有采取浪漫的處理方式有意夸大人道主義的作用,使所有的主人公都受到感化而精神“復(fù)活”,而是真實(shí)地再現(xiàn)出巴黎民眾滿腔的怒火和狂暴的復(fù)仇,德法日夫人從頭到尾沒(méi)有一絲心軟,直到死亡才能阻止她繼續(xù)編織復(fù)仇的網(wǎng)子。巴黎民眾一點(diǎn)也沒(méi)有意識(shí)到革命已面臨走入歧途的危險(xiǎn),而是沉浸在復(fù)仇的喜悅中,恨不得殺光所有貴族,這樣的描寫(xiě)比起雨果式的人道主義顯得更為客觀。其次狄更斯也沒(méi)有把人道主義視為萬(wàn)靈的藥方,借此逃避革命的殘酷性,沒(méi)有從一個(gè)極端(暴力革命)走向另一個(gè)極端(絕對(duì)的人道主義),而是辯證地看待了革命和人道主義的關(guān)系。一方面他看到了在革命過(guò)程中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正確的,為了推翻舊的封建王權(quán)需要一些流血和犧牲,而不是像雨果那樣陷入人道主義和革命的矛盾中,繼而對(duì)革命的本質(zhì)產(chǎn)生懷疑。《雙城記》里的革命者始終堅(jiān)持革命和共和國(guó)理想,沒(méi)有出現(xiàn)郭文這樣矛盾掙扎的形象。另一方面,作家反對(duì)將革命暴力擴(kuò)大化。德法日夫人的仇恨是可以理解的,在小說(shuō)的前半部分,作家對(duì)這個(gè)意志堅(jiān)強(qiáng),勇于反抗的女人還帶著一絲欣賞,但是當(dāng)她把報(bào)復(fù)的矛頭指向無(wú)辜的達(dá)奈和露西時(shí),作家對(duì)他的描寫(xiě)愈見(jiàn)冷峻。她尖刻的嘴臉,扭曲陰暗的心理,殘忍的手段,逐漸暴露,最后到了招人厭的地步,連她的丈夫都不敢正視她冰冷無(wú)情的雙眼。暴力是革命的手段,但不是革命的目的,當(dāng)革命者像德法日夫人這樣失去理智,只剩下殘暴時(shí)便是反人道的,就該受到批判。正如小說(shuō)中記述的羅蘭夫人被砍頭之前說(shuō)的話:“我看到,在廢棄這種報(bào)應(yīng)的懲罰工具像目前這樣使用以前,巴薩,萊克,德法日,那個(gè)陪審員,那個(gè)審判長(zhǎng),以及許多消滅舊壓迫者上臺(tái)的新壓迫者,都將死于他的斧下。”[23]這是狄更斯為這個(gè)時(shí)代做出的預(yù)言。
在辯證地看待革命與人道的基礎(chǔ)上,狄更斯提出改良政治的主張,把調(diào)和階級(jí)矛盾視為社會(huì)的出路。我們可以從小說(shuō)中三組對(duì)照人物形象中來(lái)看,即同為貴族的侄子達(dá)奈和叔父埃弗雷蒙德侯爵,同為革命者的德法日太太和德法日先生,以及同為犯人的卡頓和縫工。埃弗雷蒙德侯爵無(wú)惡不作,深受人民的仇恨,如果不是逃到國(guó)外,差一點(diǎn)就死于革命。與之相比,達(dá)奈被塑造成進(jìn)步貴族的形象。他待人溫和有禮,從不依仗自己的貴族特權(quán)為非作歹;他心地善良,不以家族姓氏為豪反而為恥,自己的叔父做盡了壞事,招人憎恨,作為侄子他受到良心譴責(zé),放棄了一切地位和特權(quán),主動(dòng)脫離家族來(lái)到倫敦自力更生;他慷慨仁慈,盡力幫助平民,交代仆人不要苛責(zé)莊園里的傭人,減免稅款,讓他們過(guò)得舒心自在一些;他有情有義,對(duì)仆人寬厚仁愛(ài),明知法國(guó)局勢(shì)危險(xiǎn),但是接到仆人的求救信件,他只身犯險(xiǎn)趕往巴黎救人。達(dá)奈的形象寄托著作者對(duì)社會(huì)統(tǒng)治者的期望,即反對(duì)壓迫,實(shí)施有人道的統(tǒng)治政策,改善人民生活。德法日太太和先生都是革命者的代表,但德法日太太最終被仇恨蒙蔽了心智,喪失了人性,而德法日先生在革命過(guò)程中并沒(méi)有完全與人道主義相背離,他并不像妻子那樣對(duì)砍頭和流血無(wú)比狂熱,在小說(shuō)中他多次詢問(wèn)妻子報(bào)復(fù)的行動(dòng)什么時(shí)候停下來(lái),雖然沒(méi)能徹底阻止德法日太太的瘋狂,但對(duì)馬內(nèi)特醫(yī)生一家自始至終流露出一絲同情和不忍,沒(méi)有直接參與到德法日太太對(duì)馬內(nèi)特醫(yī)生和露西的報(bào)復(fù)行動(dòng)中。而在小說(shuō)的最后一章,卡頓和一個(gè)貧苦的縫工手牽手走向刑場(chǎng),“這兩個(gè)本來(lái)各在一方,又大不相同的宇宙母親的孩子,眼看著眼,你一言我一語(yǔ),手拉著手,推心置腹”[24],他們相互親吻和祝福,在生死面前,成為了親人。作者通過(guò)這三組形象表明,如果統(tǒng)治者推行人道的政策,如果人人心中都存著愛(ài)和友善,階級(jí)矛盾是可以調(diào)和的,天各一方的人也可以相親相愛(ài),人們可以放下仇恨,握手言和。
綜上所述,盡管雨果式的人道主義和狄更斯式的人道主義為社會(huì)找到的出路不同,但不管是追求人間大愛(ài)大公,至善至美的境界,把希望寄托于超階級(jí)的人道主義對(duì)社會(huì)的救贖,還是反對(duì)階級(jí)壓迫,試圖調(diào)和階級(jí)矛盾,走政治改良的道路,他們都在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下對(duì)人類(lèi)的未來(lái)和人道主義精神做出了積極的探索和創(chuàng)作實(shí)踐,表達(dá)出作為一個(gè)人道主義者悲天憫人的情懷。
注釋?zhuān)?/p>
[1]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6 ,鄭永慧譯。
[2]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6 ,鄭永慧譯。
[3]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6 ,鄭永慧譯。
[4]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6,鄭永慧譯。
[5]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6,鄭永慧譯。
[6]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6,鄭永慧譯。
[7]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6,鄭永慧譯。
[8]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6,鄭永慧譯。
[9]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6,鄭永慧譯。
[10]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6,鄭永慧譯。
[11]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6,鄭永慧譯。
[12]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6,鄭永慧譯。
[13]鄭永慧:《〈九三年〉前言》,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6。
[14](蘇聯(lián))伊瓦肖娃:《狄更斯評(píng)論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3月第一版,蔡文顯 廖世建 李筱菊 譯。
[15](美)埃德加·約翰遜:《狄更斯—他的悲劇與勝利》,天津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林筠因 石幼珊 譯。
[16](美)埃德加·約翰遜:《狄更斯—他的悲劇與勝利》,天津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林筠因 石幼珊 譯。
[17]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6,鄭永慧譯。
[18]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6,鄭永慧譯。
[19]陳為人:《“革命”還是“寬仁”?—重溫雨果<九三年>》,《社會(huì)科學(xué)論壇》,2010/1半月刊。
[20]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6,鄭永慧譯。
[21]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6,鄭永慧譯。
[22]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6,鄭永慧譯。
[23]狄更斯:《雙城記》,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 ,1995,石永禮 趙文娟 譯。
[24]狄更斯:《雙城記》,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 ,1995,石永禮 趙文娟 譯。
參考文獻(xiàn):
[1](蘇聯(lián))伊瓦肖娃:《狄更斯評(píng)論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3月第一版,蔡文顯 廖世建 李筱菊 譯。
[2]柳鳴九:《雨果創(chuàng)作評(píng)論集》,鷺江出版社,1983年1月第一版。
[3]陳為人:《“革命”還是“寬仁”?—重溫雨果<九三年>》,《社會(huì)科學(xué)論壇》,2010/1半月刊。
[4](美)埃德加·約翰遜:《狄更斯—他的悲劇與勝利》,天津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林筠因 石幼珊 譯。
[5](法)安德烈·莫洛亞:《雨果傳》,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8年,程曾厚 程干澤 譯。
[6]張英倫:《雨果傳》,北岳文藝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