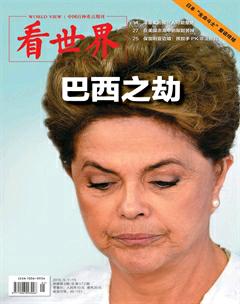風(fēng)雪看病記(上)
陶紅
2015年2月,美國(guó)東北部暴雪連連。一家人因先生在麻省理工訪學(xué),正好在波士頓。
兒子上學(xué)時(shí),在操場(chǎng)玩瘋了,雪灌到鞋里,回教室后化成冰水,一直泡著雙腳直到放學(xué)。兩天后,一直擔(dān)心的著涼癥狀出現(xiàn)了,兒子咽痛、發(fā)熱。于是趕緊打電話約醫(yī)生。可那個(gè)我們常去的醫(yī)院跟我們說:這幾天已經(jīng)約滿了,要等到三天以后。
可是三天后已經(jīng)安排了去新奧爾良的短期旅行,機(jī)票和酒店費(fèi)用已全部支付,如果不是航班取消,不能全額退款。于是一邊盼著航班取消,一邊拿常用藥對(duì)付著。結(jié)果前一天和后一天的航班都取消了,唯獨(dú)那一天的沒取消。
異地看急診
好在兒子已經(jīng)退燒,狀況基本穩(wěn)定,于是一家人經(jīng)過堆滿積雪的城市來到仿佛北極的洛干機(jī)場(chǎng)。在機(jī)場(chǎng)忽然發(fā)現(xiàn)兒子身上有疹子,懷疑是藥物過敏。問了醫(yī)生朋友,紛紛將矛頭指向臨時(shí)拿來充數(shù)的成人裝感冒沖劑,于是趕緊停藥,心中后怕不已。
到達(dá)新奧爾良第二天,疹子消了,發(fā)燒又開始了。人生地不熟,跑去求助酒店大堂經(jīng)理。她說:“離這不遠(yuǎn)有個(gè)急診(URGENT CARE)。可是能不去還是先別去。”為什么呢?她接著說:“現(xiàn)在是特殊時(shí)期,一年一度的狂歡節(jié)(MARDI GRAS)嘞。醫(yī)院里不是喝多了自己摔的,就是喝多了互相打的。你下午去,等到明天早上能看上就不錯(cuò)。”只好打消念頭。
熬到第二天,兒子癥狀沒有好轉(zhuǎn)。跟大堂經(jīng)理要了地址,硬著頭皮,無論如何也要去看看。
到了地方,發(fā)現(xiàn)并沒有傳說中的那么多人。男醫(yī)生挺嚴(yán)肅,看了看嗓子,扭身出去,半截身子夾在門里,回頭說:“一會(huì)兒護(hù)士給你做個(gè)咽試紙,如果結(jié)果陽(yáng)性,說明是鏈球菌感染。我會(huì)給你開抗生素,記得一定要吃夠十天。”然后就消失了。
直到護(hù)士拿著檢驗(yàn)結(jié)果和處方過來,告訴我們到哪里買藥,那名醫(yī)生都沒再出現(xiàn)。正納悶這簡(jiǎn)練的風(fēng)格是否正是門診和急診的區(qū)別,發(fā)現(xiàn)門口的醫(yī)生簡(jiǎn)介上說那位醫(yī)生曾是耳鼻喉科醫(yī)生,現(xiàn)在主攻美容整形了。估計(jì)在這位醫(yī)生的心里實(shí)在不愿意為了這么小的CASE花費(fèi)時(shí)間呢。
波士頓遇到糊涂?jī)嚎浦魅?/h3>
第二天,一家人返回冰雪覆蓋的波士頓。當(dāng)時(shí)正值短暫的寒假,馬上要開學(xué)了。擔(dān)心孩子有進(jìn)一步的呼吸道感染,或者由呼吸道感染引發(fā)哮喘,再次約了以往常去的那家醫(yī)院,打算好好去查一查。
出租車行駛在滿是冰雪的波士頓,這次檢查會(huì)怎樣呢?心中忐忑不安。
女醫(yī)生來了,居然是兒科主任,五十歲左右,短發(fā)、中等身材,走路很灑脫的樣子。心想,找著專家了,這下可放心了。
她問我們這次想看什么?我們說想看看有沒有肺炎(PNEUMONIA)和哮喘(ASTHMA),順便請(qǐng)醫(yī)生判斷一下過幾天能不能去上學(xué)。在國(guó)內(nèi)時(shí)我們就是這樣看的。醫(yī)生給聽聽,有時(shí)說沒問題,有時(shí)說有哮喘前兆,先吃點(diǎn)兒順爾寧之類的壓一壓,最后總能建議一句:“上學(xué)可以,不能劇烈活動(dòng)”,或“先歇兩天再去上學(xué)”。
事情到了地球另一端就不是一回事了。我們問有哮喘嗎?醫(yī)生過來拿著聽診器著實(shí)好好地聽了一番,說:“哮喘確實(shí)是有一點(diǎn)兒的,但是不嚴(yán)重,先做一次霧化,然后開點(diǎn)兒霧化的藥回去用。”嗯,這倒跟國(guó)內(nèi)一樣。
那能不能去上學(xué)呢?醫(yī)生說:“我不知道你說的能去上學(xué)是什么標(biāo)準(zhǔn),我可以給他做全身的檢查,但那樣得抽血。”我說抽血干什么?她說:“中國(guó)絕大部分人有肺結(jié)核(TB),要看看有沒有肺結(jié)核。”我心想,瞎扯,這醫(yī)生觀念也太陳舊了,都什么年代了,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基本都種過肺結(jié)核疫苗。肺結(jié)核在中國(guó)已經(jīng)是偶發(fā)事件了。
那呼吸道感染發(fā)展到什么程度了?有沒有肺炎呢?醫(yī)生說那得照X光。聽說在美國(guó)檢查費(fèi)天價(jià),也不知道保險(xiǎn)能不能覆蓋。可兒子這次著涼深重,一定不能掉以輕心。狠狠心,上樓做了。
再次回到診室,醫(yī)生盯著電腦屏幕從系統(tǒng)里看X光報(bào)告,“哦,有些問題,但是問題不大。”一會(huì)兒又?jǐn)Q著眉毛,指著屏幕上一個(gè)部位說:“這是咋回事?是沒照清楚還是有問題?你們等等啊!”她先打電話給樓上影像師,說不清楚,又親自跑上去,回來一副如釋重負(fù)的樣子:“沒問題,跟樓上的影像師核對(duì)了,沒問題。”我心想,你連個(gè)片子都看不明白呀。
三種藥拿了三回
已經(jīng)又餓又累了,一心想著早點(diǎn)兒回家。醫(yī)生開了三種藥,我們來到一樓藥房。隊(duì)排得挺長(zhǎng),先交單子、付錢,再等著叫名字拿藥,時(shí)間也很長(zhǎng)。
凳子上忍饑挨餓坐了半個(gè)多小時(shí),終于可以拿到藥了。可怎么只有一種藥?交藥的柜員說:“在系統(tǒng)里只看到了一種藥。”我們說不對(duì)呀,是三種呀。柜員說反正只能看到一種,有問題就回去找醫(yī)生吧。于是趕緊回四樓去找。
四樓前臺(tái)的護(hù)士很負(fù)責(zé)任,立刻給大夫打電話詢問。折騰了一番,說:“那兩個(gè)藥在系統(tǒng)里有些特別,要特別批準(zhǔn)到樓下藥房才行。醫(yī)生忘了在系統(tǒng)里做了。現(xiàn)在你們?nèi)ヒ粚影桑粯撬幏康南到y(tǒng)里應(yīng)該可以看到了。”
好吧,餓得腿都打顫了,下樓。回到一層,排隊(duì),等輪到我們,藥房柜員收錢、開單據(jù)。我一看,怎么又只有一個(gè)呀?那人說:“只下來一個(gè),沒有第二個(gè)。”怎么回事?一家人忍者饑餓的肚子,又上樓去找。
不用問,肯定是那個(gè)大夫忘了,在系統(tǒng)里只做了一個(gè),沒做另一個(gè)。這回四樓的大夫和護(hù)士真心覺得過意不去了。前臺(tái)的護(hù)士和大夫溝通之后,立即交代藥房,說:“特事特辦,趕快給配藥,趕快交付,不用排隊(duì),別讓人家再等了。”好嘛,他們樓上給耽誤成這樣,一個(gè)電話,就成了樓下藥房的事兒了。
一家人懷著不知道又會(huì)發(fā)生什么的心情再次下樓,稍微等了一下,終于拿到了第三種藥。抬頭看表,已經(jīng)1點(diǎn)半了。出來拿藥的時(shí)候還不到12點(diǎn)。想想在國(guó)內(nèi)醫(yī)院里各種交費(fèi)排隊(duì)的周折,真是不分伯仲呀。
回去的路上,一家人又累又餓,一言不發(fā)。往返程的司機(jī)是同一個(gè)人,來的路上還有說有笑,回去時(shí)看一家人臉色不對(duì),一句廢話沒敢說,車?yán)锏目諝馑坪跄Y(jié)了。滿城的冰雪更加重了悲涼的氣氛。
這病是看完了,賬單還不知道有多大呢,保險(xiǎn)能給支付多少?這都是未知數(shù)。那一刻我深深明白了,美國(guó)人為什么那么愛運(yùn)動(dòng)。
孩子的病漸漸好起來,關(guān)于藥費(fèi)和診療費(fèi)還有不少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