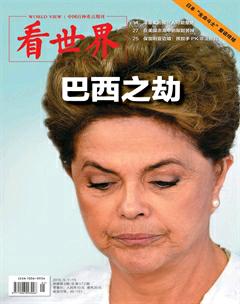扎哈·哈迪德走了,留下一大碗職場(chǎng)勵(lì)志雞湯
張曉東
像兩塊大石頭一樣放置在珠江邊的廣州大劇院;像四個(gè)白色饅頭一樣生長(zhǎng)在故宮東側(cè)的北京銀河SOHO;像一件女士裙擺一樣飄蕩在里海沿岸的巴庫(kù)阿里耶夫文化中心……你可能沒(méi)有聽(tīng)過(guò)英國(guó)女建筑師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的名字,但你一定對(duì)她設(shè)計(jì)出的這些令人嘆為觀止的神奇建筑有印象。
2016年3月31日,以設(shè)計(jì)風(fēng)格大膽前衛(wèi)著稱的扎哈在美國(guó)邁阿密因病去世,享年65歲,給世界各地留下數(shù)個(gè)帶有其強(qiáng)烈個(gè)人色彩的地標(biāo)建筑及其事務(wù)所里上百個(gè)正在進(jìn)行中的下一個(gè)潛在的傳世之作。
喜歡扎哈的人認(rèn)為她“無(wú)拘無(wú)束”,敢于挑戰(zhàn)傳統(tǒng)的建筑風(fēng)格教條;不喜歡扎哈的人則批判她“形式主義至上”,華麗卻不接地氣。隨著她的突然辭世,有關(guān)她個(gè)人設(shè)計(jì)風(fēng)格的爭(zhēng)議暫時(shí)被擱置到一邊,取而代之的是默哀和懷念——在廣州大劇院的入口處,扎哈的畫(huà)像周圍擺滿了粉絲獻(xiàn)上的鮮花。
在建筑行業(yè)里,扎哈雖然并不總收獲全部的掌聲,但卻取得了毫無(wú)爭(zhēng)議的偉大成就:她建立的個(gè)人事務(wù)所每年凈利潤(rùn)超過(guò)400萬(wàn)英鎊,源源不斷的合約讓她成為商業(yè)領(lǐng)域炙手可熱的金字招牌;她獲得的普利茲克獎(jiǎng)讓她成為打破建筑業(yè)“男性俱樂(lè)部”的壟斷,成為獲得該項(xiàng)殊榮的首位女性……
“在談?wù)撛吷删偷臅r(shí)候的確沒(méi)有辦法忽略掉她的身份特質(zhì)。一個(gè)伊拉克出生的女性穆斯林在白人男性主導(dǎo)的建筑行業(yè)呼風(fēng)喚雨,這毫無(wú)疑問(wèn)是最具有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特色的勵(lì)志職場(chǎng)故事。”《洛杉磯時(shí)報(bào)》如此寫(xiě)到。
叱咤倫敦的中東人
“是一種三連環(huán)一樣的重?fù)簟薄T诨貞洺醯絺惗貏?chuàng)業(yè)時(shí)的困惱時(shí),扎哈·哈迪德曾經(jīng)如此對(duì)BBC說(shuō),“我是個(gè)女人,這首先就是個(gè)問(wèn)題;其次我還是個(gè)外國(guó)人,這又是個(gè)不小的障礙;最后我還要設(shè)計(jì)一些‘不符合常規(guī)的東西出來(lái),這對(duì)上世紀(jì)的英國(guó)社會(huì)來(lái)說(shuō),不是什么好消息。”
盡管80年代初期就在倫敦成立了自己的事務(wù)所,但直到2006年蘇格蘭維多利亞醫(yī)院瑪姬癌癥康復(fù)中心這一小型建筑竣工之前,扎哈在英國(guó)并沒(méi)有建成過(guò)一座屬于自己的作品。在此4年之后,扎哈在倫敦的首座建筑伊芙琳·格蕾絲學(xué)院才宣告竣工,這座中學(xué)建筑為她贏得了2011年的斯特林大獎(jiǎng)。
扎哈承認(rèn),在對(duì)傳統(tǒng)文化有著堅(jiān)守情結(jié)的大英帝國(guó)想要植入一座“扭扭曲曲”、“光怪陸離”的“扎哈式”后現(xiàn)代主義建筑的確要面臨不小的阻力。而更為崇尚藝術(shù)(不管是傳統(tǒng)還是后現(xiàn)代)的歐洲大陸以及經(jīng)濟(jì)發(fā)展帶動(dòng)下城市基建日新月異的亞洲,則成了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內(nèi)扎哈·哈迪德事務(wù)所的主要戰(zhàn)場(chǎng)。
“針對(duì)外國(guó)設(shè)計(jì)師的偏見(jiàn)的確存在,但我在亞洲和歐洲大陸遇到的比較少。”扎哈說(shuō),反而是以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為主導(dǎo)的英美兩國(guó)給了她不少的閉門羹,“或許不是因?yàn)槲沂莻€(gè)女人,而是個(gè)來(lái)自中東的穆斯林。”
30歲出道、40歲才有作品落地竣工的扎哈是個(gè)“大器晚成”的經(jīng)典案例。在她短暫卻又高產(chǎn)的建筑師生涯中,停留在圖紙上沒(méi)有建成的作品無(wú)數(shù),但唯有位于威爾士的卡迪夫大劇院讓她無(wú)法釋?xiě)选?/p>
上世紀(jì)90年代中期,卡迪夫地方政府對(duì)外招標(biāo),希望建成一座“高水平”的文化地標(biāo)。扎哈的投稿以黑白兩色對(duì)撞的“海灣項(xiàng)鏈”方案在初期脫穎而出,此后還贏得多項(xiàng)國(guó)際大獎(jiǎng),這個(gè)地標(biāo)一度被視為扎哈的囊中物。
但在1995年的圣誕節(jié)前三天,當(dāng)?shù)卣臈墭?biāo)公告震驚了整個(gè)建筑界。“這個(gè)方案過(guò)于具有特色,因此不予采用。”后來(lái)《紐約時(shí)報(bào)》爆料稱,是當(dāng)?shù)氐囊蝗簶O端保守政客和輿論人士在幕后扼殺了“海灣項(xiàng)鏈”。
卡迪夫大劇院事件后來(lái)演變成針對(duì)扎哈伊拉克裔身份的種族攻擊:一位威爾士當(dāng)?shù)氐淖h員稱這個(gè)方案是“麥加大清真寺的翻版”,指控扎哈設(shè)計(jì)這個(gè)方案是為了傳教;一些當(dāng)?shù)厝松踔翈в刑翎呉馕兜刭|(zhì)問(wèn)她:“你的丈夫去哪兒了?是被關(guān)起來(lái)了嗎?”
扎哈后來(lái)接受《紐約客》采訪時(shí)稱,那段時(shí)期“人們根本不再關(guān)心問(wèn)題的本質(zhì)(建筑的風(fēng)格和設(shè)計(jì)),而只開(kāi)始探討那些吸引眼球、能引起沖突的東西”。
出生在前薩達(dá)姆時(shí)代的扎哈成長(zhǎng)于巴格達(dá)一個(gè)進(jìn)步知識(shí)分子家庭,她從小被信仰天主教的修女帶大。她認(rèn)為自己不算“虔誠(chéng)的穆斯林”,但與生俱來(lái)的種族和宗教標(biāo)簽卻足以讓有心搞偏見(jiàn)的人找到足夠的借口。
此后刻意遠(yuǎn)離英國(guó)建筑行業(yè)的扎哈逐漸在世界其他角落找到了愿意欣賞她作品的人,而卡迪夫大劇院之后的十年恰好也是她加冕建筑“女魔頭”、事業(yè)走向黃金期的十年。
建筑界的“扎哈女士”
《紐約客》曾經(jīng)給這位建筑界唯一的女強(qiáng)人取過(guò)一個(gè)外號(hào):扎哈女士(Lady Zaha),不僅因?yàn)樗c流行偶像Lady Gaga的名字押韻,還在于兩位女性之于女權(quán)運(yùn)動(dòng)的某種相似的領(lǐng)袖型影響力。
但比起流行音樂(lè)產(chǎn)業(yè),建筑業(yè)則更顯得對(duì)女性不友好——更不要說(shuō)是像扎哈這樣來(lái)自第三世界國(guó)家的女性。“我從來(lái)不使用自己的性別作為談資,”扎哈2004年接受《衛(wèi)報(bào)》采訪時(shí)表示,“但如果年輕一代能夠因?yàn)槲业某晒Χ@得打破性別天花板的動(dòng)力的話,那我的確愿意成為模范。”
一份由美國(guó)建筑師協(xié)會(huì)舊金山分部發(fā)布的報(bào)告顯示,盡管2015年學(xué)習(xí)建筑專業(yè)的女性占到了42%,但她們只占到建筑行業(yè)雇員的28%,而只有17%成功熬到了高級(jí)職位或合伙人的階段。“盡管有像扎哈這樣的勵(lì)志者出現(xiàn),但這個(gè)行業(yè)總體上還是被男性、尤其是白人男性所把持的。”《洛杉磯時(shí)報(bào)》說(shuō)道。
女建筑師丹妮絲·布朗在2013年接受《洛杉磯時(shí)報(bào)》采訪時(shí)稱她不得不面對(duì)對(duì)她“頤指氣使”以及“帶有敵意”的工作同僚。“當(dāng)他們開(kāi)派對(duì)的時(shí)候,一般直接忽略我。因?yàn)槲沂羌依锏摹拮印!钡つ萁z和他的丈夫以合伙人的方式共同經(jīng)營(yíng)著一家事務(wù)所,但她通常被置于附庸的地位。
事實(shí)上,和丈夫一起開(kāi)事務(wù)所是很多女建筑師在行業(yè)立足的不得已選擇。《紐約時(shí)報(bào)》報(bào)道稱,即使有時(shí)候她們的成就已經(jīng)明顯高過(guò)作為其事業(yè)伙伴的丈夫,但在借機(jī)商討重要議題的高爾夫聚會(huì)上,女建筑師通常不會(huì)接到邀請(qǐng)。
當(dāng)扎哈面臨這個(gè)問(wèn)題的時(shí)候,她選擇了迎難而上而不是加以妥協(xié)。她自己的事務(wù)所只以自己的名字冠名,而不是像其他女建筑師那樣“找個(gè)夫姓來(lái)冠”。實(shí)際上,直到她去世為止都一直未婚且無(wú)子女,她是真正意義上“嫁給建筑的女人”。
做事雷厲風(fēng)行、標(biāo)準(zhǔn)高要求嚴(yán)的扎哈視建筑行業(yè)為傳統(tǒng)家庭生活的禁區(qū),她認(rèn)為這一行不適合那些想要過(guò)朝九晚五生活的人。“你想要過(guò)得輕松的話,就不要選擇做建筑師。我們的工作是隨時(shí)隨地的,沒(méi)有上班和下班這種區(qū)分。”
“扎哈的離去對(duì)女性建筑師群體而言是個(gè)沉重的打擊,”在紐約一間大學(xué)建筑系任教的斯塔克萊格教授指出,那些有意從事建筑行業(yè)的女性就好像“失去了人生導(dǎo)航的燈塔”。上述美國(guó)建筑師協(xié)會(huì)的報(bào)告同樣指出,有三分之一中途退出這個(gè)行業(yè)的女性建筑師是因?yàn)榭床坏娇梢?jiàn)范圍內(nèi)的楷模。
“扎哈在中東地區(qū)的影響力是毫無(wú)疑問(wèn)的,”Quartz網(wǎng)站的敘利亞裔編輯洛巴納·邁瑞則坦言,自己從小學(xué)的時(shí)候就知道了扎哈,她長(zhǎng)期以來(lái)被視為年輕穆斯林女性的偶像。“我們可以對(duì)自己的父親和兄長(zhǎng)說(shuō),獨(dú)立和成功的女性是存在的。”
絕不妥協(xié)的“女魔頭”
通過(guò)一座又一座科幻感十足的建筑在世界各地成名的扎哈也在同全球建筑業(yè)者合作的過(guò)程中被賦予了一個(gè)毀譽(yù)參半的的外號(hào):女魔頭。有媒體解釋說(shuō)如此稱呼她是因?yàn)樗鈱?shí)在暴躁,稍有不滿即刻爆發(fā);有的業(yè)內(nèi)人士則坦言是因?yàn)樗跊Q策過(guò)程中一向固執(zhí)己見(jiàn),聽(tīng)不進(jìn)去其他人的建議,對(duì)自己的設(shè)計(jì)方案充滿自信。
在廣為流傳的“扎哈十大名言”中,“如果周圍環(huán)境就是個(gè)糞坑,那你還需要讓我去跟那些屎妥協(xié)不成?”這一句話不僅成為她對(duì)自己筆下“絲毫不走尋常路”那種設(shè)計(jì)稿的最佳辯護(hù),更成為她“女魔頭”形象的側(cè)面反映。
在扎哈的設(shè)計(jì)理念中,鋼筋混凝土可以隨心所欲,如同捏面團(tuán)一般。在她的設(shè)計(jì)中,有著猛然下沉的地板、傾斜的墻面、仿佛要飛升的天花板,內(nèi)外空間奇特地相互融合,仿佛是天外來(lái)客一般,墜落于城市之中。
這種自成一派的建筑雖然為不少城市締造了新的地標(biāo),但也引來(lái)不少“破壞傳統(tǒng)文化”和“影響整體視覺(jué)效果”的批評(píng)。此外,對(duì)視覺(jué)美感的首要保證在很多時(shí)候意味著犧牲建筑的經(jīng)濟(jì)型,這讓擁有決策權(quán)的各地政府陷入兩難。
扎哈在2012年提交的2020年?yáng)|京奧運(yùn)會(huì)主場(chǎng)館方案在經(jīng)歷了三年的大討論后最終于2015年被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布否決,取而代之的是日本本土設(shè)計(jì)師更低調(diào)、更省錢的方案。
在扎哈的方案中,主場(chǎng)館的外形如同一頂棒球帽,呈現(xiàn)非常分明的肌理感,主體結(jié)構(gòu)連接處則輔以格子形外殼,整體呈流線型。場(chǎng)館有數(shù)個(gè)橢圓形和卵形窗子,從內(nèi)部看,猶如身處宇宙飛船內(nèi)。
但這個(gè)極具浪漫主義色彩的方案卻被大量日本民眾批評(píng)為“花哨”和“不實(shí)用”,在一項(xiàng)民意調(diào)查中竟然有9成受訪者表示不滿這一方案。幾次易稿后的扎哈方案雖然從外型上看有所變化,但仍然造價(jià)不菲。
最終扎哈事務(wù)所和日本政府分道揚(yáng)鑣,東京“新國(guó)立競(jìng)技場(chǎng)”成為“女魔頭”扎哈無(wú)數(shù)瘋狂建筑手稿中又一件未能完成的狂想之作。但無(wú)論如何,由扎哈領(lǐng)銜的這一波現(xiàn)代主義建筑熱潮卻并不會(huì)就此停止。
日本建筑師安藤忠雄表示,扎哈給了人類社會(huì)一張通往未來(lái)的通行證。他表示:“新世紀(jì)以來(lái),由于造型能力與計(jì)算機(jī)技術(shù)的發(fā)展,建筑固有的形態(tài)也隨之改變。扎哈也成為了引領(lǐng)世界建筑界的先鋒。扎哈的(國(guó)立競(jìng)技場(chǎng))設(shè)計(jì)案可以作為一個(gè)新的象征。”
《紐約客》則說(shuō):“扎哈引領(lǐng)的革命才剛剛開(kāi)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