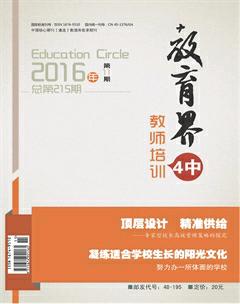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陸嘉明
羅氏下筆所狀劉備之哭,極盡一個(gè)“態(tài)”字。
哭而有“態(tài)”,眉間心上,情貴蘊(yùn)藉。李清照有詞曰:“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人無語而默然流淚,哭而有“態(tài)”,便愈見悲情婉篤;白居易《長恨歌》云:“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玉容淚水縱橫,哭之“態(tài)”如花帶雨,不由人不愛憐痛惜;宋毛滂也有詞云:“淚濕闌干花著露,愁到眉峰凝碧。”哭而如花著露,愁而如遠(yuǎn)山峰起,不勝嬌柔憂思之“態(tài)”,自有一種悲切深重的心情。可見,以“態(tài)”狀哭,別饒意思幽微的美感風(fēng)韻。
“態(tài)”,一般指人之容貌外在的動(dòng)感狀態(tài),但又形之于其內(nèi)在的心理活動(dòng)和情意狀態(tài)。“態(tài)”,與人的顏值有關(guān)亦無關(guān)。有關(guān)者“態(tài)”依顏值而呈現(xiàn);無關(guān)者“態(tài)”與顏值高低無必然聯(lián)系。有美學(xué)家說,女性之美,不唯形貌,更在有態(tài)。顏值不高若有“態(tài)”,有“態(tài)”便可愛。可愛,令人愉悅,美感于斯生焉。當(dāng)然,顏值高而又有“態(tài)”,那就更美了,恰如宋晏幾道《浣溪沙》詞云:“腰自細(xì)來多態(tài)度,臉因紅處轉(zhuǎn)風(fēng)流。”古人有言,女子有態(tài)須傾國,誠然可信。西施捧心顰眉,容貌姿態(tài)之美無不驚艷;東施效顰則矯揉造作,態(tài)貌何其丑也。可見人之“態(tài)”,美在真,美在自然。黛玉在寶玉面前不時(shí)傷心落淚,哭態(tài)中甚或時(shí)露嬌態(tài)、嗔態(tài)、慍態(tài)、悲態(tài),其美在心,在情意,在女兒態(tài)。至于寶釵,可惜了個(gè)美人胚啊,心在仕途經(jīng)濟(jì),被功名利祿的韁繩捆住了本真之心,失去了天真無邪的女兒“態(tài)”,即使品貌綽約超群,卻也遜色三五分了。
今說劉備之哭,羅氏約略狀其形態(tài)、姿態(tài)、情態(tài)、意態(tài)、神態(tài)、心態(tài)……一一交互呈現(xiàn),在在栩然如生。男兒哭態(tài),英雄之淚,逸態(tài)橫生,別有一番人情世態(tài)和骨干氣息。哭態(tài)之美,首先在真,在自然,在情感收放自如的本然狀態(tài),在人性優(yōu)點(diǎn)和弱點(diǎn)相與糾結(jié)終而顯示人間暖情的本色流露。
且說時(shí)值秋末冬初,涼風(fēng)透骨,黃昏將近,哭聲遍野。劉備戰(zhàn)事失利,倉促撤軍,但不忍心丟棄十?dāng)?shù)萬百姓,自引三千余軍馬,一程程挨著往江陵進(jìn)發(fā),然而,“正行間,忽然一陣狂風(fēng)就馬前刮起,塵土沖天,平遮紅日。”時(shí)簡雍袖占一課,卜為今夜大兇之兆,力勸“主公可速棄百姓而走”。劉備哪里肯聽其勸,說“百姓從新野相隨至此,吾安忍棄之?”簡雍為之非常著急,再次苦勸:“主公若戀而不棄,禍不遠(yuǎn)矣。”正商議欲駐于前面當(dāng)陽縣景山,“只聽得西北喊聲震地而來。玄德大驚,急上馬引本部精兵二千余人迎敵。曹兵掩至,勢不可當(dāng)。玄德死戰(zhàn)。正在危迫之際,幸得張飛引軍至,殺開一條血路,救玄德望東而走。”待歇馬稍定時(shí)——
看手下隨行人,止有百余騎;百姓、老小并糜竺、糜芳、簡雍、趙云等一干人,皆不知下落。玄德大哭曰:“十?dāng)?shù)萬生靈,皆因戀我,遭此大難;諸將及老小,皆不知存亡:雖土木之人,寧不悲乎!”
眾人“戀我”卻遭此大難,十余萬生靈竟“不知存亡”,滿目凄惶,悲從中來,因此當(dāng)眾“大哭”。愚發(fā)現(xiàn),歷史深處的英雄,當(dāng)痛感黎民百姓的苦難時(shí),敢于放聲大哭,也是一種勇氣,一種豪邁,一種浩然之氣。
搵一掬英雄之淚,吐一腔坦誠之言,哭態(tài)真切自然,一如常人常態(tài)。羅氏沒有過度的鋪張渲染,也沒有敷衍痛苦萬狀的內(nèi)心情緒,平平寫來卻情態(tài)躍然紙上,筆致多有留白則漫出人性的溫度。情因憂起,言以情發(fā),讀來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不覺間令人怦然心動(dòng)。
說來也怪,與此場景相與對(duì)照的又一情景,劉備一反常態(tài),甚至有違人性和人情,竟以非常之舉表行外之意,以非常之態(tài)示態(tài)外之慰,一時(shí)著實(shí)叫人捉摸不透頗費(fèi)思量。
是說趙云浴血奮戰(zhàn)乃至在夜戰(zhàn)中“與曹軍廝殺,往來沖突,殺至天明,尋不見玄德,又失了玄德老小,云自思曰:‘主公將甘、糜二夫人與小主人阿斗,托付在我身上;今日軍中失散,有何面目去見主人?不如去決一死戰(zhàn),好歹要尋主母與小主人下落!并立下誓言:我上天入地,好歹尋主母與小主人來。如尋不見,死在沙場上也!”
趙云趙子龍,真英雄也。單騎救主拼殺無數(shù)血染戰(zhàn)袍,僥幸危境得援死里脫生,縱馬躍過長坂橋遽行二十余里幸與劉備會(huì)合。斯時(shí)悲欣交集憂患猶釋,自當(dāng)一吐彼時(shí)思念之痛或一泄郁積難解的心中悲情,豈料劉備異乎尋常別起波折:
愛將生還得歸,他哭了;
糜夫人拼死救子壯烈投井,他卻沒有哭;
愛子一時(shí)不見動(dòng)靜,恐已生命不保,他也沒有哭;
其實(shí)“阿斗正睡著未醒”,兒子生命無虞,他不哭,也不喜,想不到一仁慈者突如其來竟會(huì)作出如此非常舉動(dòng)——
云喜曰:“幸得公子無恙!”雙手遞與玄德。玄德接過,擲之于地曰:“為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趙云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云雖肝腦涂地,不能報(bào)也!”
前之誤傳子龍“反投曹操”,連張飛等也深信不疑,唯劉備堅(jiān)信“子龍從我于患難,心如鐵石,非富貴所能動(dòng)搖也。”“子龍此去,必有事故。吾料子龍必不棄我也。”
愛將終于生還,他哭了。劉備本就好哭,聽聞夫人慘死戰(zhàn)亂,焉能不悲不哭?又親見兒子生死未卜,又焉能不急不哭?是不是羅氏于此惜墨如金,有意不著一字而以大片留白激發(fā)讀者想象呢?
宋邵雍有詩《知人吟》曰:“事到急時(shí)觀態(tài)度,人于危處露肝脾。”當(dāng)時(shí)劉備一時(shí)落敗,軍民離散處境危急,但為人處世依然;情理互融肝膽相照,即使態(tài)度異于常理、常情、常態(tài),也必然寓有個(gè)中緣由,或出乎情勢變化的非常態(tài)表現(xiàn)。因之,愚也不知可否,只能發(fā)揮想象,猜度一二,以解其中奧妙。
人到情緒激越時(shí),也許會(huì)說不出話來;人到極度悲傷時(shí),感情沉淀于胸,也可能不哭,不言,處于沉默狀態(tài)。劉備初因“老小”隨軍失散后“不知下落”“不知存亡”而“大哭”過,是情動(dòng)于衷而發(fā)之于聲,人之常情也。一旦得知子存妻亡,消息突如其來毫無心理準(zhǔn)備,悲痛沉郁抑之于內(nèi)心,情感陡轉(zhuǎn)而無所發(fā)落,情至深處欲哭無淚,沉默盈積語噎默聲,恰如古人所言:“意致凄然,妙在含蓄。”水停以鑒,火靜而明。水在平靜時(shí)方能照見萬物,火在靜止時(shí)最為明亮,看似無依無憑無聲無息,實(shí)有至情至理在啊。
想我年少初讀三國,驀見劉備擲子于地的非常之舉,不無驚愕且久以詬病屢屢責(zé)之:你為人父,親情呢?即為常人,人性呢?萬一發(fā)生意外,你對(duì)得起舍身救子的夫人嗎?你對(duì)得起舍命救主的將軍嗎?你有錚錚俠骨,那么寸寸柔腸呢?你是憐惜將才有儒家風(fēng),那么“幼吾幼”的仁愛之心呢?如此薄情,如此冷酷,凡欲成就大事者非得犧牲自己的親情放逐兒女之情嗎?凡此種種不時(shí)糾纏于我解不開理還亂的繁雜思緒之中。今屆晚年歲暮重讀三國,好像多了一個(gè)心眼,不再單純用線性思維來評(píng)判事物和臧否人物了。
那么,劉備這一擲子于地的反常之舉,到底應(yīng)作何解釋呢?
16
讀三國思之夜深,一宿夢酣黎明即起。時(shí)值早春天氣,風(fēng)其料峭,乍暖還寒,推窗竟見漫天皆白,周遭冰雕玉砌晶瑩剔透,好一派江南雪意!我居水岸有臘梅兩株,花蕾迎雪爛漫綻放。雪色把盤曲的虬枝勾勒出黑白相間的靈動(dòng)線條,雪凝繁花寒浸嫩黃,漫出淡淡幽香清迥獨(dú)出,樹姿花容較之暖晴常態(tài),別饒一種凌風(fēng)傲雪的骨韻之美。
驀然間,一暈靈光乍現(xiàn),愚思豁然似有所悟,探索深研的思路開闊了。
一樹寒梅雖經(jīng)風(fēng)欺雪壓,卻異態(tài)紛呈亂花交枝,蕊間碎玉妝點(diǎn),一一染成香雪。較之于晴光明艷,平添雪里精神。
花如是,人不亦如是嗎?
由此想到當(dāng)時(shí)憩于一棵大樹下的劉備,驀見趙云,感極而泣,屬常態(tài);聞夫人慘死,竟然無語,也不哭,原來于危難之時(shí),有一種精神支撐著他的靈魂,這時(shí)即以非常態(tài)強(qiáng)抑內(nèi)心悲痛之情啊;至于擲子于地的驚心之舉,屬常人更難以理解的非常之態(tài)了。細(xì)想起來,糜夫人當(dāng)時(shí)遇見趙云時(shí)的一番言語袒露了她的心跡:“妾得見將軍,阿斗有命矣。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飄蕩半世,只有這點(diǎn)骨血。將軍可護(hù)持此子,教他得見父面,妾死無恨!”她之所以不聽趙云再三勸言上馬突圍逃命,實(shí)出乎愛子和愛夫的雙重感情,既體諒為夫“飄蕩半世”的艱辛,又拼將一死確保將軍全力以救劉氏一脈骨血,也以一種精神力量勇決若是,真一女中丈夫也。當(dāng)時(shí)劉備面對(duì)一死一活的現(xiàn)實(shí)景況,心態(tài)微妙五味雜陳,喜之極,悲也至極;感之極,傷也至極。物極必反,情極必異。當(dāng)是時(shí)也,人心呈多緒多端的復(fù)雜情狀。情通款曲形之于言行舉止的外在表現(xiàn),羅氏若按常人常態(tài)狀摹人物,反倒不合情理,更難以表現(xiàn)人物的心態(tài)和精神了。
觀其“態(tài)度”,行狀若相反相違;度其“肝脾”,情態(tài)卻始終如一,但表現(xiàn)出來,仿佛年代久遠(yuǎn)的模糊銅鏡映照出來的影像,是也若非,非也若是,朦朧間猶覺是是而非又非非而是;仿佛一喉異曲,正言若反,反言若正,交響間猶覺正反相和而旨?xì)w同一。這就把人物的復(fù)雜心態(tài)和精神狀態(tài)惟妙惟肖地呈現(xiàn)出來了。
這正是羅氏用筆的高妙之處。“常態(tài)”與“非常態(tài)”,庶幾是兩個(gè)極致,看似決然不同,卻能在藝術(shù)辯證法中奏出正反相和或正反轉(zhuǎn)換的審美效果。愚今思之,劉備在這一非常時(shí)間和非常場合,有三種社會(huì)角色:一為主帥;一為丈夫;一為父親。當(dāng)三種角色一旦重疊在共時(shí)性空間時(shí),對(duì)同一事件的情感態(tài)度即會(huì)發(fā)生微妙的變化:作為一軍主帥,且處兩軍交戰(zhàn)的緊急關(guān)口,在“價(jià)值”的天平上,一端是愛將,一端是妻孥,二者孰重孰輕?但作為丈夫和父親,在“情感”的天平上,依然一端是愛將,一端是妻孥,那么,二者又孰重孰輕?三種社會(huì)角色一時(shí)疊合于一身,權(quán)衡輕重作何態(tài)度,豈不太難了嗎?其實(shí),感情之輕重與否無關(guān)緊要,而情感態(tài)度則因人因事因時(shí)因地隨機(jī)變化,表現(xiàn)方式也因之各呈異態(tài),或正或反或正反交互,無一不以角色的轉(zhuǎn)換和內(nèi)心活動(dòng)的起伏,以及多重矛盾心理的糾纏和粘著,表現(xiàn)為行為和感情狀態(tài)的多重性和多態(tài)性。于是乎,復(fù)雜多元的生命氣象出焉,精彩紛呈的戲劇化情景現(xiàn)焉。
不是嗎,劉備是時(shí)潰不成軍,形勢危急,前無目標(biāo)后有追兵,軍民離散了,夫人慘死了,盡管趙云得歸,孺子得救,但角色轉(zhuǎn)換間情摧肺腑一時(shí)何以為言?兇吉未卜痛苦萬狀一時(shí)何以為系?當(dāng)他惴惴然從趙云手中接過“睡著未醒”的兒子時(shí),心態(tài)交渾的憂喜,心志沉浮的瞬間,心思掙扎的糾結(jié),心情起伏的涌動(dòng)……一切顯意識(shí)如匆匆過客,熙熙攘攘你搡我擁,不及停歇即喚醒郁積內(nèi)心深處的潛意識(shí),慨然與之牽手并以非同常態(tài)的表達(dá)方式,化為斯人于常人難以理解的言行了。
從羅氏寫作的審美形態(tài)看來,一“擲”一“言”,既與趙云奮突重圍舍命救主而義薄云天的壯舉,是一種響應(yīng),一種慰藉,有疼惜愛將的心情在,即時(shí)釋放出來的愧疚心情也在;又與孺子逃過一劫生命無恙的幸運(yùn)和命數(shù),是一種感動(dòng),一種寬慰。然而,復(fù)雜人性此消彼長的閃現(xiàn)又難以兼賅兩全,因而呈現(xiàn)出來的外在狀態(tài)就異乎尋常了。
愚又想,為父擲子于地而竟然于夢中未醒,可見在將軍和眾人面前也有故意作態(tài)的用意,正如詩道:“無由撫慰忠臣意,故把親兒擲馬前。” 何況又故意說道:“為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為父的對(duì)稚子的責(zé)備口吻,分明有一種愛憐在,盤桓胸中的牽掛和慶幸思緒也在,看似反常卻正常,道是無情實(shí)有情。
到底不可以凡俗者論,有的時(shí)候,人之為“人”,英雄氣也搵不住兒女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