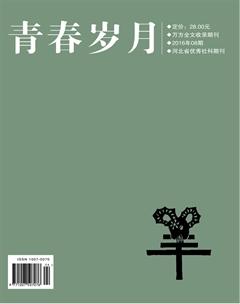白居易閑適詩精神內涵矛盾性研究
許慧玲
【摘要】白居易的在他任江州司馬期間所做的閑適詩,既有豁達樂觀、享受風光及生活的,也有孤獨寂寞、憂傷不能為國效力的。在此期間,曠達的心態與感傷情緒交織,情緒既有享閑適生活的閑適舒雅,又有理想失落的哀傷愁緒。本文將探究白居易任江州司馬期間閑適詩精神內涵的矛盾現象及其背后的原因。
【關鍵詞】白居易;閑適;矛盾
白居易的在他任江州司馬期間所做的閑適詩,既有豁達樂觀、享受風光及生活的,也有孤獨寂寞、憂傷不能為國效力的。在此期間,曠達的心態與感傷情緒交織,情緒既有享閑適生活的閑適舒雅,又有理想失落的哀傷愁緒。白居易的閑適詩寫作起于貞元十六年,止于會昌六年,筆者在此重點研究白居易任江州司馬期間即元和十年至元和十三年間的閑適詩創作的精神內涵矛盾性。
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刺殺,白居易急請捕賊,以雪國恥,觸怒了執政群僚;白母看花墜井而逝,白居易著“賞花”“新井”詩,被認為有害名教。中書舍人王涯上述追論白居易“所犯狀跡,不宜治郡”,被追貶為江州司馬。志向高遠忠誠諷諫的白居易慘遭貶謫,路途奔波、舟車勞馬,詩人不得不面對理想與現實的沖突。他寫了不少雜律詩、感傷詩表達了他的憂愁心情,但是他的閑適詩別有一番風味。閑適詩是白居易泄導情緒的一個途徑,由此受到詩人的喜歡和重視,這種情景一直持續到白居易的晚年。在這些詩作之中,我們可以看到詩人的內心寫照,一方面,白居易遭貶卻調整心態樂觀積極,另一方面,他不時因孤獨、不能濟世而憂愁。
部分閑適詩傳達了詩人遭貶卻豁達樂觀,能在自然中徜徉表達達觀、適意之情懷。在優美的環境,自由輕松的心態下,做了不少悠閑適意的詩作。被貶去江州的路上。“帆影日漸高,閑眠猶未起。……何況不失家,舟中載妻子。”仕途失意,原應是憂傷苦悶,加之鞍馬舟楫,更添疲憊惆悵。然而,詩人慵懶晚起,閑情問擺渡人在哪。船上炊稻烹鯉,飽食再以秋江水盥漱。遭貶謫,卻無失意之傷感,而是抒發了他的滄浪意,更是豁達地認為舟中載著妻子不失家。貶謫給他帶來了憂痛,但此時,江州路上,他已調整心態,能徜徉自然,適意賞美景了。而在他到達江州貶所后,所作的描寫江州富饒的物產以及秀美的風景的閑適詩,傳遞了其陶醉在閑適、悠游的生活中的愜意滿足的心情。然而,初貶時,他“望秦嶺上回頭立,無限秋風吹白須。”凄愴悲傷溢于言表,隱含了仕途不得志不能兼濟天下理想破滅的哀愁及對前路的擔憂;同樣是被貶書下,前往江州,時間間隔不遠,白居易卻十分哀痛悲傷。“人煩馬蹄跙,勞苦已如此。”“三聲猿后垂鄉淚,一葉舟中載病身。”《舟行江州路上作》里的悠閑自適已不在,這里,白居易感慨路途勞苦,行途遙遠奔波,路途的遙遠與奔波勞碌渲染了濃烈的凄愴之情。也許是山高水阻,實質也許是貶謫的悲憤郁悶,使詩人的詩充滿了悲切。
貶謫在江州后,詩人以閑適之心寄情大自然,氣定神閑。“時傾一杯酒,曠望湖天夕。”元和十一年,他已任江州司馬,但他可以飲酒望湖,詠詩觀飛翮,悠閑、細致地品味江州生活,清靜自由。“及茲多事日,尤覺閑人好。”作者在山水中陶醉了,感受并享受“閑適”的樂趣。他認為這種閑隔絕了塵世,年過不惑,歸山不老,似乎,詩人想享受歸山的生活,以閑為趣。但相反的,貶謫在江州后,身處逆境,遠離朝廷,部分閑適詩也傳遞了詩人強烈的孤獨感。這些詩里面,孤獨感彌漫了整首詩,如《北亭獨宿》、《山中獨吟》、《霖雨苦多江湖暴漲塊然獨望因題北亭》等。詩題直接運用“獨”字,這個獨,不僅是作者身體上的獨,更是內心上的孤獨。“孤”、“獨”“寂寞”、“靜”、“愁”濃烈地渲染孤獨的意緒,“獨到山下宿,靜向月中行”,“單幕疏簾貧寂寞,涼風冷露秋蕭索”。這些孤獨感,或是表達了作者或詩人獨自吟味人生、感受禪意的境界,表達委順任運、隨遇而安、知足保和的思想,如“恐為世所嗤,故就無人處”,“舊西濫水江,獨行吟舊詩”;官曹冷落,世態炎涼的感傷之情,“獨有秋江水,煙波似舊時”,“蕭條殘活計,冷落舊交親”;對親友思念之情,“此去更相思,江西少親故”,“共思除醉外,無計奈愁何”。白居易的孤獨情感、愁情意緒幾乎彌漫了所有江州時期創作的詩歌中,既有仕途失意、遠離親友的心靈孤獨,也有遭遇冷落、人情冷暖的人生感慨;既有孤寂的感傷,也有獨自品味自我、反省內心的安閑寧靜。這種情緒正是詩人出世之思和入世之心集于一身的矛盾表現。
我們可以看到,在他任江州司馬期間,曠達的心態與感傷情緒交織,情緒既有享閑適生活的閑適舒雅,又有理想失落的哀傷愁緒。白居易確是此般矛盾的。那么,為什么白居易會既有出世之思又有入世之心呢?
首先是“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士人精神,做官是每個士人夢寐以求的事。加之白居易生于“世敦儒業”的下層官吏家庭,“仆本儒家子,待詔金馬門”,因此在他思想中,是以儒家為主導的,而儒家強調入世精神和個人社會責任。后來被貶江州,白居易尚年輕,正直風華,卻面臨突然的仕途失意,白居易十分憤懣憂愁,或許他還未能對被貶江州曠達。第二是作者的出世的濟世精神。正如他坦言“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謂之閑適詩,獨善之意也。”黑暗的社會現實、無情的官僚體制、百姓的窮苦流離使得白居易心生哀憐與憤怒。具體而言,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亂”之后唐朝由衰落到中興的階段。這段時期,藩鎮割據、宦官專權、“二王八司馬”事件相繼發生,深深地激發了白居易的兼濟精神。即便被貶至遠離朝廷的江州,但是寒微的家世,幼年艱苦生活的經歷,使得白居易不愿意重復以往的貧困生活,歸隱于山林并不能解決溫飽問題。“欲作云泉計,須營伏臈資”、“非無解掛答纓意,未有支持伏臘資”,可見,解決溫飽問題是歸隱必須解決的,或許這也就解釋了為何白居易居住江州時不時會談到“須營伏臈資”。 物質方面的需要滿足不了、實現不了,于是內心就有了更多的痛苦,這也可以算是其矛盾心態形成的一個原因。
其次,白居易為何會遭貶卻仍然豁達樂觀呢?在元和十二年的《與元微之書》中他隱露了達江州后有三泰。一是家人“悉置在目前,得同寒暖饑飽”;二是飲食皆美,且免求人;三是環境幽雅,可以終老。也許是因為這三泰給他帶來的安慰,他逐漸擺脫悲苦的情緒,開始找尋生活中的樂趣來寬慰自我。他認為:只有擺脫了“世網”和“險艱”的人生才能“意自足”。這是江州三泰給他帶來的生活中家人、飲食、環境的安慰。其次是好友的陪伴吟賞,白居易與好友元稹的友情可謂是一段佳話。白居易和好友元稹共同悠游足歲,留下了許多留戀光景的篇章。在與志同道合的好友的游玩下,白居易緩解了不少仕途失意的哀愁,轉而徜徉大自然,欣賞自然的美麗。第三是佛教思想對白居易的影響。正如《舊唐書·白居易傳》中記述了他任江州司馬時的一段生活:“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為事,都不以遷滴介意。在濫城,立隱舍于廬山遺愛寺。……至于愉然順適之際,幾欲忘其形骸。”白居易在江州時跟佛家思想有了更為深入的接觸并鐘情于佛家思想。佛家思想中超越世俗名利,達觀隨緣,自適以求得空靈之心的心性觀使白居易從名利中解脫出來。正如在貶謫江州四年所作詩句,“官不官,系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他的心態調整了,“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歲月,或免罷之后,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往。”白居易憑借著外在條件,如富饒的江州物產、秀美的風景、家人的安定以及與朋友的志同道合,加之以內心達觀的積極調節自我的心態,使他慢慢恢復過來。
貶謫江州期間是白居易一生中關鍵的時期。這一時期,他創作了不少悠閑自在、吟賞自然的閑適詩,但同時,他的閑適詩又透露著他的孤獨寂寞,有理想失落的哀傷愁緒。心態的矛盾性構成了白居易思想的復雜性,研究這一時期的閑適詩創作能深入、多方面探測白居易的內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