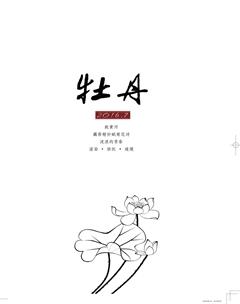淺析權德輿大量寫作銘文序的原因
楊萍
權德輿,中唐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全唐文》將其文章編為二十七卷,其中銘文序共八十篇,數(shù)量相當可觀。究其大量創(chuàng)作銘文序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權德輿當時為文壇盟主,文章久負盛名,具有較大的影響力;二是因其人格魅力,雖然身居高位,卻為人謙和。
一、權德輿銘文序簡介
權德輿所作銘文序是其文章的類型之一,《全唐文》將其文章編為二十七卷,其中銘文序共八十篇,碑銘序文三十篇:遺愛碑銘序文兩篇、紀功碑銘序文一篇、先廟碑銘序文三篇、神道碑銘序文二十二篇、唐故章敬寺百巖大師碑銘序文一篇、唐故太清宮三洞法師吳先生碑銘序文一篇。墓志銘序文四十六篇,在權德輿銘文序言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內(nèi)容相對也更為豐富和復雜。另外還包括塔銘序文三篇,碣銘序文一篇。序言中的主人公包括權德輿的一些好友、同僚,如陸參、唐款、賈耽、張薦、戴叔倫和仲子陵等。
二、權德輿大量寫作銘文序的原因
(一)文壇盟主的影響力
權德輿仕宦顯達,并以文章著稱。論其家世,自十二世祖前秦仆射安邱公權翼以來,就數(shù)代為官,且自先世就以儒學傳家,德行清明,家風雅正。如其父權皋,曾為安祿山的幕僚,“安史之亂”爆發(fā)前,以逃離叛逆的義勇行為而得到時人的稱贊。在這樣德行、政事、文章顯世的家風影響之下,權德輿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十五歲為文數(shù)百篇,并將自己寫的數(shù)百篇文章編為《童蒙集》十卷,聞名士林。韓愈《唐故相權公墓碑》云:“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吊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楊于陵《祭權相公文》稱,權德輿十五歲,即以文章“飛聲天下”。《舊唐書·本傳》云:“德輿生四歲,能囑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五為文數(shù)百篇,編為《童蒙集》十卷(今已佚),名聲日大。”又《新唐書·本傳》云“德輿七歲居父喪,哭踴如成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時至中年,權德輿以文名應召入朝,并且自此之后,仕途通達,久居要津。在當時文壇上,他也是十分活躍的人物,且是較早提倡革正文體的作家之一,加之他特殊的政治地位,時人推其為當時的文壇盟主。《舊唐書·權德輿傳》亦云:“于述作特盛,六經(jīng)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記為請者十八九,時人以為宗匠焉。”又《贊》云:“權之藻思,文質彬彬”。其文弘博雅正,溫潤周詳,公卿侯王、碩儒名士之碑銘、集紀,多出其手。可見,在中、晚唐人心目中,權德輿是貞元、元和間的文壇盟主,古文創(chuàng)作大家,且在其所有的古文作品中集序多,碑志多,二者幾乎囊括了當時所有名流,是當時他家所不可比擬的,這些都表明了權公在當時文壇的盟主、大家地位。故宋代姚鉉在《唐文粹》序中稱贊說:“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至于賈常侍至,李補闕翰,元容州結,獨孤常州及,呂衡州溫,梁補闕肅,權文公德輿劉賓客禹錫,白尚書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雄杰者歟!”
因為權德輿的文壇盟主地位,如上文所云“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記為請者十八九”,可見得權公銘文已成為時人的榮耀。縱觀權德輿這八十篇銘文序言,傳主涉及當時朝廷要員杜佑、渾瑊等人,也涉及當時的文壇大家姚南仲、戴叔倫等人,幾乎囊括一代名流。設立家廟,為自己的先人撰寫廟碑,是一件非常重要之事,尤其是那些達官顯赫更是將其看得意義非常,正如權德輿《南康郡王贈太師韋公先廟碑銘(并序)》中所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乃立宗廟,以安神明”。唐中書令南康郡王邀請權公為之先人太師韋公撰寫“德厚流光,追養(yǎng)繼孝”。另有元和五年(810年),相國司空燕國公在京師蘭陵里設立新廟,亦請權公為之先人撰寫銘文,以永代德。請文壇盟主,同時又身兼一朝宰相的權德輿撰寫碑銘不得不說是一種莫大的榮耀。
(二)居高位而人謙和
在為官的一生中,權公時刻心系國家和百姓的安危,在當時國民的心中他雖位居高官,卻為人謙和,從不居官自傲。唐德宗貞元八年(792年),權公被征為太常博士,因得到朝廷的重視,同年六月即轉為左補闕。在補闕任上,權公盡責盡職,“閑雅存誠,心常坦夷而不離法度,操本堅峻,而盡歸忠厚”(王仲舒《祭權少監(jiān)文》)。七月,河南、河北,江、淮、荊、襄、陳、許等四十余州發(fā)生大水,毀壞了良田和房屋,災民流離失所,他立即上《論江淮水災上疏》,建議德宗皇帝派遣能干的使臣趕赴災區(qū),救濟災民,并主張減輕災區(qū)人民的賦稅。同年七月,司農(nóng)少卿裴延齡因巧幸恃寵,判度支,兼管國家財政收支。針對這一情況,權德輿不顧個人安危,先后兩次上疏唐德宗,義正詞嚴,直言不諱地反對裴延齡任職,陳述度支的重要性,擇人必須慎重。貞元十年(794年),權德輿轉起居舍人,知制誥。貞元十八年(802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后拜禮部侍郎,轉兵、戶、吏三曹侍郞、太子賓客,遷太常卿。在此期間,他大力選拔人才,舉賢任能,且不管門第等級,只要有德,一律任用,并反對徇私舞弊。他曾三次典士舉,凡“舉士于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布衣不用;既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jīng),在得人,不以員拘”。在他的主持下,發(fā)現(xiàn)和造就了很多有用之才,多達百余人,《新唐書》中曾云:“知禮部貢舉,真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為公卿、宰相。”
權德輿一生樂交名士,這也是體現(xiàn)其人格魅力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權公一生交友甚多,在此不一一說明,試舉幾人,以彰其人格魅力。唐次,建中初進士,官至禮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權德輿在少年時代游于江湖之時,就已經(jīng)與唐次結為莫逆之交,二人同為文學和政治之同道,權公引唐次為知音,唐公卒后,權公為文《大理評事唐軍墓志銘(并序)》。崔元翰,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辛酉科狀元及第,為人性喜孤獨,極少結交,一心于翰墨,好學不倦。在建中元年(780年)之前,權公居于丹陽練塘之時,讀書交友,游于江湖間,二人在此時結為朋友,且二人之友誼一直持續(xù)到崔元韓去世。賈耽,唐代地理學家,德宗貞元九年(793年)拜相,權公與賈耽為官場同僚,且二人亦為忘年之交,有很深的感情,賈公去世之后,權公親自為其撰寫《賈公墓志銘(并序)》。姚南仲,中唐著名文人,權德輿與之結交甚早,早在大歷十四年(779年),姚公出為海鹽令時,權德輿正僑居于吳讀書交友,二人就已經(jīng)相識,姚公極為賞識權公,故與其結為忘年之交,且對權公有提攜之恩,二人友誼一直持續(xù)到姚仲南去世,權公為姚公撰有《姚公神道碑銘(并序)》一文。戴叔倫,大歷、貞元年間重要詩人,貞元二年(786年),二人同在洪州,在此相識,結為知己,唱酬往復,從此結為終身摯友,戴叔倫去世之后,權德輿為文《戴公墓志銘(并序)》。
權德輿位居高官,且為人謙虛,性格溫和,一生結交名士無數(shù),從不輕易拒絕請銘文者之請求,往往有請之撰寫銘文者,權公都欣然應之,并認真書寫。這也是權公至今留有數(shù)目多達八十篇銘文(并序)的一個重要原因。
(河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