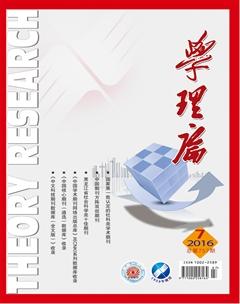孫中山論香港問題的三個向度
陳鴻惠
摘 要:香港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策源地以及革命運動的指揮部。孫中山把振興中華、收復失地作為畢生奮斗目標,并在其革命學說中針對香港問題提出許多精辟見解。孫中山有關香港的重要論述可以歸納為三個向度,即愛國主義的價值觀、主權在中的政治論、中西兼容的治理觀。這些閃耀著孫中山思想光輝的重要觀點,對于當前持續推進“一國兩制”的香港實踐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關鍵詞:孫中山;香港問題;向度
中圖分類號:D676.5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6)07-0068-03
香港問題是中國近現代民族民主革命不可回避的重要政治問題,也是孫中山始終關注和論及的重要思想內容。本文試從價值觀、政治論、治理觀三個向度,探析孫中山有關愛國主義、主權在中、中西兼容的香港問題觀。
一、愛國主義的價值觀
愛國主義是孫中山身體力行、始終如一的價值觀。孫中山認為,維護國家統一是愛國主義的核心要素和顯著標志;香港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傳統其來有自、歷久彌堅;收回香港是全體中國人團結、奮斗、救中國的重要目標。
(一)維護國家統一是愛國主義的集中體現
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主流趨勢,支持國家統一既是對歷史演變大勢的認識,也是對愛國主義價值的弘揚。
首先,中國歷史不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簡單循環。分裂只是中國歷史的現象和支流,只是暫時的亂象;統一才是中國歷史的規律和主流,才是長久的趨勢。“由此可知中國的各省在歷史上向來是統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統屬的;而且統一之時就是治,不統一之時就是亂的……中國眼前一時不能統一,是暫時的亂象,是由于武人的割據。”[1]746統一與分裂不僅事關封建王朝的治亂興衰,更是中華民族能否復興的關鍵所在。“統一成而后一切興革乃有可言,財政、實業、教育諸端始獲次第為理,國民意志方與以自由發舒,而不為強力所蔽障。”[2]51
其次,對國家統一的追求已經沉淀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和中國人民的歷史意識。這正是中華民族雖然在歷史上屢遭戰亂但是仍舊渾然一體的重要原因。“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地印在我國的歷史意識之中,正是這種意識才使我們能作為一個國家而被保存下來,盡管它過去遇到了許多破壞的力量,而聯邦制則必將削弱這種意識。”[3]258-259
最后,愛國主義的核心要素是堅持并維護國家統一。這是劃分愛國者與否的最重要標準,也是辨識敵我關系的分水嶺。中國人民深惡痛絕一切背叛和分裂祖國、損害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行徑,鼓吹分裂者就是野心家。“我們推翻清朝,承繼清朝的領土,才有今日的共和國,為什么要把向來統一的國家再來分裂呢?提倡分裂中國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據。”[1]747
(二)香港中國人一向富有愛國主義傳統
孫中山對香港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傳統有著深切的認識和由衷的稱贊。
首先,香港的中國工人抗法反英斗爭使孫中山認識到中國人的覺悟性和團結力。早在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香港的中國工人就以拒絕修理法國船艦的實際行動支援祖國內地的抗法斗爭,并由此遭到英國殖民當局的殘酷鎮壓。當時正在香港讀書的孫中山,對于英法帝國主義的沆瀣一氣極為憤怒,更從香港的中國工人罷工運動看到了“中國人已經有相當的覺悟”和“種族的團結力”[4]158-163。
其次,香港中國人長年支持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斗爭。孫中山充分利用香港既毗鄰廣東卻又在清政府治外的獨特地緣優勢,使香港成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補給站。不僅興中會總部設在香港,而且廣西鎮南關起義、廣州黃花崗起義等多次武裝斗爭都在香港設立指揮部。香港中國人的愛國熱情日益高漲,不論富家巨室還是販夫走卒都給予革命運動以人力及物力支持。這些愛國壯舉也引發了英國殖民當局的戒備和打壓,此后香港中國人通過積極抗爭才迫使英國殖民當局有所收斂。“從前因各商家協助革命,為政府逮捕,今可無虞,當可與予一致行動。”[2]117
(三)收回香港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愿望
統一中國、收復疆土是孫中山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也是包括香港中國人在內的中國人民的共同愿望。“‘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5]373
“中國本部形式上向來本分作十八省,另外加入東三省及新疆,一共是二十二省;此外還有熱河、綏遠、青海許多特別區域,及蒙古、西藏各屬地。”[1]746在孫中山的內心深處,香港、澳門、臺灣等地從古至今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收復港澳臺將是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的重要歷史坐標。“惟俟數年后,中國已臻強盛,爾時自能恢復故土。中國有四萬萬人,如數年以后,尚無能力以恢復已失之疆土,則亦無能立國于大地之上。”[6]413-414
在孫中山建國大業的日程表上,首要是統一中國內地,結束南北方的封建軍閥割據局面;其次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治外法權、關稅特權和已割讓領土;最終實現民族、領土、軍政、內政、財政的完全獨立與統一。“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2]52
二、主權在中的政治論
在孫中山看來,英國侵占中國香港是于法無據、于理無由的野蠻行為;英國對香港的統治并未改變中國擁有香港主權的法理和歷史事實;只有打破封建軍閥以及其背后的帝國主義,才能徹底解決香港問題。
(一)香港系為英國無理侵占
英國在侵占香港后,刻意強調香港的主權和治權均屬于英國女王。孫中山卻尖銳指出,香港問題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的結果,英國侵占香港是不合理、不合法的野蠻行為。
首先,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是造成中國領土分崩、百姓遭殃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對領土擴張和殖民利益貪得無厭、得寸進尺。“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于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1]14另一方面是封建主義腐敗無能、喪權辱國,出賣人民利益以討取列強歡心。“上則因循茍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翦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于鄰邦,文物冠裳,被輕于異族。”[1]14
其次,英國侵占香港是出于強權而非公理。英國在西方列強中最早以武力手段逼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非法攫取香港并實施殖民統治。孫中山明確指出中英“江寧條約”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尤其是在鴉片戰爭以后,國勢日蹙,國本動搖,土地淪于異族者,幾達三分之一,如英國之割香港……受兵力脅迫而償外人之款者,如江寧條約賠款二千一百萬兩……列強憑借不平等條約,得在中國內地設立工場……”[7]43孫中山強烈譴責英國對中國輸入鴉片、侵蝕領土的無理霸道行為。“所以奪我香港……據何公理?逼我吸銷鴉片,劃我國土地為彼勢力范圍,據何公理?”[8]43
(二)香港主權始終屬于中國
雖然香港為英國所侵占并經受殖民統治,但是主權無可置疑屬于中國,中國遲早要從英國手中收回香港。
在孫中山的領導下,興中會于1894年在美國檀香山成立并于1895年將總部設在香港。《香港興中會章程》明確將香港視為中國領土,總部設在香港即是總部設在中國,“會名宜正也。本會名曰興中會,總會設在中國,分會散設各地。”[9]22
在對外交涉中,孫中山一再強調中國終歸要收回香港。在與英國政府代表的談話中,孫中山坦率告知:“現在你們還要來取西藏。我們中國此刻沒有收回領土的力量,如果有了力量,恐怕要先收回英國占去了的領土罷。”[1]664在此后與外國記者的談話中,孫中山多次申明數年后中國人在英國的權限必然與英國人在中國的權限相等。在與日本重要人士的談話中,孫中山明確指出:“惟香港、澳門則有意收回。”[7]318
(三)解決香港問題必須打破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聯盟
孫中山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態度上經歷了巨大的思想變化。
在辛亥革命之前,孫中山把斗爭矛頭對準封建主義,雖然對帝國主義有所警惕,但是仍幻想用革命道義以及承認不平等條約來避免列強干涉中國革命。“凡革命以前所有滿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民國均認為有效,至于條約期滿而止。其締結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則否。”[6]10
在辛亥革命后,孫中山認識到革命失敗的根源在于對帝國主義的政治幻想以及與帝國主義所支持的封建軍閥的妥協。“曾幾何時,己為情勢所迫,不得已而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謀妥協。此種妥協,實間接與帝國主義相調和,遂為革命第一次失敗之根源。”[1]587在與蘇俄和中共的合作過程中,孫中山進一步認識到,若不打破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聯盟,就無法斷絕導致中國戰火連綿的根源,也無法改變中國四分五裂的局面。“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是在軍閥和那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打破了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5]338香港問題的徹底解決,有賴于消滅封建軍閥并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不過要以后真是和平統一,還是要軍閥絕種;要軍閥絕種,便要打破串通軍閥來作惡的帝國主義;要打破帝國主義,必須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條約。”[1]973
三、中西兼容的治理觀
孫中山敏銳地把握住香港問題的兩重性質,即中國主權因殖民侵略而遭到破壞,以及香港的社會發展程度領先于中國內地。孫中山從香港與內地在市政建設上的較大差距,深入比較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與中國封建主義政治制度的巨大差異,從而得出既要學習西方制度經驗又要發揚中國文化傳統的結論。
(一)香港問題的兩重性質
在孫中山眼里,香港是一種矛盾交織、角色交叉、文化交匯的多重映象。香港既是中國內地走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前車之鑒,又是中國內地地方治理的他山之石;既有歐美制度的暴風驟雨,又有中國文化的無聲潤物。
在領土和主權上,香港是中國內地全面淪為西方列強勢力范圍的前車之鑒。香港的割讓只是中國陷入被帝國主義瓜分泥淖的開始,而不是結束,侵略者的野心持續在神州大地上橫行無忌。“香港完全割歸英國,由英國人管理,是英國的全殖民地……不止是英國人在中國是這樣橫行,就是其他各外國人都是一樣。”[1]980香港問題的根本性質是中國的被侵略以及領土的被分割,這是英國人無論如何也無法掩飾的。“造成香港的原因,并不是幾十萬香港人歡迎英國人而成的,是英國人用武力割據得來的。因為從前中國和英國打仗,中國打敗了,把香港人民和土地割歸到英國,久而久之,才造成現在的香港。”[1]618
在社會發展程度上,香港的近代化程度高于苦難深重的中國內地。英國殖民當局為了鞏固在港統治,逐漸吸收香港中國人的個別上層人物參與立法及行政事務。相對于中國內地從辛亥革命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雙重奴役”轉變為辛亥革命后帝國主義列強的“多層奴役”,香港中國人的政治處境至少在表面上有所改善,其政治權利也算是聊勝于無。“就字面講,香港既是全殖民地,上海是半殖民地,上海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當然比香港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要高……香港割歸了英國……在那個立法局里頭,還有幾個中國人……還有很大的發言權,還可以議訂法律來管理香港……試問中國有沒有人在上海工部局里頭能夠有大發言權呢?中國人能不能夠在上海工部局里頭議訂法律來管理上海呢?”[1]980這種對比不是對英國殖民主義的歌功頌德或者涂脂抹粉,而是又一次從反面強調了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1]995,不論中國內地還是香港才可能真正享有地方自治的政治權利。
(二)從市政考察到政治研究
中國香港和美國檀香山一樣,在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啟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少年時期,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生活和學習,接觸并思考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萌發了改良祖國、拯救同群的奮斗目標。從美國檀香山到中國香港,孫中山的政治思想從改良興中轉為革命救國,從萌發趨于成熟。
青年時期,孫中山到香港求學,在對比其家鄉香山與香港的巨大發展差距之后,“由市政之研究進而為政治之研究”[2]115,激發了推翻專制、實行共和的革命思想。“即我于何時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是也。我之此等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兩地相較,情形迥異,香港整齊而安穩,香山反是……香山、香港相距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間在一荒島上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2]115孫中山對香港與內地發展落差的思考結果,是香港所仿效的英式資本主義政治制度遠勝于內地所奉行的封建主義政治制度。要改變中國的落后狀況,就要推翻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借鑒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中國對于世界他處之良好事物皆可模仿,而最要之先著,厥為改變政府。現社會中最有力之物,即為一組織良好之政府,中國則并無(良)政府,數百年來只有敗壞一切之惡政府。我因此于大學畢業之后,即決計拋棄其醫人生涯,而從事于醫國事業。由此可知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于香港也。”[2]115
(三)政治制度需要文化支撐
孫中山對香港與內地近代化差距的思考,并未停留于政治制度層面的原因分析,而是深入到制度背后的文化底蘊。孫中山認為,西方民主共和的制度優勢,加上中國人易于管理的文化特性,可以造成中西合璧、安居樂業的中國。“試觀海峽殖民地與香港,前者有華人一百萬有奇,后者有華人六十萬,我等未往該兩地之前情形如何不必論,今則皆安居樂業而為良好公民,可見中國人民乃容易管理者也。”[2]117
在思考過程中,孫中山跳出了以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體用之爭”窠臼,提倡中西一體、各有優劣、取長補短、相得益彰。既然中國的文化和倫理優越于西方,就應該傳承創新;既然西方的制度和技術領先于中國,就應該吸收消化。“但是恢復了我們固有的道德、知識和能力,在今日之世,仍未能進中國于世界一等的地位……恢復我一切國粹之后,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然后才可以和歐美并駕齊驅。”[1]688-689中國人傳統的倫理道德比如忠、孝、仁、義、禮、智、信等,經過適當的改造后不僅可以和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兼容并蓄,而且可以提供更加持久有效的精神支撐。“彼將取歐美之民主以為模范,同時仍取數千年前舊有文化而融貫之。”[9]560
孫中山反對從閉關自守的一個極端走向崇洋媚外的另一個極端。“中國從前是守舊,在守舊的時候總是反對外國,極端信仰中國要比外國好;后來失敗,便不守舊,要去維新,反過來極端的崇拜外國,所以把中國的舊東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國;只要聽到外國有的東西,我們便要去學,便要拿來實行。”在孫中山看來,地方自治是中華民國的建國基礎,唯有在地方實行自治才能使全國人民得以共治、共享。孫中山更是反對不顧中國的國情、社情、民情,盲目引進并照搬照抄歐美國家的政治制度。一是反對將美國聯邦制套在中國大地上,導致中國分裂成許多小的國家;二是反對封建軍閥借聯省自治之名而行地方割據之實,挑戰中央政府權威并分裂大一統的中國。
孫中山有關香港問題的精辟論述,啟發我們更加深入地思考當前“一國兩制”的香港實踐,如何處理主權與治權的關系、內地與香港的關系、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系。孫中山在香港問題上始終高揚的愛國主義旗幟,更是我們持續推進祖國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號角和先聲。
參考文獻:
[1]孫中山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孫中山全集:第7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5.
[3]孫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5.
[4]林柏克.孫逸仙傳記[M].徐植仁,譯.上海:上海民智書局,1926.
[5]孫中山全集:第11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6.
[6]孫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2.
[7]孫中山集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8]孫中山全集:第4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2.
[9]孫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