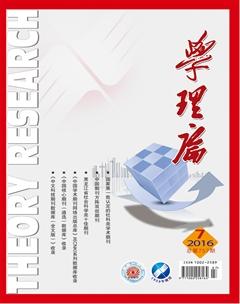王志才故意殺人案評析
黃美虹
摘 要:王志才故意殺人案,由山東省高院再審改判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同時規定對其限制減刑。該案被最高人民法院作為指導性案例,在系統內予以公布。本文將從認罪悔罪如何認定、婚戀民事糾紛及積極賠償的認定與適用、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還是死刑緩期執行的考量因素、限制減刑的考量及適用問題等幾個方面對該案進行評析,進而對我國刑法定罪量刑的影響因素有更加清晰的認識。
關鍵詞:坦白悔罪;民事糾紛;限制減刑
中圖分類號:D9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6)07-0114-02
201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第一批指導性案例,成為中國特色案例指導制度的一個良好開端。其中的第4號案例首次適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增設的死刑緩期執行限制減刑制度,對司法實踐和法學研究具有很大的指導意義。本文將運用刑法學的相關法理,對該案的判決因素進行梳理分析和解讀,以期對刑法定罪量刑的考量因素、死緩限制減刑制度及其蘊含的司法理念有更加清晰準確的認識。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志才與被害人趙某某(女,歿年26歲)在山東省濰坊市科技職業學院同學期間建立戀愛關系。2005年,王志才畢業后參加工作,趙某某考入山東省曲阜師范大學繼續專升本學習。2007年趙某某畢業參加工作后,王志才與趙某某商議結婚事宜,因趙某某家人不同意,趙某某多次提出分手,但在王志才的堅持下二人繼續保持聯系。2008年10月9日中午,王志才在趙某某的集體宿舍再次談及婚戀問題,因趙某某明確表示二人不可能在一起,王志才感到絕望,憤而產生殺死趙某某然后自殺的念頭,即持趙某某宿舍內的一把單刃尖刀,朝趙的頸部、胸腹部、背部連續捅刺,致其失血性休克死亡。次日8時30分許,王志才服農藥自殺未遂,被公安機關抓獲歸案。
山東省濰坊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9年10月14日以(2009)濰一初字第35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人王志才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宣判后,王志才提出上訴。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18日以(2010)魯刑四終字第2號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并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最高人民法院根據復核確認的事實,以(2010)刑三復22651920號刑事裁定,不核準被告人王志才死刑,發回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經重新審理認為:被告人王志才的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罪行極其嚴重,論罪應當判處死刑。鑒于本案系因婚戀糾紛引發,王志才求婚不成,惱怒并起意殺人,歸案后坦白悔罪,積極賠償被害方經濟損失,且平時表現較好,故對其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同時考慮到王志才故意殺人手段特別殘忍,被害人親屬不予諒解,要求依法從嚴懲處,為有效化解社會矛盾,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50條第2款等規定,判處被告人王志才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同時決定對其限制減刑。該案被最高人民法院作為指導性案例,向社會進行了公布。
二、案件評析
1.坦白悔罪如何認定。在司法判決中,幾乎都要考量犯罪人的悔罪態度和表現,通過對悔罪情況的考量和認定,決定是否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從輕或減輕處罰。這是刑法教育和預防功能的體現,也是公正司法的要求,一方面,能夠鼓勵犯罪分子積極進行思想意識改造;另一方面,也能夠更好地貫徹寬嚴相濟、以人為本的刑事政策。但是,“悔罪態度及表現好”如何準確地進行考量,才能達到司法功能所要達到的目的,這是量刑的關鍵所在。一般認為,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去進行考量:一是如實供述犯罪事實及作案過程的情況,包括主觀上所持的心理態度,故意還是過失;二是主動交代作案工具及與本案有關聯的人和事;三是深刻認識到其過錯及造成的社會危害性,積極采取補救措施進行賠償處理等。
悔罪態度是犯罪人的內心活動,我們只能從其外在的悔罪表現去評價和認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否真正認識到其行為的不正當性或惡劣性,并有真誠悔改和重新做人的意念,也要在具體的案件中去加以評析。犯罪人真誠悔罪,可以緩解被害人家屬的仇恨情緒,化解雙方當事人的矛盾對立,減小案件所造成的社會負面影響。但如果其行為極端殘忍和惡劣,民眾認為其“死一百次不足惜”,我們認為,即使其“坦白悔罪情況好”也不能對其從輕或減輕處罰。甚至我們也不能排除,犯罪人是為了規避或減輕法律的懲罰而偽裝悔罪,這樣其社會危險性不但沒有降低,反而更高了[1]。因此,簡單的通過犯罪人認罪服法、賠償損失等情節來認定悔罪表現是不妥當的,犯罪人可以輕易地利用悔罪表現相關減刑的規定,逃避應有的刑事責任,那么,現實結果將與刑法的初衷背道而馳。
在該案中,王志才犯故意殺人罪的事實已經認定,且手段殘忍,罪行極其嚴重,山東省中院一審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但最高院沒有核準王志才死刑,重審對被告改判死刑緩期二年執行,與其坦白悔罪行為有很大的關系。首先,他故意殺人后并沒有逃跑,逃避法律的追究,這與很多犯故意殺人罪后逃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投案自首的犯罪人的情況有所不同,從此情形看,王志才應該不存在偽裝悔罪的情況。其次,王志才次日服藥自殺未遂,被公安機關抓獲,說明他認識到自己行為的過錯性和應受懲罰性,說明其再次危害社會的可能性相對較小。同時,其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減小其給被害人家屬造成的損失及給社會造成的惡劣影響。從以上幾個方面考量,王志才是符合“悔罪態度及表現好”的情節的,所以重審改判其死刑可不立即執行。
2.適用死緩的情形分析。《刑法》第48條規定:“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對于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行。”首先,死緩的適用前提是“應當判處死刑”,其次,要考慮其是不是“必須立即執行”。一般認為,犯罪人罪行極其嚴重,人身危險性非常大,不立即執行就會對社會的和諧安定,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及公共利益等造成很大的威脅,就應該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那么,什么才是死緩需要考量的“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情形呢?在這方面,法律沒有明確的規定,具體的情形也會因個案而異。刑事司法實踐過程中,一般認為,以下情形可視為“不是必須立即執行”:一是犯罪后主動歸案自首,坦白悔罪,積極賠償損失,消除犯罪影響的。二是由于被害人的原因或過錯導致被告人激情、憤怒犯罪的。三是有令人憐憫的情節的,如家境貧困等原因。當然具體個案中,還可能存在其他的情形。
在一些罪行極其惡劣的刑事犯罪中,人們往往對判處死刑和死緩的態度差異非常大,因為這很有可能造成犯罪人“生死兩重天”的結果,因為二者在執行上有天壤之別。死刑即死刑立即執行,而死緩在緩刑考驗期內沒有故意犯罪的,自動轉為無期徒刑。很多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極力創造條件爭取死緩判決,如偽裝悔罪,積極賠償損失等。死刑緩期執行的二年過后改判無期,無期執行期間再爭取改判有期徒刑,最后再爭取保外就醫或者假釋,就又可以逍遙自在,這樣對犯罪的懲戒作用就會大打折扣,根本沒有起刑法的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作用。
該案中,被告人王志才故意殺人,手段殘忍,后果嚴重,符合被判處死刑的條件,重審之所以判處緩期二年執行,也是考慮了其平時表現良好,由于婚戀糾紛,導致其激情殺人,案發后坦白悔罪表現好,人身危險程度不高等因素,符合“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情形。
3.民事糾紛與死刑適用。《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規定“對于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故意殺人犯罪,適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應當與發生在社會上的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其他故意殺人犯罪案件有所區別”。這個規定出臺的初衷應該是為了保護弱者,另外也是考慮了被害人也會有過錯。通常情況下民間糾紛引發的犯罪會有以下一些情形:在糾紛中處于弱勢的一方在被欺壓、被逼迫的情形下,因為一時沖動而犯罪;被害人一方存在一定程度的過錯,這種過錯是激發被告人犯罪的直接或間接原因[2]。但是如果當事人雙方地位平等,甚至被害人相對弱勢,被告人相對強勢,那量刑時就應該對被告人嚴懲不貸。
在該案中,犯罪人王志才與被害人趙某某都是相對獨立的個體,其相互地位是平等的,其不存在相互的權利和義務,應該說趙某某拒絕與王志才結婚是趙某某的基本權利,現實生活中,這樣的情形再平常不過,從這方面看,趙某某并不存在過錯。至于趙某某拒絕的言語是否過于嚴厲刻薄,傷害到被告人的自尊和人格,案情中沒有提及,也無從考量其真實性。犯罪人作案手段殘忍,造成的后果極其嚴重,民事糾紛的從輕量刑原則對該案應該不能適用。
4.死緩限制減刑的適用。死緩限制減刑,是《刑法修正案(八)》增設的一項重要的刑罰制度,其適用對象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偏重,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又偏輕的情形,因為我國的死緩執行過程中無一例外地都進行了減刑,并沒有最終執行死刑的結果,甚至很多減為了25年以下的自由刑[3]。這就說明我國的刑法帶有明顯的“死刑過重,生刑過輕”的色彩,死緩實質上變成了一種確定性程度比較大的生刑。另外,該制度也是貫徹“以人為本”“少殺慎殺”刑法人道主義理念的要求,更能體現司法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
死緩限制減刑具體應該如何考量并準確認定呢?首先,我們應該承認,其應該以犯罪人用死緩為前提,即滿足死緩所要具備的“應當判處死刑”與“不是必須立即執行”兩個條件。其次,我們再去考慮是否應當對其限制減刑。本案鑒于被告人王志才有坦白悔罪,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平時表現良好等因素,應該說其人身危險程度不是很高,即應該符合“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情形,所以對其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之所以規定對其限制減刑,還是針對其犯罪行為的本質來說的,即其犯罪行為具備了手段殘忍,犯罪后果極其嚴重的行為因素,且被害人家屬不予諒解,從這個角度上說,被告人王志才還是不能免死。為有效化解雙方當事人矛盾對立,判處死緩限制減刑比死刑立即執行和緩期二年執行更加平衡合理。
三、本案結語
死緩限制減刑制度是一項相對比較新的刑罰制度,在適用上不明確的因素還很多。通過對該指導性案例的分析評價,我們認為,它與刑法規定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限制減刑制度等其他制度的聯系是非常緊密的,在個案審判過程中,要綜合、系統地去考量各種因素在量刑過程中的認定及適用問題,在罪刑法定原則的前提下,做到量刑上罪、責、刑的適應與平衡,以使司法判決的結果更能體現司法的功能及其價值追求。
參考文獻:
[1]成銀.李昌奎強奸殺人案評析[D].長沙:湖南大學,2012.
[2]葉良芳,應玉倩.死緩限制減刑的司法適用——最高人民法院第12號指導案例評析[J].浙江社會科學,2013(2).
[3]黎宏.死緩限制減刑及其適用[J].法學研究,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