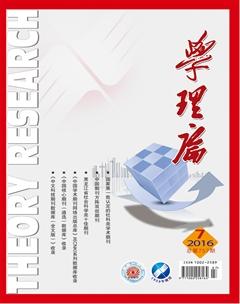華俄道勝銀行在華發(fā)行的紙幣:羌帖名稱考略
陳文龍
摘 要:19世紀(jì)末,俄羅斯帝國(guó)東進(jìn),圖謀遠(yuǎn)東的朝鮮和中國(guó)東北地區(qū)。1896年6月,中俄為了共同抵御日本的威脅,秘密簽訂了《御敵互相援助條約》即《中俄密約》。此條約使沙俄取得了溝通太平洋海濱的筑路權(quán)。中俄成立道勝銀行來(lái)解決修筑中東鐵路所需要的巨額資金。華俄道勝銀行名義上雖系中俄合營(yíng),然而事實(shí)上權(quán)利由俄人把持。道勝銀行發(fā)行的紙盧布為什么叫“羌帖”?歷來(lái)眾說(shuō)紛紜,最有可能的說(shuō)法為“契丹盧布”一說(shuō)。
關(guān)鍵詞:羌帖;道勝銀行;中東鐵路;紙盧布
中圖分類號(hào):K251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589(2016)07-0149-03
中日甲午戰(zhàn)爭(zhēng)后,清朝無(wú)奈地接受《馬關(guān)條約》,把中國(guó)遼東半島割讓日本,這對(duì)于全力東進(jìn)的俄羅斯無(wú)疑是個(gè)巨大的威脅。惱怒的俄國(guó)伙同在遠(yuǎn)東有共同利益的德、法兩國(guó),在國(guó)際上對(duì)日本進(jìn)行干涉。新興的工業(yè)國(guó)日本,在實(shí)力上遠(yuǎn)遠(yuǎn)不能同傳統(tǒng)歐洲強(qiáng)國(guó)相提并論。日本勒索了清朝巨額“贖金”后,放棄了遼東半島。
西方列強(qiáng)促使“還遼”事件的成功,更加堅(jiān)定了清廷朝野“以夷制夷”的牽制策略。沙俄則乘機(jī)向清朝頻頻示好,經(jīng)過(guò)一系列的外交努力,中俄兩國(guó)在遠(yuǎn)東問(wèn)題上達(dá)成聯(lián)合抵御日本的共識(shí)。1896年6月3日,《中俄密約》在彼得堡簽訂,俄國(guó)開(kāi)始修筑到達(dá)東方海岸線的鐵路。
一、華俄道勝銀行的性質(zhì)和業(yè)務(wù)
橫貫中國(guó)東北的中東鐵路,途徑呼倫貝爾草原、大興安嶺莽林、冰封沼澤葦塘。地理環(huán)境嚴(yán)苛,氣候極其惡劣,況且19世紀(jì)末的東北地區(qū)人煙稀少,鐵路每向前延伸一步,均付出高昂的代價(jià)。耗費(fèi)2.5億盧布的中東鐵路,對(duì)于歐洲國(guó)家中經(jīng)濟(jì)相對(duì)落后的俄羅斯,如此巨額的鐵路建設(shè)費(fèi)用,俄國(guó)在那里籌集的?什么國(guó)家或者公司會(huì)向沙俄供給充足的資金?
俄國(guó)為修筑中東鐵路籌集資金,在1895年由俄國(guó)圣彼得堡萬(wàn)國(guó)商務(wù)銀行聯(lián)合法國(guó)多家銀行合資成立道勝銀行,總行設(shè)在圣彼得堡。擁有注冊(cè)資本金600萬(wàn)金盧布的道勝銀行,表面形式上主要以法國(guó)資本為主,實(shí)際上主要股權(quán)由俄方控制,發(fā)言權(quán)在俄國(guó)手里。
《中俄密約》簽訂后,沙俄急忙派出財(cái)政部次官拉曼諾甫與清廷駐俄、德等國(guó)公使許景澄磋商修筑中東鐵路的具體事宜。1896年8月,清朝代表許景澄同華俄道勝銀行在柏林正式簽訂《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其中第一條規(guī)定:華俄道勝銀行建造,經(jīng)理此鐵路,另立一公司,名曰:中國(guó)東省鐵路公司[1]19。合同規(guī)定清朝已經(jīng)把鐵路籌款修筑等事宜交辦給華俄道勝銀行辦理。
1896年9月2日,俄國(guó)誘使清朝簽訂了《中俄銀行合同》。“第一條中國(guó)政府以庫(kù)平銀五百萬(wàn)兩,與華俄道勝銀行合伙做生意。”[1]1在道勝銀行中中國(guó)是出了本金的,銀行主要業(yè)務(wù)是為修筑中東鐵路籌款,銀行總部應(yīng)該在中國(guó)境內(nèi),俄國(guó)卻把華俄道勝銀行總部設(shè)置在圣彼得堡,但是不愿放棄中國(guó)利益的道勝銀行,把勢(shì)力逐步深入到中國(guó)的哈爾濱、上海、北京、滿洲里、漢口、齊齊哈爾等地,在俄國(guó)勢(shì)力范圍內(nèi)的東北及中東鐵路沿線滲透的密如蛛網(wǎng)。龐大的道勝銀行在實(shí)際運(yùn)作過(guò)程中,和中東鐵路一樣,完全把清朝擠出了銀行決策和管理層。華俄道勝銀行存續(xù)期內(nèi)在華大量發(fā)行貨幣,給中國(guó)人民帶來(lái)深重的災(zāi)難。俄國(guó)十月革命后,中國(guó)政府借助國(guó)際形勢(shì),清除了帝俄在華勢(shì)力,中國(guó)占據(jù)本金股份的道勝銀行被政府收回,帝俄殘余勢(shì)力在法國(guó)繼續(xù)登記道勝銀行營(yíng)業(yè)。直到1926年9月,道勝銀行在匯兌投機(jī)中慘敗破產(chǎn),中國(guó)設(shè)置的分行隨總部倒閉一起陸續(xù)關(guān)閉。
二、華俄道勝銀行發(fā)行的紙幣
散文《一九二九底愚昧》中,蕭紅也感受到十月革命后沙俄在中國(guó)發(fā)行的紙盧布大幅貶值。她描述到:“那還是在我小的時(shí)候,‘買羌貼‘買羌貼,‘羌貼是舊俄的紙幣(紙盧布)。鄰居們買它,親戚們也買它,而我的母親好像買得最多。……因?yàn)橘I‘羌貼這件事情父親始終是不成的”[2]。蕭紅喚作的“羌貼”,即是沙俄在華發(fā)行的紙盧布,它們主要流通于中東鐵路沿線,屬于硬通貨,大家都喜歡使用。1914年歐戰(zhàn)爆發(fā),沙俄參戰(zhàn)無(wú)暇顧及遠(yuǎn)東,在中東鐵路沿線流通的“羌帖”,兌現(xiàn)困難,貶值幅度大。沙俄為了籌集戰(zhàn)爭(zhēng)款項(xiàng),慫恿倒賣炒作羌帖。善良的東北人民以為羌帖在沙俄勝利后,能恢復(fù)原價(jià),遂大量買賣羌貼,撈一筆的心態(tài)在蔓延。然而好景不長(zhǎng),一戰(zhàn)尚未結(jié)束,十月革命帝俄滅亡。華俄道勝銀行無(wú)力兌現(xiàn)羌貼,像廢紙一樣的羌帖,東北民間用來(lái)糊墻,俗稱“墻貼”。
三、紙盧布名稱的幾種說(shuō)法
華俄道勝銀行發(fā)行的紙盧布為什么叫“羌帖”?說(shuō)法極多,歸納一下,下面三種說(shuō)法具有代表性。
1.“契丹盧布”說(shuō),北方歷史上的契丹民族給俄羅斯人感受最深。俄語(yǔ)稱中國(guó)為“契丹”,契丹音同羌。清朝來(lái)到中國(guó)的俄羅斯人把發(fā)行在中國(guó)的紙幣,叫“羌帖”。
2.清朝黑龍江流域的少數(shù)民族文化和經(jīng)濟(jì)落后,他們看到俄國(guó)人使用“洋炮”不知何物?習(xí)慣稱為“老槍”,因“槍”發(fā)音在漢語(yǔ)中同“羌”相同,慢慢把“老槍”訛傳為“老羌”。
3.中國(guó)自古以中原自居,其他居住周邊少數(shù)民族被稱為“南蠻、北蠻、東夷、西羌”。清末,沙俄從中國(guó)西邊蜂擁而至。西邊來(lái)的俄羅斯人被清人誤以為是古代的烏孫人后代,進(jìn)而演化為“老羌”。
四、清代對(duì)俄羅斯帝國(guó)的不同稱呼
羌帖,由俄國(guó)控制的華俄道勝銀行發(fā)行,它的名稱必然和清代對(duì)俄羅斯的稱呼有一定的聯(lián)系。清初,各種文獻(xiàn)及文學(xué)著作對(duì)侵入黑龍江流域的沙俄稱呼繁多,如老羌、老槍、羅察、羅剎等。清詩(shī)人吳兆騫《奉送巴大將軍東征羅察》題注中說(shuō):“邏察一名老羌,烏孫種也。”[3]93而方登峰《老槍來(lái)》詩(shī)序言:“俄羅斯國(guó),即古大食,善用火槍。”[4]古代文學(xué)著作及民間較多使用“老槍”和“老羌”。黑龍江都督宋小濂在《呼倫貝爾紀(jì)行》一詩(shī)“羌村道中”,更是直接說(shuō)土人呼物羅斯為老羌。
而當(dāng)時(shí)清代國(guó)家正式文獻(xiàn)“羅剎”一詞出現(xiàn)的頻率較高。1670年8月,清康熙帝致沙皇的一封國(guó)書:“有切爾尼果夫斯基所部少數(shù)羅剎盤踞雅克薩,侵?jǐn)_我邊民達(dá)斡爾和女真人。”[5]1381682年派往雅克薩的副都統(tǒng)郎談等人,回來(lái)報(bào)告調(diào)查沙俄軍隊(duì)情況,奏稱:“攻取羅剎甚易,發(fā)兵三千足矣。”[5]1501683年秋,康熙諭理藩院尚書阿穆珊瑯給沙皇發(fā)的國(guó)書上稱:“鄂(俄)羅斯國(guó)羅剎等,無(wú)端犯我索倫邊疆”[5]151。清朝同俄國(guó)往來(lái)的正式國(guó)書,以及大臣們的奏章均稱闖入黑龍江流域的俄羅斯人為“羅剎”。清初,剛剛睜眼看世界的中國(guó),極度缺乏包括俄語(yǔ)在內(nèi)的各種翻譯人才,同西方國(guó)家的交往大多依靠在華傳教士,很多文件是他們用拉丁文翻譯的。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談判期間,中國(guó)使團(tuán)代表索額圖的龐大隊(duì)伍中,“以譯員身份隨同使團(tuán)一起去的有在中國(guó)供職的兩名耶穌會(huì)士——西班牙人徐日升和法國(guó)人張誠(chéng)”[6]70。這些西方傳教士雖然長(zhǎng)期生活在中國(guó),可對(duì)深?yuàn)W的中文和滿文了解不深,在翻譯過(guò)程中或許造成俄羅斯國(guó)名被誤譯成“羅剎”,而發(fā)給俄羅斯的國(guó)書,其國(guó)名依然是俄文原拼寫,滿文和漢文確是“羅剎”。
羅剎,男奇丑,女姝美,食啖人,乃暴惡鬼名也。清初,尋求財(cái)富的沙俄冒險(xiǎn)分子們,歷經(jīng)千山萬(wàn)水越過(guò)西伯利亞冰原、浩瀚的貝加爾湖、莽莽外興安嶺,將俄羅斯帝國(guó)的邊境推進(jìn)到到黑龍江、松花江流域。他們所到之處“焚毀居處,殺害居民,捕捉俘虜”[7],“給和平的達(dá)斡爾族地區(qū)留下了駭人聽(tīng)聞的印象”[6]31。此時(shí)的清朝士大夫階層以及廣大的百姓們,對(duì)世界和俄羅斯不甚了解,他們對(duì)在中國(guó)東北邊疆侵?jǐn)_的哥薩克人,極其厭惡痛恨,稱他們是“惡鬼羅剎”。
雅克薩之戰(zhàn)前,康熙皇帝對(duì)和平解決邊疆問(wèn)題抱有一絲希望,國(guó)家正式給俄羅斯沙皇的國(guó)書,措辭非常恰當(dāng),對(duì)俄羅斯有蔑稱性的“羅剎”一詞,萬(wàn)萬(wàn)不會(huì)出現(xiàn)。從清朝皇帝的國(guó)書以及大臣們的奏折可以看出“羅剎”不是指俄羅斯國(guó),而是專指侵犯我國(guó)邊境地區(qū)殘忍的哥薩克人。黑龍江志稿也記錄了雍正年間,羅剎(即俄邊民)擾邊,羅剎即為俄羅斯邊疆居民。
五、“羌貼”名稱的最可信說(shuō)法
1.依據(jù)不足的“老羌說(shuō)”。沙俄入侵我國(guó)黑龍江流域的哥薩克人,相貌奇異,他們“深眼高鼻,綠眼紅發(fā),其猛如虎,善放鳥槍”,“其國(guó)在大洋東,相去萬(wàn)里。”[3]323烏孫、大食等中國(guó)古代西域國(guó)家,其國(guó)人相貌怪異。清初人地理認(rèn)知狹隘,當(dāng)沙俄從西方而來(lái),就以為是烏孫人來(lái)了,稱俄羅斯為“老羌”。到了近代,中東鐵路招募的護(hù)路軍,他們大多是哥薩克,來(lái)到東北以后,這支特殊的沙俄軍隊(duì)參與了20世紀(jì)初,發(fā)生在中國(guó)東北的歷次重大事件:義和團(tuán)運(yùn)動(dòng),日俄戰(zhàn)爭(zhēng),呼倫貝爾“獨(dú)立”,內(nèi)蒙古王公烏泰叛亂以及蒙古族陶克陶胡反清抗墾起義。他們所做的事情,和清初殘害我國(guó)邊境地區(qū)的“羅剎”無(wú)異,人們驚呼“老羌”又來(lái)了。
然而,沙俄在中國(guó)發(fā)行紙盧布時(shí),中國(guó)人已經(jīng)睜眼看世界了,知道俄羅斯不是古代生活在西域的羌族種群后裔,頻繁出現(xiàn)在文學(xué)作品中的“老羌”一詞,在清末中國(guó)日益接受西方文化以后,不會(huì)成為中東鐵路公司發(fā)行紙幣的名稱,羌帖來(lái)源于“老羌說(shuō)”論據(jù)不足。
2.牽強(qiáng)附會(huì)的“老槍說(shuō)”。清初黑龍江流域少數(shù)民族是以狩獵為主要生產(chǎn)方式,狩獵工具落后,以弓箭為主,缺乏槍支。此時(shí)進(jìn)犯我國(guó)黑龍江流域的哥薩克,使用的槍支是當(dāng)時(shí)最先進(jìn)的武器——火繩搶。北方漁獵民族對(duì)于能獲得火繩槍非常期盼,如此先進(jìn)的武器怎能當(dāng)成無(wú)用的“老槍”。20世紀(jì)初,世界槍械發(fā)展了,北方民族的老式火繩槍使用效果不佳,被人們稱為老槍。槍和羌發(fā)音近似,逐漸訛傳為“老羌”。
而早在18世紀(jì)初,清流人方式濟(jì)所著《龍沙紀(jì)略》中,介紹黑龍江邊塞人食用的菜種:“老槍菜,即俄羅斯菘也。……老不堪食,割球烹之,略似安肅冬菘。”“老槍雀,一名千里紅,與雀無(wú)異,惟顯有紅毛,產(chǎn)俄羅斯地。”[8]方式濟(jì)在介紹幾個(gè)菜種時(shí),都提到俄羅斯,這可以看出所謂的“老槍”不是俄羅斯帝國(guó)的名稱,“老槍”應(yīng)該是民間對(duì)沙俄的另一稱呼“老羌”的音轉(zhuǎn),和沙俄當(dāng)初使用的武器無(wú)關(guān)。
3.最有說(shuō)服力的為“契丹盧布”說(shuō)。俄語(yǔ)稱中國(guó)為Китай,直譯是“契丹”。在歷史上建立元朝的蒙古人曾經(jīng)稱中國(guó)北方為契丹,隨著蒙古人建立橫跨歐亞的帝國(guó),這一名稱在歐亞大陸地區(qū)和民族中廣泛傳播,“契丹”逐漸被歐亞民族泛指為中國(guó),俄羅斯被蒙古金帳汗國(guó)統(tǒng)治近二百五十年,蒙古人稱中國(guó)為“契丹”一詞也影響到俄羅斯人。
1885年,曹廷杰“變裝前往伯利一帶,密探俄界情形”[9]65,歷時(shí)129天,探得180條。其中提及俄羅斯境內(nèi)貿(mào)易賦稅問(wèn)題,他說(shuō):“東海濱省屬地,除乞塔、尼布楚勿論外,近年伯利歲人票稅俄帖十八萬(wàn)張,海參崴歲入票稅俄帖五十余萬(wàn)張……田賦、狗馬諸稅,不在此數(shù)。”[9]90-91他又簡(jiǎn)述了“俄帖”的發(fā)行和使用情況,“俄帖統(tǒng)由該國(guó)王發(fā)給,通行六大部,凡買金與官俸、官餉,皆給此帖,無(wú)民間私行印用者;“其六大部一切票稅,田賦諸正供,仍用帖解庫(kù),故俄境人民喜用俄帖。”[9]109曹廷杰稱俄境內(nèi)流通的錢幣為“俄帖”,而未提及“羌帖”等稱謂。
曹廷杰考察俄羅斯東西伯利亞地區(qū)之時(shí),俄國(guó)流通的貨幣“俄帖”還未進(jìn)入中國(guó)境內(nèi)。1927年,東省鐵路經(jīng)濟(jì)調(diào)查局編輯的《北滿與東省鐵路》一書寫道:“外國(guó)貨幣流通于北滿市上者,不一而足,而以日本與俄國(guó)鈔幣為最多。”“俄幣之流行,始自東省鐵路之敷設(shè),蓋當(dāng)時(shí)北滿固定錢幣,當(dāng)?shù)厣虡I(yè),率皆用之為媒介。”[10]314俄國(guó)鈔幣廣泛地流通于中東鐵路沿線各城鎮(zhèn),乃至呼倫貝爾及蒙古各地皆使用。中東鐵路流通的俄國(guó)貨幣有金盧布、銀盧布和紙盧布,以金盧布為本位金。東省鐵路經(jīng)濟(jì)調(diào)查局對(duì)流通的外國(guó)貨幣也未談及“羌帖”等說(shuō)法。
“羌帖”“羌洋”在中東鐵路時(shí)期華方的各種文獻(xiàn)資料頻繁出現(xiàn)。俄國(guó)十月革命后,中東鐵路罷工不斷。民國(guó)七年二月(公元1918年),哈爾濱地包工人王學(xué)賢、穆祥吉為中東鐵路公司苛待華工一事,向東省鐵路督辦事稟:“近因羌洋毛荒,百物騰貴,因而衣食不足,要求增加薪水。……獨(dú)俄工人改為月薪,頭等工人月薪羌洋二百四十元,……惟我華人無(wú)奈,幾向俄總管懇求。”[11]310民國(guó)八年五月三日滿洲里站中國(guó)商號(hào)全部罷市,五月十三日哈爾濱警察總局稟報(bào):“中、俄商會(huì)各出羌洋大帖二萬(wàn)元,計(jì)四萬(wàn)元;俄道勝銀行出羌洋老帖四萬(wàn)元駐滿江防司令部出羌洋老帖二萬(wàn)元,共計(jì)十萬(wàn)元。”[12]219
而在俄方管理的中東鐵路當(dāng)局正式文獻(xiàn)中,從未出現(xiàn)“羌帖”“羌洋”一詞,大多以盧布、俄洋出現(xiàn)。民國(guó)七年十月七日,中東鐵路公司車務(wù)處為華工薪金事復(fù)函:“當(dāng)俄工平均日得一盧布六十戈比之薪金時(shí),華工則得一盧布;在回旋區(qū)域及各處俄國(guó)守備夫、火爐夫及工人月薪有二十五盧布至三十盧布之?dāng)?shù),而華人月薪則為十五盧布。”[12]5民國(guó)八年六月(公元1919年),中東鐵路公司為改訂中東鐵路界內(nèi)各城鎮(zhèn)所有商鋪、工廠之營(yíng)業(yè)牌捐,發(fā)布第七十二號(hào)命令,“桶捐,三、中國(guó)燒酒:每桶俄洋二元”;“簽封捐,葡萄酒,每瓶俄洋一元。”[12]271-2721920年北洋政府交通部致道勝銀行函第八號(hào):“該路章程第十款內(nèi)載,公司股票本金之總額定為五百萬(wàn)盧布,共分一千股,每股五千盧布。”[13]
在中東鐵路附屬地沙俄實(shí)行的是具有殖民色彩的統(tǒng)治,中國(guó)方面與其往來(lái)的各類公文,不會(huì)用“老羌”等對(duì)俄羅斯有蔑視地稱謂,中國(guó)民間戲稱乃至官方非正式場(chǎng)合的稱呼則另當(dāng)別論。華俄道勝銀行在華發(fā)行的紙盧布,稱“羌洋”、亦稱“羌帖”,說(shuō)白了就是“中國(guó)大洋”“中國(guó)紙幣”的意思,俄羅斯方面也按中國(guó)方式進(jìn)行稱謂,如此雙方認(rèn)同的名稱,應(yīng)該來(lái)源于俄人習(xí)慣稱中國(guó)為“契丹”,一詞,因契丹音同羌。
參考文獻(xiàn):
[1]黑龍江省檔案館.中東鐵路(一)[M].哈爾濱:黑龍江檔案館,1987.
[2]蕭紅.一九二九底愚昧[J].七月,1937(5).
[3]吳兆騫.秋笳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4]沈德潛.清詩(shī)別裁集:下冊(c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416.
[5]中國(guó)科學(xué)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華史:第1卷[M].哈爾濱:人民出版社,1976.
[6][蘇]巴赫魯申.哥薩克在黑龍江:上[M].郝建恒,等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75.
[7][蘇]潘克拉托娃.蘇聯(lián)通史:第1卷[M].莫斯科:莫斯科出版社,1955:254.
[8]楊賓.龍江三紀(jì)[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153.
[9]叢佩遠(yuǎn),趙鳴岐.曹廷杰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5.
[10]張研,孫燕京.民國(guó)史料專刊(638)[M].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314.
[11]黑龍江省檔案館.中東鐵路(二)[M].哈爾濱:黑龍江檔案館,1987.
[12]黑龍江省檔案館.中東鐵路(三)[M].哈爾濱:黑龍江檔案館,1987.
[13]傅角今.中東鐵路問(wèn)題之研究[M].上海:世界書局,192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