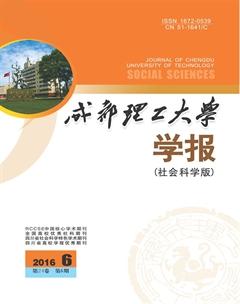龍榆生的詞史思想與價值お
韓辰
摘要:龍氏的詞史思想是近代史學與傳統詞學相結合的產物。在“一代有一代之音樂制度”、“一代有一代之社會風尚”兩大詞史思想的理論基礎之上,龍榆生更為客觀、理性地闡釋了“詞”的發展歷程,突破了傳統詞學中“空言標榜”的習氣和拘于“四聲清濁”的“圖譜之學”,為中國近代詞學的進一步發展指明了方向。
關鍵詞:龍榆生;詞史;詞學;近代;史學
中圖分類號: I206.5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6720539(2016)06009205
從19世紀中葉開始,西方文明開始大規模涌入中國這塊古老的大地之中,使中國被動地開始了近代化的過程。西方近代學術對中國傳統文化與學術的沖擊,既給中國傳統學術帶來了生存危機,同樣也給其帶來了近代化的契機。中國傳統學術順應時代的發展開始了自我革新的歷程。詞為“艷科”、“小道”,因此詞學在中國傳統學術中被視為支流,是當時正統意識形態控制較為薄弱之處,因此成為文化與學術近代化先驅們首先發難的場所。
縱觀龍榆生的詞學論著,自始至終將近代史學(包括音樂史、文化史)的方法與史家的精神融入詞學的研究與建構之中,變王國維“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之說為更為具體客觀的“一代有一代之音樂制度”[1]208、“一代有一代之社會環境”[1]63,將詞作為一種最富“音樂性之文藝”,進而將詞放到音樂生態之中加以考察,對歷代詞學批評和明清以來蔚為大觀的圖譜之學進行了根本性的突破和客觀的評價。同時,在此基礎上,結合歷代的社會環境與風尚,結合詞家個人的性格與經歷,對歷代詞家、詞派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客觀評價與梳理。
自20世紀30年代初期,陸續有劉毓盤的《詞史》,胡云翼的《中國詞史略》等著作問世。于此同時,龍榆生先生的詞史思想,通過《詞學季刊》和《同聲月刊》兩大平臺也得到了發展與宣揚,并與夏承燾、唐圭璋一起將中國近現代詞學的建構帶入了正軌。龍氏認為:“吾信中華民族不亡,則我國文字語言,亦必隨之永遠存在。中國語言不滅,則用以表現我國國民情感之歌詞,亦不必全棄前人之法度,而為外夷之‘馬首是瞻”。[1]143本文以龍榆生先生個人詞學的建立過程為典型,管窺中國詞學近代化過程中詞史思想的形成及其在近代詞學發展過程中的價值。
一、一代有一代之音樂制度
詞作為文體與音樂相互依存,后世音譜失傳成不可歌之“長短不葺之詩”。到明清之時,詞譜學逐漸興起。清代中葉“浙派”、“常州派”相繼而起,其后繼者各有主張,相互爭鳴。發展到清代之時,雖名家輩出,詞學大興,然而出現了僵化的傾向。在詞律上標榜“嚴守圖譜”,拘泥于四聲清濁。同時各詞家對某種詞風的片面推崇也給詞學的發展帶來了阻礙。突破這一局面,需要將“詞”的創作,放在歷史上真實的音樂生態之中來考察,使之回歸到音樂文學的本質之上。
晚清詞家雖有所反思,并企圖從音樂的角度來闡釋“詞”這一文體,但終究未能有根本性的突破!如況周頤《蕙風詞話》開篇提出:“《陽春白雪》,皆曲名。是先有曲而后有歌也,填詞家自度曲,率意為長短句而后協之以律,此前一法也。前人本有此調,后人按腔填詞,此后一法也。……唐宋已還,大雅鴻達,篤好專精之,謂之詞學。獨造之詣,非有所附麗,若為駢枝也。曲士以詩余名詞,豈通論哉。”又提出:“唐人朝成一詩,夕付管弦,往往聲希促節,則加入和聲,凡和聲皆以實字填之,遂成為詞。”[2]這樣的提法在當時不僅只蕙風一家,雖然注意到了詞與音樂相關這一事實,終究沒有系統地對詞與音樂的關系及歷史演進軌跡進行系統梳理,從而未能從根本上對傳統詞學的藩籬從根本上進行突破。
龍氏在其個人詞學思想的構建之初,便結合音樂史對詞體的演進歷程進行了梳理,其作用在于徹底突破傳統詞學所構建的基礎。其1933年4月發表在《詞學季刊》創刊號上的論文《詞體之演進》,便是其之后數十年詞學思想發展的奠基與發軔之處。
龍氏首先從源頭上厘清“詩”、“詞”、“曲”之間的分別,證明“詞”即“曲子詞”之簡稱,曲子詞正是“詞”所謂真正的源頭,因而詞是依附于隋唐燕樂而發展的,既不同于“詩”也不同于“曲”。“則‘詞為詩余之說不攻自破。”[1]6這是中國近現代詞學第一次系統地對傳統詞學從源頭上進行突破。
進而龍氏詳細論述了隋唐燕樂的形成與發展,認為:
吾人既明隋唐以來樂曲之流變,與其分合盛衰之故,將進而考求依此種曲拍成之詞體,及其進展之歷程,不得不于歌詞體制之新舊過渡期中,加以深切注意。若僅從文字形式上之長短參差,以上附南朝樂府,或以‘胡夷里巷之曲為詞體之起源,而不察其轉變之由,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皆非本文之所欲置辯者也。[1]46
通過對史料的仔細梳理,龍氏證明:曲子詞始為底層人所作“胡夷里巷之曲”,后或有文士深通音律者為之,經過文士不斷地修飾進而趨于雅化。從中唐到五代再到北宋初,小令頻繁地創調、變調與文人對于小令的廣泛創作,使詞與音樂的配合日趨精審。慢詞到柳永手中得到了大規模的創調,進而豐富了詞體,為蘇東坡等提升詞格做好了準備。到南宋,由于自度曲風尚的形成,其詞樂與歌詞的創作形式又發生了新的變化。因而詞體是伴隨著詞樂的不斷發展而變化創新的。
這些論斷不但突破了傳統詞學“就詞論詞”的方法,更是從根本上對傳統的“詞譜之學”所建構的基礎進行了否定。僅僅通過同調比較的方法,而專重“平仄”、“句讀”、“領字”、“韻腳”無法概括與解釋在音樂生態中不斷變化的“詞”的創作。1933年12月,龍氏發表《詞律質疑》一文,對明清以來將“四聲清濁”作為“詞律”的說法進行了否定。文中提出,“詞律”最初當指“宮商音律”、“樂句長短”而非“四聲清濁”。然而,晚晴詞家中諸如鄭文焯、況蕙風等正多拘于所謂以“四聲清濁”為標準的“詞律”、“詞譜”。文中引用況氏言論“除尋常三數熟調外,悉根據宋元舊譜,四聲相依,一字不易。”與“今日而言宮調,已與絕學無殊,無庸深求高論”[1]159,從而恰見其自相矛盾。傳統的“詞譜之學”以此不攻自破。
然而,龍榆生能從“詞樂”的角度對傳統詞學進行突破,但是其弊端在于,詞樂畢竟已經失傳數百年之久,如只從音樂的角度,依靠對“詞樂”只言片語的描述,從而勾勒出“詞”發展的歷史是抽象而不明確的。只有在一定程度上還原出了歷代詞樂的變化與聲詞配合的歷程,從而進一步對“詞”的歷史進行更為全面和成熟的勾勒!
龍氏進而汲取傳統“詞譜之學”合理的部分,通過分析不同時期詞作四聲配合方式與句法的變化,來推斷詞樂發展與聲詞配合的情況!在《論平仄四聲》一文中提出:
樂有抑揚高下之節,聲有平上去入之差,準此以談,則四聲與音律,雖為兩事,然于歌譜散亡之后,由四聲以推究各詞調聲韻組織上之所由殊,與夫聲詞配合之理亦可仿佛。[1]171
比如在小令的發展與變革的問題上,1937年龍氏在《制言》雜志發表《令詞之聲韻組織》一文,通過對從晚唐到北宋各階段的令詞聲韻組織與句法形式加以分析,從而推斷當時聲詞配合的發展情況,以此更為清晰地勾勒出令詞發展的歷史線索。其認為:令詞本脫胎于近體詩,從晚唐到五代,詞的平仄與句法配合漸與近體詩不同,反映出“依聲填詞”的發展和歌詞與詞樂配合日趨精審。北宋小令以近乎近體詩式者最為流行,而《花間集》中“不為后人所用,句法組織大異律詩(則)漸開慢詞之軌轍”,這是對令詞發展歷史的全新勾勒。在北宋慢詞的轉變的問題上,龍榆生撰有《慢詞之聲韻變化》一文,同樣從慢詞的聲韻組織與句法形式的變化,勾勒出慢詞發展中詞樂與聲詞配合的演變歷程。
總之,龍氏將詞放到其最初作為音樂文學的環境中加以考察,并對其發展軌跡進行了梳理,這是對“詞”進行歷史性研究的基本前提之一,也是被前代詞學所忽視的。通過結合音樂史對“詞”進行重新的定義,并將歌詞創作的動態變化結合詞樂發展的歷史進行考察,將明清以來僵化的“詞譜之學”進行了系統的否定,并建立起一套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對“詞”的“聲韻”、“句法”進行研究的新方法。
二、一代有一代之社會環境
龍榆生詞學的最顯著的特點便是將近代史學的精神與方法融入傳統的詞學研究之中,從而建構起近代詞學的新體系。將“詞”放到其最初作為音樂文學的環境之中加以考察是對“詞”進行歷史研究的大前提,同時需要對“詞”的創作主體的心態、性格以及所生活的社會環境進行相應的研究,進而更為全面梳理“詞”各個方面的歷史線索。
首先是對于歷代詞家與詞風的沿革。“文學即是人學”,因此作為創作主體的詞家,歷來被詞學之士所重視。傳統詞學往往習慣將詞家作為某種詞風的代表,并將詞家作為自己師法的對象。常州詞派的周止庵認為:學詞之途徑當是“問途碧山,歷稼軒、夢窗,以還清真之渾化”。又如將蘇辛二家作為豪放派的代表,將李清照作為婉約派的代表。諸如種種不勝枚舉。然而龍榆生正是要突破這一傳統,其在《蘇辛詞派之淵源流變》一文中說:“冀閱者瞭然于蘇辛詞派之特殊精神,以發揚其志趣;不僅空言標榜,為文學史上作一有系統之敘述而已。”[1]289以史家的眼光,客觀地將歷代詞家的創作實際和詞風的發展遞變作詳細的梳理和客觀的分析。
自1933年3月,龍榆生撰寫《論賀方回詞質胡適之先生》開始,三年間先后發表《蘇門四學士詞》、《東坡樂府綜論》、《清真詞敘論》、《南唐二主詞敘論》、《漱玉詞敘論》等論文。晚年又發表論文《試論朱敦儒的〈樵歌〉》、《試談辛棄疾詞》。上述文章無一例外都是從考證作者的生平事跡入手,進而闡釋其心態的形成和性格特點,以此從外部來分析詞家自身風格的形成。這種研究方法是近現代詞學研究的主流之一,其大成者當屬詞學近代化的又一主將夏承燾先生及其論著《唐宋詞人年譜》,從而徹底清算了常州詞派以來的“風雅比興”之說。然而,龍氏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近代詞學草創時期就已經開始將“史學”、“譜牒之學”運用于詞學的研究。
以《蘇門四學士詞》一文為例。文章開篇,龍氏提出蘇詞之三大特征,在內容方面包攬宇宙間萬事萬物,“詞體于是日尊,而離普遍性日遠”;在修辭方面則字面生硬而特崇風骨;同時在應用方面“則調外有題,詞中所表之情,未必與曲中所表之情相應。在此前提之下,龍氏認為:
且執蘇詞之三特征,以衡量其門下之所為,可以推見詞風轉變之由,與個人情性、時代環境,咸有莫大關系。[1]313
文中考證了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四人各個年齡段所處的不同環境與經歷,從而說明詞家各階段不同的心態和與之相應變化的詞風。
然而,史學對于龍榆生詞學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其對于詞家生平考證之深,更在于其以史家將歷史前后貫穿的宏觀視角來勾勒“詞”以及“詞學”的發展歷程。龍榆生在其詞學體系構建之初所撰寫的《詞體的演進》(1933年4月刊于《詞學季刊》創刊號)一文之中就將“詞”放入一個不斷發展的歷史之中,但這種歷史又并非簡單機械地演進,而是還原客觀的藝術生態。1933年6月在《文史叢刊》第一集發表《蘇辛詞派之淵源流變》,通過對宋詞自身發展的歷程和兩宋不同的社會環境的客觀分析,進而解釋蘇東坡對詞體進行突破的原因并分析了蘇辛以及同調詩人們詞風的異同,突破了前代詞人“空言標榜”的局限。1933年8月于《詞學季刊》第一卷第二號刊發論文《選詞標準論》將歷代“詞選”的情況進行了系統地梳理。1934年4月《兩宋詞風轉變論》一文中龍氏提出:
兩宋詞風之轉變,各有其時代關系,物窮則變,階段顯然。既非“婉約”、“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執南北以自限。[1]251
以歷史沿革的眼光來通盤考察宋詞的發展過程從而打破以宗派為限而缺乏客觀性的傳統詞學。直到1957年,龍氏晚年發表于《新建設》的《宋詞發展的幾個階段》一文才將兩宋整個詞學發展的歷程進行了更為宏觀而清晰的勾勒。
同時龍榆生以為詞學“三百年來,屢經劇變”[1]411,因而對晚明直至清末的詞學發展過程同樣以史家之眼光進行了審視,因而龍榆生的詞學不但是對傳統詞學的一種突破更是對傳統詞學的一種總結。其發表于《同聲月刊》第一卷第三號的《晚近詞風之轉變》(1942年2月)一文闡述了晚清內憂外患之下“士大夫感奮之余,寄情聲律。”從而在詞的創作上突破前賢的事實!龍氏以為:
“嘗怪常州詞派,獨標宗旨,議論精辟,為依聲家開無數法門,而張周二氏所為詞,似不足與其言相副,久乃益信吾所持‘至情之激發,有關世運,不可力強而致,為顛撲不破之說。所可學而能者,技術辭藻,其不可學而能成者,技術辭藻,其不可學而能者,所謂詞心也。詞心之養成,必其性情之特至,而又飽經世變,舉可驚可泣之事以醞釀之,所謂“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者,止庵能言之,而所作恒未能稱,則亦時為之也。”[1]515
其中“詞心”是詞中情感的來源,是詞氣格高下的核心。而外在的社會環境和創作主體的經歷是決定“詞心”的主要條件之一。因而,龍氏以為詞的創作受“世運”的影響是“不可顛撲”的道理。這也正反映出在龍榆生的詞學思想中,外在的社會環境對創作主體與詞的發展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同年又于《同聲月刊》第一卷第十號發表《論常州詞派》(1942年9月)一文,結合清代中葉以來的社會環境和士林風尚,客觀敘述了常州詞派的創立與發展的歷史。
總之,龍榆生結合社會環境的變化和創作主體與之相應的經歷和心態來解釋詞的發展,正是從史學的角度從外延來建構詞學史,這與從音樂史的角度對詞進行分析互為表里。
三、龍榆生詞史思想的貢獻與價值
龍榆生詞史思想對近代詞學的最大貢獻是將史學(音樂史、社會文化史)引入到詞的研究之中,其價值在于突破了傳統詞學重感發而缺少系統性與理性的弊端。這在龍榆生詞學的建構過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龍榆生早在其1934年出版的《中國韻文史》中反復強調“一代有一代之音樂制度”、“一代有一代之社會風尚。”這兩大觀點正是構建其史學化詞學系統內核與外延的兩個根本支柱。
在構建《詞學季刊》這一詞學研究平臺之初,龍榆生便發表文章《研究詞學之商榷》(1934年4月,《詞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一文,為詞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龍氏提出“詞學”的概念:
在歌詞盛行、管弦流播之際,恒為學者所忽略,不聞著有專書。迨世異時移,遺聲寂寞,鉤稽考索,乃為文學史家之所有事。歸納眾制,以尋求其一定之規律,與其盛衰轉變之情,非好學深思,殆不足以舉千年之墜緒,如網在綱,有條不紊,以昭示來學也。[1]113
認為首先在傳統諸家的“圖譜之學”以外,別為“聲調之學”通過歌詞來推斷“曲中所表之聲情”和“曲調之性質”。將詞作為帶有音樂性質的文學體裁,將其還原到歷史客觀的音樂生態當中來加以考察。同時突破傳統的“詞話”,另立“批評之學”,而其方法“必須抱定客觀態度,詳考作家之身世關系,與一時風尚之所趨,以推求其作風轉變之由。其利病得失之所在。”其盛贊夏承燾所撰《詞人年譜》,考證宏博,以為“詞史之學”方興未艾。此外,還認為;“‘目錄之學,所以示學者以從入之塗,于事為至要。”需要重考作家史跡,考證版本之流傳,詞家品藻應當結合作家之身世關系與一時風尚轉移。以上種種都說明龍榆生正是將“詞學”作為文學史來加以建構的。從龍榆生所作論著來看,音樂史與社會文化史一直貫穿于其詞學建構之中,并最終建立起了屬于近現代文學史的“詞學”。
試圖將傳統詞學與近現代史學方法相結合的嘗試,在20世紀之初已經出現端倪,而龍榆生“詞學”體系的建立與龍氏在《詞學季刊》與《同聲月刊》兩大平臺上的倡導在中國詞學近代化歷程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并最終與夏承燾、唐圭璋等學者共同建構起近現代詞學的主流。
1926年,上海大東書局出版的《清代詞學概論》(徐珂著)應為首部試圖借助近代史學系統梳理“詞”的發展歷史的著作。該著作將清代詞的創作與學術從“派別”、“選本”、“評語”、“詞譜”、“詞韻”、“詞話”等方面以時間為次序進行了述論。然而,此書僅僅停留在對詞家與作品進行羅列的層面上,且由于徐珂師從于常州詞派譚獻一脈,因而此書的論述與評判的角度以常州詞派為尊,為此書所做序文中稱徐珂為“譚門顏子”[3]甚為恰當!其評判常州詞派以外的清代詞學多失客觀。因而此書依然缺少理性的歷史眼光。
1927年,上海書局出版陳鐘凡著《中國韻文通論》,以“通史”的規模將中國古代韻文進行了梳理,將“詞”作為韻文發展的一個階段。然而,其局限在于只將“詞”限于唐五代兩宋,未能客觀地從詞發展的整體歷史出發,也未能將詞置于社會歷史文化的大背景下討論,依然存在較大的局限。
1931年,上海群眾圖書公司出版劉毓盤著《詞史》。已經深刻地意識到晚清以來詞壇的弊端正在于“莫測其真意之所在而又拘以格律,諧以陰陽”[4]。此論著將“詞”從唐到五代到兩宋到元明清的歷史進行了整體的勾勒,并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對各代詞家詞風的形成進行了相對客觀分析,然而卻較少將詞作為音樂文學放到音樂生態之中進行研究。
同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夏敬觀著《詞調溯源》,提出了詞與音樂密切的歷史,并考證詞所配之音樂起于隋代燕樂,將詞的發展與音樂生態的發展相結合,并明確地指明了詞體的由來。然而,對于詞樂與詞進一步發展的歷史并未加以梳理,且僅僅依靠關于詞樂的有限史料也很難具體地闡釋詞與詞樂的關系。
1932年,神州國光社出版王易著《詞曲史》。將詞放在音樂生態之中加以考察,并將有關音樂的史料與詞的文本相結合從而推斷詞與詞樂發展的歷史。例如在《唐代詞體之成立》一節中提出:“可知詞體成立之順序凡有三例,初整齊而后錯綜……流衍至于五代短章不足以盡興,于是伶工樂府,漸變新聲,增加節拍,而化短為長、引、近間作矣”[5]。然而,王易并沒能從社會文化的角度對詞曲的發展歷史進行研究。
1933年,上海大東書局出版胡云翼著《中國詞史略》與《中國詞史大綱》,其著作基本上沿襲了胡適《詞選》將宋詞分為“歌者之詞”、“詩人之詞”、“詞匠之詞”的觀點,未能結合詞本身音樂文學的性質與社會文化發展的背景對詞的歷史進行合理的闡述。
可見,在龍榆生進行詞學研究與創辦《詞學季刊》之前,已經存在將傳統詞學與近代史學相結合的傾向,然而或注重詞學的外延或注重詞的內部研究,未能全方位地來考察“詞”的發展史。將兩者同時并重的開端應在20世紀30年代龍榆生的詞學研究。
四、結論
綜上所述,龍榆生詞學將史學與傳統詞學相結合,使近代詞學的發展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提出“一代有一代之音樂制度(樂章)”、“一代有一代之社會風尚”的概念,將詞的發展放到音樂生態的背景中加以考察,突破了傳統詞學拘泥于以“四聲”、“清濁”等為標準的“圖譜之學。”同時,結合社會制度、士林風尚與詞家的個性與生活經歷,從外延對詞進行研究,從而突破了傳統詞學拘于門派而“空言標榜”數個詞家的局限,轉而客觀地闡釋“詞”的發展和詞家風格形成的原因。龍榆生將詞學史學化,并在《詞學季刊》和《同聲月刊》加以提倡,是中國詞學近代化歷程中的關鍵一步和重要特點,也是龍榆生詞學的價值所在。
參考文獻:
[1]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況周頤.蕙風詞話[M].王幼安,校訂.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3.
[3]徐珂.清代詞學概論[M].上海:上海大東書局,1926:1.
[4]劉毓盤.詞史[M].上海:.上海書店,1985:2.
[5]王易.詞曲史[M].上海:神州國光社,1932: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