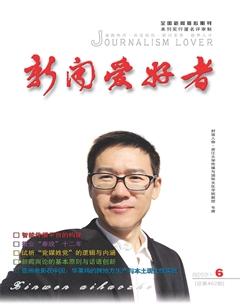從受眾的視角分析食品行業(yè)品牌危機傳播效果
李宜馨
【摘要】實驗法研究表明,在食品行業(yè)品牌危機傳播中,受眾面臨不同類型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品牌危機時,產品傷害事件類型、受眾的產品涉入程度和感知風險水平等三個變量對受眾品牌購買意愿產生影響。可辯解型和不可辯解型兩種產品傷害事件類型都會對受眾購買意愿帶來負面影響,受眾不會因為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未違背有關法律法規(guī)的監(jiān)管和限制而給予更多寬容,更不會寬容產品出現(xiàn)的違法傷害事件(如不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同時,受眾的涉入程度和感知風險水平在其做出品牌購買意愿時具有調節(jié)作用。
【關鍵詞】產品傷害事件;涉入程度;感知風險;品牌危機傳播
近年來,食品行業(yè)的產品傷害事件頻發(fā),引發(fā)了不計其數的品牌危機。例如,冠生園的陳餡月餅、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等導致的品牌危機等案例都廣為人知。因此,在當前“互聯(lián)網”經濟發(fā)展的時代背景下,開展食品行業(yè)品牌危機傳播效果的研究,對企業(yè)進行品牌危機傳播管理和積極貫徹落實國家的政策方針具有重要意義。
關注食品行業(yè)中眾多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的品牌危機傳播案例時,我們發(fā)現(xiàn)有些產品傷害事件是違反相關食品管理法規(guī)或安全標準約定的;有些是在媒體或法庭上能夠澄清和證明產品是無害的,只是觸及了人們的道德底線。前者稱之為不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比如“高露潔涉嫌致癌危機”等,后者稱作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比如“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等。[1]頻發(fā)的產品傷害危機給企業(yè)和社會帶來不良影響,程度嚴重的食品傷害事件甚至給社會穩(wěn)定帶來惡劣影響。但是,我們發(fā)現(xiàn)有些食品品牌爆發(fā)產品傷害危機后,受眾仍然繼續(xù)購買。究竟產品傷害事件在品牌危機中是如何影響受眾的品牌購買意愿的呢?為此,本文將從受眾心理、行為的角度,重點研究以下問題:
(1)在食品行業(yè)品牌危機傳播中,受眾面對可辯解型和不可辯解型兩種不同類型的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的品牌危機時,其品牌購買意愿是否存在差異。
(2)在食品行業(yè)品牌危機傳播中,受眾不同程度的涉入度和感知風險水平對品牌的購買意愿是否存在顯著不同。
一、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由于企業(yè)品牌運營管理過程中的失誤,存在缺陷或危險性的產品的屬性和訴求受到消費者的質疑和不信任,并且這一狀況在消費者群體中廣泛擴散傳播,對企業(yè)組織的品牌形象造成不良影響,即品牌危機。[2]本文的研究則具體到食品行業(yè)中,指的是因為食品傷害事件問題引發(fā)的品牌危機。
誘發(fā)產品傷害危機的因素存在于企業(yè)經營與管理過程中的各個方面和環(huán)節(jié)中,從產品到市場、從員工到消費者、從社會責任到公共關系、從內部環(huán)境到外部環(huán)境等。誘發(fā)產品傷害危機的因素主要包括:產品因素、市場因素、受眾因素、媒體因素、立法和監(jiān)督因素等。李安云認為競爭對手采用進攻性的營銷手段使企業(yè)市場占有率、銷售量等降低,從而產生企業(yè)危機。[3]Berman認為消費者的日趨成熟性及其強烈維權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的加強,以及消費者對產品的錯誤使用容易產生產品傷害危機。[4]
學者檢驗了作為消費者的受眾對危機企業(yè)的態(tài)度、對危機產品危險性的感知、購買意愿及消費者類型對危機責任歸因等方面的影響,發(fā)現(xiàn)產品傷害危機影響到消費者的信任,改變了消費者的購買行為。Siomkos和Malliaris研究了企業(yè)信譽、外部反應(政府、媒體的反應)和企業(yè)反應影響消費者對危機企業(yè)和危機產品的態(tài)度。[5]Siomkos和Kurzbard發(fā)現(xiàn),相對于聲譽低、不知名的企業(yè),對聲譽高、知名的企業(yè)而言,產品傷害危機對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不會產生負面影響。[6]王曉玉等引入了目標消費者考慮集的概念研究產品傷害危機事件及其處理響應過程對消費者考慮集的影響。[7]
但是,現(xiàn)有相關研究沒有從受眾涉入程度和感知風險的調節(jié)角度來研究在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的品牌危機中,產品傷害事件如何影響受眾的品牌購買意愿。Yeung &Morris的研究發(fā)現(xiàn),食品安全風險感知主要由社會和心理因素決定,技術角度的食品危害對風險感知影響較小,甚至沒有關系,而往往是受眾心理因素發(fā)生扭曲,放大了食品安全風險。[8]全世文等分析了受眾在食品安全事件后的購買恢復階段對奶制品的感知風險與風險態(tài)度及其影響因素,同時,對比分析了影響受眾對國產品牌和國外品牌奶制品的感知風險因素。[9]
綜上所述,現(xiàn)有研究并沒有探討不同類型的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的品牌危機傳播過程中受眾感知風險的差異及其對品牌購買意愿的調節(jié)作用。
根據上述理論回顧,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①:
假設1:較于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的品牌危機,不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的品牌危機導致受眾對該品牌產生較低的購買意愿。
假設2: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品牌危機時,受眾的涉入程度對該品牌購買意愿有顯著影響。
假設2a: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品牌危機
時,較于低涉入程度的受眾而言,高涉入程度的受眾產生的該品牌購買意愿較高。
假設2b:不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品牌危
機時,低涉入度的受眾和高涉入度的受眾對該品牌的購買意愿沒有顯著差別。
假設3: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品牌危機時,受眾的感知風險水平對該品牌的購買意愿有顯著影響。
假設3a: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品牌危機
時,受眾的購買意愿受其感知風險水平的影響,感知風險越高,其品牌購買意愿越低。
假設3b:不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品牌危
機時,受眾的品牌購買意愿受其感知風險水平的影響,感知風險越高,其購買意愿越低。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實驗法開展研究,實驗法是指在有控制的條件下可重復的觀察,其中一個或更多的自變量受到控制,以使建立起來的假設(即所確定的因果關系)有可能在不同情境中受到檢驗[10]。具體操作時以速溶咖啡的產品傷害事件為例,采用2(產品傷害事件類型:可辯解型&不可辯解型)×2(產品涉入度:低涉入度&高涉入度)×2(感知風險:感知風險低&感知風險高),均為組內實驗設計。②正式實驗之前,選擇40名被試者前測,結果表明兩種產品傷害事件類型的文字刺激材料存在統(tǒng)計學意義上的顯著差異。
正式實驗在大學校園實施,共有274名在校學生作為被試者。從性別來看,其中男性140名,女性134名;從年級來看,大一、大二占到60.8%,研一、研二占到29.8%,其余為大三、大四,占9.4%。為了避免被試者猜測研究意圖而影響研究結果,首先對被試的產品涉入度和感知風險水平進行測量。其次,讓被試者閱讀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的文字材料,并對購買意愿等進行打分;接下來讓被試者分別閱讀干擾材料,并對捐款意圖、飲食調整等進行打分,以最大可能消除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材料刺激對被試者接下來的判斷產生干擾;然后再讓被試者閱讀不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文字材料,并對購買意愿進行打分。
對研究中涉及的相關變量進行測量時,主要借鑒了前人使用的量表③,以保證量表的可信度。比如,對產品傷害事件類型的判斷,參考方正等人的研究,通過這一問題進行編碼:“在丙烯酰胺事件中,您在多大程度上確認A公司的咖啡確實存在危害?”(1=完全沒有危害,7=危害極大)對產品涉入度的測量,參考Zaichkowsky的量表,測量題項包括“飲用速溶咖啡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速溶咖啡跟我的生活息息相關”等[11];同樣,參考全世文等人的研究對感知風險進行測量,包括“在丙烯酰胺事件中,您在多大程度上確認A公司的咖啡確實存在危害?”等題項;關于購買意愿的測量,主要參照Siomkos的研究,采用了7點式的Likert量表④,分值越小代表受眾的購買意愿受損程度越高。
三、研究結果
在進行研究假設驗證之前,對變量進行信度檢驗,結果表明Cronbachs alpha系數⑤分別為0.858和0.766,量表的測量項目具有很好的內部一致性。同時,為方便統(tǒng)計處理,我們借鑒葛巖等的做法對數據進行了分類,即將受眾的產品涉入度(1~4=低涉入度,5~7=高涉入度)和風險感知水平進行分類(1~4=感知風險低,5~7=感知風險高)[12]。通過上述實驗研究,發(fā)現(xiàn)在食品行業(yè)的危機傳播過程中,產品傷害事件的類型、受眾的涉入度及感知風險確實影響受眾進行品牌購買選擇。
首先,按照產品傷害事件的類型分組后發(fā)現(xiàn),可辯解型情況下受眾的品牌購買意愿(M=3.122,SD=0.180⑥)高于不可辯解型事件情況下的購買意愿(M=2.662,SD=0.180)。方差分析顯示,兩組之間的購買意愿差異邊際顯著。假設1未得到充分支持,說明在不考慮受眾的涉入度和風險態(tài)度時,兩種不同類型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的食品品牌危機對受眾的購買意愿都有阻礙,但二者之間不存在統(tǒng)計學的顯著差別。
其次,在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的品牌危機傳播過程中,高涉入度受眾的平均購買意愿(M=4.20,SD=1.64)大于低涉入度的平均購買意愿(M=3.04,SD=1.60)。但是,t檢驗⑦結果顯示不同涉入度的受眾面對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時,其購買意愿在統(tǒng)計學上無顯著差別,假設2a未得到驗證。在不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的食品品牌危機傳播過程中,高涉入度受眾的平均購買意愿(M=3.00,SD=2.45)大于低涉入度的平均購買意愿(M=2.64,SD=1.39)。但是,檢驗結果顯示不同涉入度的受眾面對不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的品牌危機傳播過程時其品牌購買意愿無顯著差別,假設2b成立。因此,假設2未充分得到支持。
再者,在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的品牌危機傳播過程中,以受眾感知風險為自變量,受眾的品牌購買意愿為因變量,分別結合兩種不同類型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的品牌危機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在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的品牌危機傳播過程中,獨立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十分顯著,即不同風險感知水平的受眾之間的品牌購買意愿存在顯著差異,假設3初步得到支持。而且,感知風險高的受眾其品牌購買意愿(M=2.70,SD=1.43)小于感知風險低的受眾購買意愿(M=4.63,SD=1.41),支持了假設3a。在不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的品牌危機傳播過程中,獨立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也十分顯著,至此假設3得到驗證成立。此時,感知風險高的受眾其品牌購買意愿(M=2.37,SD=1.36)小于感知風險低的受眾購買意愿(M=3.69,SD=1.40),假設3b亦成立。
通過上文對研究假說的檢驗,我們得知在食品行業(yè)品牌危機傳播中,不考慮受眾的涉入程度和感知風險水平時,無論該產品傷害事件是可辯解型還是不可辯解型,受眾對該品牌的購買意愿均不存在十分顯著的差別。這不僅體現(xiàn)在以產品傷害事件類型作為單一獨立變量時,也體現(xiàn)在它與感知風險水平交互作用的主效應上。而且,當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食品品牌危機時,不論受眾的涉入程度高低,其品牌購買意愿的差異性不存在統(tǒng)計學的顯著差別,高涉入度受眾的平均購買意愿(M=4.20,SD=1.64)大于低涉入度的平均購買意愿(M=3.04,SD=1.60)。研究同時還證明當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食品品牌危機時,受眾的感知風險水平對該品牌購買意愿的影響具有顯著差別。當受眾的感知風險越高,其購買意愿越低,感知風險高的受眾和感知風險低的受眾之間的購買意愿存在顯著差異。
從中,我們還發(fā)現(xiàn)了另外一個問題:為什么受眾的涉入度在兩種不同類型的食品傷害事件中,對其品牌購買意愿的影響均無顯著差異呢?一般情況下,高涉入度的受眾對此類產品關系較為密切、經常購買此類產品,會對其產生品牌依賴,因此爆發(fā)產品傷害事件時,受眾重新進行品牌的篩選比較會面臨較高的品牌轉換成本,輕度危害的產品傷害事件(比如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易獲得諒解,會繼續(xù)購買。但是,本研究發(fā)現(xiàn)事實并非如此,在以速溶咖啡的產品傷害事件為例進行的研究中,被試者面對兩種不同類型的產品傷害事件并未表現(xiàn)出顯著的購買意愿差異,普遍傾向不會購買該品牌產品。
四、研究不足與展望
研究表明在食品行業(yè)品牌危機傳播中,無論是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還是不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都會對受眾購買意愿帶來負面影響,受眾不會因為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未違背有關法律法規(guī)的監(jiān)管和限制而給予更多寬容,更不會寬容產品出現(xiàn)的違法傷害事件(如不可辯解型產品傷害事件)。但是受眾的涉入度和感知風險水平在其做出品牌購買意愿時具有調節(jié)作用。
多元方差檢驗的結果顯示,在食品行業(yè)中因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的品牌危機傳播過程中,當產品傷害事件類型與受眾涉入度及感知風險水平互動時,偏Eta方⑧值未達到過0.10。這說明從本研究使用的三個變量出發(fā)來理解受眾面對產品傷害事件引發(fā)品牌危機時品牌購買意愿的差異,其解釋力有限,也說明可能有其他影響因素會對因變量產生影響,在將來的研究中可以考慮產品傷害事件的傳播媒介可信度、受眾信任傾向等因素,同時亦可以選擇更多的產品品類進行實驗研究。
注 釋:
①在實證研究中,未獲取實證研究材料之前,研究人員無法回答自己的研究問題,但是通過閱讀文獻資料、個人親身經歷,或者之前研究經驗,研究者會對所要回答的問題有一個初步的預測。這個預測以假設的形式被正式表述出來,即對兩個或多個變量之間的關系所做的預測性陳述。假設能夠清楚地暗示變量之間的關系,因此能夠指導研究過程。(詳見陳陽.大眾傳播學研究方法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②組內設計又稱作“被試內設計”(within-subjects design),其實驗進行的方式是:每個被試接受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實驗處理,而且每個被試接受的實驗處理是完全一致的。此處三個二相乘表示操作控制的變量是三個,每個變量有兩個水平。
③量表是有關研究變量的強度、方向、程度、層次或趨勢的復合測量手段,它包含著一組題項,對每種題項的回復對應著固定數值,其總值表示了研究對象的特征和性質。
④Likert量表是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李克特(Rensis Likert)于20世紀30年代發(fā)展而來,是實證研究中最常使用的定序量表,7點式表明量表中的每個題項都有7個不同程度的選擇。
⑤克朗巴哈系數(Cronbach's alpha)檢視信度的一種方法,由克朗巴哈在1951年提出。通常情況下Cranbach's alpha系數在0.6以上,被認為可信度較高。
⑥M表示平均數是一組數據集中趨勢的量數,是指在一組數據中所有數據之和再除以這組數據的個數,它是反映數據集中趨勢的一項指標。SD表示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在概率統(tǒng)計中最常使用作為統(tǒng)計分布程度(statistical dispersion)上的測量。標準差定義是總體各單位標準值與其平均數離差平方的算術平均數的平方根,它反映組內個體間的離散程度。下文中的M和SD均為此含義。
⑦t檢驗是概率統(tǒng)計學用t分布理論來推論差異發(fā)生的概率,從而比較兩個平均數的差異是否顯著。
⑧偏Eta方是一個統(tǒng)計量,能直觀地看出每個因素對總體變異的貢獻,如果A因素的Eta方值=X%,表示A因素解釋了總變異的X%。
參考文獻:
[1]方正,江明華,楊洋,李蔚.產品傷害危機應對策略對品牌資產的影響研究——企業(yè)聲譽與危機類型的調節(jié)作用[J].管理世界,2010
(12):105-118.
[2]曹榕,金玉秋.網絡環(huán)境下企業(yè)品牌危機的化解[J].新聞愛好者,2012(3):19-20.
[3]李安云.品牌危機的成因、防范及處理模式探討[J].商場現(xiàn)代化,2009(2):131-132.
[4]Berman B. Planning for the inevitable product recall[J].Business Horizons,1999, 42(2):69-78.
[5]Siomkos G.J. and Malliaris P.G. Consumer Response to Company Communications during a Product Harm Crisis[J]. Journal of Applied Business research,1992,8(4),:59-65.
[6]Siomkos G.J.,Kurzbard G.The Hidden Crisis in Product-harm Crisis Management[J],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4,(2):30-41.
[7]王曉玉,晃鋼令,吳紀元.產品傷害危機及其處理過程對消費者考慮集的影響[J].管理世界,2006(5).
[8]Yeung, R.MW & Morris. J. Consumer perception of food risk in chicken meat[J]. Nutrition & Food Science. 2001,31(6).
[9]全世文,曾寅初,劉媛媛.消費者對國內外品牌奶制品的感知風險與風險態(tài)度——基于三聚氰胺事件后的消費者調查[J].中國農村觀察,2011(2):2-15.
[10]陳陽.大眾傳播學研究方法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125.
[11]Zaichkowsky, Judith Lynne.The 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reduction,revision,and application to advertising[J]. Journal of advertising,1994,v23(4).
[12]葛巖.網民評論對消費態(tài)度和意愿的影響[J]現(xiàn)代傳播,2010(10):102-108.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編校:董方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