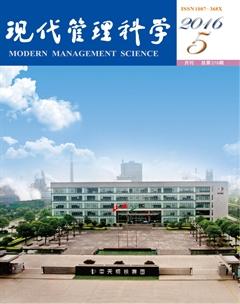國際經濟環境新趨勢與“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的何去何從
馮朝陽 韓曄
摘要:文章總結了時下國際經濟環境六個新趨勢,即全球經濟進入“再調整”深水區、發達經濟體復蘇“在路上”、國際區域合作“深化期”等,而此時“新常態”下中國經濟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如“調檔減速”、“優結構保增長”、“升級版”對外開放等,在此基礎上,給出了“新常態”下我國經濟應對國際經濟環境新趨勢的應對策略。
關鍵詞:新常態;國際經濟環境;經濟增長
一、 引言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歐元區國家、美國等西方國家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通縮,全球結構轉型與調整持續給經濟施壓,2015年12月16日,習近平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表示“中國開放的大門永遠不會關上”,發聲與全球各國一道面對經濟下行壓力。目前,金融危機已經逐漸消弭,國際經濟環境有復蘇跡象但依舊乏力,長期內各國的經濟增長仍然具有空間與潛力,然而由于全球正處于新一輪的“再調整”過程之中,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甚至新興經濟體內部“分化”現象顯著,我國經濟目前進入了“新常態”的試探期,經濟下行“探底”壓力巨大,整體的國際經濟環境一言以蔽之:“在溫和復蘇中砥礪前行”。
二、 時下國際經濟環境新趨勢新動向
1. 全球經濟處于“再調整”深水區,“小步慢跑”勢頭占優。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各國紛紛轉變經濟發展模式,逐漸地轉向了國內市場的實體經濟,調結構擴內需。為刺激國內經濟的發展以及就業美國推出了“再工業化”策略,以此刺激經濟,歐元區國家也都紛紛制定了優先發展本國制造業的政策,繼而國際經濟出現了一個顯著特征:制造業開始向發達國家回流。這不僅給原本處于出口比較優勢地位的新興經濟體帶來沖擊,而且還使得全球“再調整”格局進一步向深水區邁進,突出的特點就是由于受到發達國家“再調整”戰略的影響,處于“外圍”圈的低發展梯度的發展中國家在勞動力成本、資源等比較優勢的顯現,增速上卻占據絕對優勢,未來發展空間與潛力巨大。
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有所起色,新興經濟體雖然面臨較為嚴重的經濟下行壓力,但是仍舊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根據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2015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3.1%,高于2014年全球經濟2.6%的增長值,世界貿易組織預計2015年全球貿易總量增長約2.8%,這一數值恰好與2014年的增長持平,同時高于2012年~2014年平均水平約0.4個百分點。全球經濟目前而言,“小步慢跑”走勢顯著。
2. 發達經濟體復蘇已“在路上”,非均衡增長是其主要特征。金融危機過后,美國經濟出現了強勢復蘇的局面,美國放棄了量化寬松這一政策間接表明了美國經濟良好發展勢頭。根據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美國2015年第三季度的增長年率為2.1%,略高于初次預估的1.5%。“頁巖氣革命”使得美國本土油氣開采成本的下降,直接構筑了美國“再工業化”的成本優勢,使得很多諸如因特爾等高端制造業回流,給經濟增長注入了持久活力,傳統產業得益于美國的“再工業化”競爭力不斷提高,技術革新使得勞動生產率也不斷提高,國內消費需求的持續回暖,內需的動力拉動驅使了美國經濟的強勁增長。
歐元區國家目前已經走過了經濟周期中由衰退向復蘇挺近的拐點,復蘇“在路上”但較微弱,增長勢頭弱于美英兩國。歐元區2015年第三季度的經濟同比增長率為1.6%,而同期的美英兩國的增長分別為3.5%、3%。以德國為首的以制造業刺激經濟增長成效雖已顯現,但由于新興市場需求的低迷,德、法、意的出口疲軟成了歐元區經濟增長的最大拖累,這反應出了歐元區國家經濟增長放緩的一個趨勢。由于歐元區經濟經濟增長“低迷”,增加了歐洲央行增加其量化寬松政策的可能性。歐盟委員會還下調了2016年歐元區國家的經濟增長和通脹的預期值,表明歐洲未來幾年經濟增長依舊承壓。
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是促進日本經濟增長內生化的關鍵力量,雖受國際油價下降的影響,日本經濟有所受益,而由于消費不振,其在2015年第三季度的環比增長0.3%,雖擺脫了技術性衰退的陰影,但日本經濟距離強勁增長還有較遠距離,這一態勢增加了日本增加量化寬松政策的預期,因此日本經濟處于“低溫”徘徊期。
3. 新興經濟體處于“陣痛期”,下行壓力凸顯。全球貨幣政策的變動、大宗商品價格浮動、發達經濟體“再工業化”以及低梯度發展中國家比較優勢等不利因素拖累了新興經濟體國家的經濟增長。然而,由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強筋帶動作用、勞動力優勢、能源資源優勢等會逐步縮小新型經濟體國家與發達經濟體國家的差距(張亞雄等,2015)。新興經濟體處于“再調整”的周期中,經濟下行壓力巨大。新興經濟體所包含的國家之中,脫離高增長“俱樂部”的成員在逐漸增多,尤其是作為金磚國家的巴西,2015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長僅0.9%,環比增長僅0.6%。巴西國家地理與統計局預期的數據顯示2015年巴西經濟增長率是2.5%,增長速度慢于美英等發達經濟體。非洲最大經濟體南非也由于投資熱度銳減、國內政治信任危機等因素。受深陷烏克蘭地緣政治危機、國際資源價格下調等因素的影響,俄羅斯在2015年出現了連續三季度負增長的頹勢,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也預期俄羅斯經濟將在2016年持續萎縮。
4. 國際區域合作與競爭進入“深化期”,締造經濟新活力。全球一體化使得各個國家都深知合作共贏的重要性、更加體會到彼此合作的必要性。以美國為首的TPP以及TTIP這兩個協定最為典型,設定了更為高一級的貿易標準,也就是所謂的“對內自由、對外限制”的貿易合作框架;同時歐盟也通過與地中海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來拓展其區域合作邊界,在西半球成立的一個全部是發展中國家的“拉美及加勒比國家共同體”致力于推動區域及次區域經貿、政治、文化等合作;我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戰略更是將次區域合作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因此,在未來,國際區域合作與競爭將進入“深水區”,將為世界經濟締造新的活力。
5. 地緣政治復雜多變,非傳統安全進一步凸顯。首先,歐美俄深陷“伊斯蘭國”泥潭之中,國際反恐壓力未減反增;其次,隨著以中國為首的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崛起,美國調整了以往的戰略,將目光移向了亞太地區,必然對亞太周邊地區的政治、經濟等國際環境造成影響;第三,中東地區動蕩局勢又加重趨勢,俄羅斯、土耳其、美國、歐盟、以色列、伊朗等國家和區域組織都在該地區內存在一定影響,彼此角逐,為全球經濟的振興與復蘇平添了諸多不確定因素。
三、 “新常態”下我國經濟主要趨勢
2014年5月習近平總在河南省的考察講話道出“新常態”,其中心含義是指我國目前正處在重要的戰略機遇期,要有信心,要適應我國經濟的“新常態”。然而,目前國內學者對其的解釋卻呈現出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局面。有的認為我國經濟“新常態”指的就是我國經濟增長的“調檔換速”,有的確認為“新常態”指的是我國經濟由“非常態”向“常態”發展演進的一個理想階段。齊建國(2015)認為“新常態”時期我國將面臨更多的困難,而非進入了一個發展的“理想階段”。新常態下我國經濟主要有以下五個最為顯著的趨勢。
1. 我國經濟進入“調檔換速”的“相對穩定期”。“新常態”并不意味著經濟一直下行,而是在尊重經濟規律的基礎上,經濟增長在合理的范圍區間內有所浮動,主要應控制好浮動幅度(周明生等,2015)。從“十二五”經濟調整來看,我國主動的調整經濟結構與質量效果初顯,期間,我國經歷了2010年10.4%的高增長速度到2014年的7.4%的中高增速,據最新統計顯示,2015前三季度的增長率分別為7%、7%、6.9%,預計我國2015年增速7%。在“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具體數值可從以下方面考慮,即,我國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同時還伴隨著該年度生產總值較2010年有翻番的目標,從已有的的數據來看,2010年~201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約36%,剩下幾年平均增長率約在6.6%才能達到目標,而2015年增長率應該在7%左右,因此,整個“十三五”時期我國年均增長率在6.5%應該是底線,同時習近平也提出了我國經濟增長不能夠低于6.5%。在結構調整、質量和效率提高的大前提下,由高速向中高速的“調檔換速”符合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態勢,在相當長的一段是其中,我國將處在中高速增長的“相對穩定期”之中。
2. 經濟“優結構”進入“深度調整期”。從需求結構來看,經濟增長逐漸放緩的最為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國經濟的結構失衡(王小魯,2015)。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經濟發展過多地講求高速,而忽略了質量,甚至是以犧牲結構為代價的。長期以來,投資和出口是我國經濟增長主要驅動力,消費拉動明顯不足,尤其是在進入新世紀之處的幾年內,“雙順差”更加助推了這種畸形增長模式。受國際國內經濟環境的影響,依靠投資和出口的拉動型經濟“輝煌”已不再,我國經濟正在由要素推動型向消費需求驅動型轉變。2015年前三季度,固定資產投資較前半年增速回落1.1%,出口總額同比下降1.8%,出口需求與投資占比繼續回落,而2015年我國最終需求支出對我國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了58.4%,已經接近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60%的水平,同比增長了9.3%。從產業結構來看,我國一直以來都是工業化推動型經濟,粗放的工業發展模式也對我國資源承受力、環境承載力等產生了不利影響,其已不能適應“新常態”經濟的發展訴求,我國在未來將會由工業化拉動向服務業驅動方向轉變。目前產業結構調整已經“箭在弦上”,2015年前三季度三產比重達到51.4%,同比增長2.3%,高于二產10.8個百分點。
3. 經濟增長“新動力”邁進“孵化期”。在這個時期,“中國制造”逐步地向“中國創造”轉變,在我國優勢產業中,原始創新比重會逐漸提高;在國內國際需求旺盛的市場中,不斷形成集成集聚創新;在傳統與弱勢產業中,立足于引進、消化、吸收、在創新四部曲,而再創新的比重會有顯著提升。由此,創新驅動戰略將會在我國經濟中將是濃墨重彩的一筆,為我國經濟增長與發展注入“新動力”,也是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核心。在“新常態”背景下,我國將以學習占優逐步向以創新驅動的技術進步轉變。然而,我國從要素和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型經濟轉變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就目前來講我國將進入創新驅動型經濟的“孵化期”。
4. 對外開放階段進階“升級版”。中國傳統的模式已經不能夠適應新時代潮流,“代工時代”已經趨于尾聲,薄利多銷參與低端國際競爭的黃金時間已經逝去,由此,我國出口產品將更加邁向高端化,由于國際環境的變化,我國內部面臨資源環境約束、外部面臨勞動力成本、投資降低等不利因素,我國的國際收支會發生變化,甚至對某些國家會產生貿易逆差,可以緩解國內資源約束,促進國內經濟增長。同時,借助“一帶一路”戰略,將我國的中西部地區也放到了對外開放的前沿,我國能夠做到全面全方位的開放,打造新時期對外開放的“升級版”。
5. 區域協調發展駛入“夯實期”。在區域結構中,我國中西部地區經濟占比將進一步提高,同時借助于我國“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以及京津冀協同發展等重大區域戰略,我國區域結構將更加趨于協調,區域均衡發展水平進一步向“倒U”曲線峰頂處靠攏。與此同時,我國區域一體化進程顯著加快,全國城市圈和經濟發展“巨型區”形成,全國四大地域差距逐漸收斂,中西部地區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新引擎”,增長速度明顯快于東部地區,東北地區逐漸從從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走出來,經濟復蘇趨勢顯著。“新常態”下我國區域合作會更廣更深,區域交流會進一步加強,全國東中西協調發展買入“夯實期”。
四、 “新常態”下我國經濟應對國際經濟環境趨勢的對策建議
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依舊存在的情況下,我國應立足本國“新常態”的特點,加強“向外投資”力度,實時調整我國對外開放基本策略,積極推動國際經濟秩序的調整,利用本國比較優勢推動貿易多元化發展。
1. 優結構保增長是“新常態”下我國經濟應對國際經濟環境的基石。我國在經歷了“十二五”時期的調結構穩增長以來,經濟結構趨良性發展,然而“新常態”下我國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此時我國經濟應盡快實現“優結構”,面對2020年的小康和翻番目標,我國的經濟增長不能單單地求穩,更應該做的是“保增長”,在“十三五”期間應該保證6.5%的增長底線。在國際環境不確定因素依舊存在情況下,唯獨我國經濟做到“優結構保增長”才是應對復雜國際經濟環境的根本所在。
2. 立足本國需求結構,鼓勵對外投資,打造“走出去”升級版。我國經濟正在走向“新常態”,我國需求結構中投資對經濟拉動作用在減弱,而此時,國際經濟環境正處于復蘇的“小步慢跑”時期,外部環境相對較好,同時國外市場需要外部投資的注入來激活本國低迷的市場,如歐盟、日本等國。同時,就目前而言,跨國公司已經成為了國際經濟交流的主要的組織者,通過推動企業大膽“走出去”,不僅僅能夠分解國內產能,而且還能夠為萎靡的國際經濟帶來新的活力。但是傳統“走出去”的往往都是附加值低的資源、原材料等企業,我國應立足“新常態”,大力鼓勵高端產業“向外走”,同時可以利用國外投資收益對國內“代工”收益經濟替代,還能夠起到優化國內經濟結構的功效。
3. 推動我國貿易自由化、多元化發展。比較優勢理論與要素稟賦理論都強調了各個國家在貿易中能夠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對外存在比較優勢,只有充分利用本國比較優勢,摒棄貿易保護主義,國際貿易才會更加順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都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金融危機以后,國際市場的萎縮對我國出口影響較大,因此多元化的貿易關系將是我國經濟“新常態”下應對國際經濟環境的重要砝碼。可以通過金磚國家、上合組織、“一帶一路”戰略等平臺積極發展多邊貿易關系,降低對美、歐、日的依賴度,積極加強同新型經濟體的貿易往來,要通過“走出去”戰略不斷開發拉美與非洲的潛力,這樣還可以使我國盡快擺脫產業鏈低端的困境。
4. 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降低我國經濟金融風險。我國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而人民幣在全球貿易結算的份額目前僅在3%左右,在大國對弈的國際環境中,人民幣是唯一的非國際貨幣。我國對外開放“升級版”箭在弦上,人民幣國際化是我國金融開放的核心,資本流動、進出口貿易以及外匯儲備等很容易受到美、歐等貨幣政策波動的影響,因此人民幣國際化是降低國際貨幣危機的一個主要手段,也是保證“新常態”經濟在“調檔換速”中穩健發展的重要支撐。我國應該利用“一帶一路”積極推動雙邊貨幣計價結算,降低對美元、歐元的依賴。我國還應該利用亞投行、金磚國家銀行及絲路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與項目,在互利共贏的前提下,穩步促進人民幣周邊化向區域化轉變,逐步使人民幣走向世界,這也有助于提升我國金融話語權。
5. 積極參與國際區域合作組織,推動國際經濟秩序調整。2015年12月19日,我國在IMF投票權上升到第3位、印度提升至第8位、巴西提升至第10位,新興市場話語權大幅度提升,新型經濟體的快速崛起對現有的全球經濟格局帶來了劇烈的沖擊。在當前大部分國際平臺都由發達國家把持的不利形勢下,我國應該通過區域性平臺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在順應全球治理的潮流下,我國應該積極利用上合組織、金磚國家峰會等區域治理平臺以及“一帶一路”等次區域合作機制,重視APEC、G20等國際組織,在IMF、WTO等框架內加強同歐美發達國家交流尤其是與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合作、鞏固與拉美和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伙伴關系,從一個被動接受者向一個重要參與者與維護者轉變,亦可形成倒逼國際經濟秩序調整的機制。
參考文獻:
[1] 張亞雄,張曉蘭.從“十三五”時期國際經濟環境看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機遇與挑戰[J].經濟縱橫,2015,(11):11-17.
[2] 齊建國.中國經濟“新常態”的語境解析[J].西部論壇,2015,(1):51-59.
[3] 周明生,郎麗華.新常態下經濟轉型與“十三五”時期經濟展望—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國際高峰論壇(2015)綜述[J].經濟研究,2015,(8):184-192.
[4] 王小魯.經濟增長放緩的根本原因是結構失衡[J].河南社會科學,2015,(5):6-7.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項目號:15BJL109)。
作者簡介:馮朝陽(1987-),男,漢族,河北省寧晉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區域經濟;韓曄(1981-),男,漢族,山東省聊城市人,聊城大學商學院講師,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收稿日期:2016-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