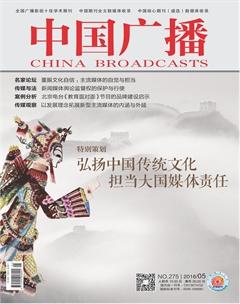新型廣播需要新型產品
蔡萬麟
【摘要】“新型廣播”是廣播轉型的方向和目標,新型廣播應當有新型產品相因應。新型產品要能代表新的生產能力、新的核心競爭力。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特別策劃《致我們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記》代表了“新型產品”的一種方向,具有一定的樣本意義。本文結合這組特別策劃的實踐,從內容創新、形式探索、優勢強化、深度追求四個維度,探尋了廣播新聞新型產品在題材范疇、體裁樣式、聲音優勢、深度表現諸方面開拓創新、提升價值的啟示和路徑。
【關鍵詞】新型產品 內容創新 形式探索 優勢強化 深度追求
【中圖分類號】G222 【文獻標識碼】A
2015年8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以下簡稱中央電臺)提出:“充分利用好積淀的經驗和資源,實現突圍與轉型,占領新市場,發掘新市場,努力建設新型廣播,是我們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以“新型廣播”作為廣播轉型的方向和目標,言簡意遠。何謂“新型廣播”?這需要一篇大文章。僅就內容生產而言,新型廣播應當有新型產品相因應,是顯然的。有了新型產品,才可以支撐新型廣播。
新型產品要能代表新的生產能力、新的核心競爭力。它應具有如下特征:符合國家戰略發展趨勢,代表主流價值觀,體現廣播未來競爭力,具有成長性,符合市場新需求,承載傳播新價值。以這樣的標準看,《致我們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記》(以下簡稱《印記》)允稱“新型產品”。
《印記》是一個好創意,大容量的架構、大力度的推送,頗有些橫空出世的意味,形成業界一道景觀。中央電臺經濟之聲承擔了其中的“職業季”和“習俗季”。執行的過程即是學習的過程。《印記》長長的標題,實際就是定位、標準和要求,精微把握,洵非易事。投身愈久,愈感覺到其立意之高遠、取旨之弘深。例如:傳承意義上的積淀感(“印記”),中國傳統的價值觀(“文化”),逝者如斯的歲月感喟與悲憫情懷(“正在消逝”),文化歸屬的主體意識(“我們”),對傳統遺存的鄭重與肅穆(“致”)。策劃者在“印記”之上,不惜累加修飾,又冠以致敬、寄語的意味,這樣的議題設置分明也是嚴苛的叮嚀,樹立起一個標準,決定了文字的風格、聲音的調性。作為執行團隊之一,我們自當細心把握,時時前瞻而后顧。可以想見,這一番創作雖然收獲頗豐,但其過程卻是罕有的艱辛。即如筆者這樣的老廣播,三十多年來如此精細地帶領團隊打磨一件作品,也是屈指可數的頻次。
當前,新媒體驚濤拍岸,傳統媒體自不能總在此岸。廣播轉型已是迫在眉睫,這需要革故鼎新的一個過程、一番功夫。經歷了兵刃相接的新聞競爭之后,廣播似乎開始慢下來、靜下來,抖一抖征塵、望一望四周、想一想來路,于是,驀然發現曾經遺忘的風景,隱約聽到歷史深處的回聲。我們把這一切告訴自己,也深情款款,致我們永不消逝的忠實聽眾。《印記》正是轉型期的創新之作,可謂應運而生。
《印記》雖不代表新型產品的全部,卻透射出新型產品的諸多要素和因子,它的啟示是全方位的,也具有一定的樣本意義。
一、內容創新:大舉突進文化領域,發掘內容新市場
受到電視的挑戰與擠壓,廣播這些年的改革可謂望盡天涯、壯懷激烈。但有一個比較優勢始終占據,即快速、便捷、伴隨。這使得廣播在相當長時間里保持了聲音傳播中的王者地位。然而,新媒體像一個莽撞的年輕人,沒有規矩地來了。當第一波強沖擊過后,人們漸漸注意到新媒體催生的新生態、新規則、新邏輯,于是發現,傳統媒體受到的最大沖擊其實是內容。做好內容依然是王道,內容創新成為緊要。新的傳播生態使傳統媒體在內容上的比較優勢被弱化甚至消解。理論上說,新聞人人可以生產、人人可以推送,一些內容似乎已經無需生產。面對新的需求,要探尋內容表現的新意,也需要開疆拓土,發掘新的市場,創造新的價值,重新打造比較優勢。
《印記》即是一次內容創新,是對題材范圍的著力開拓。“方言季”“地名季”“工匠季”“職業季”“習俗季”“戲曲季”“聲音季”“自然季”……選取傳統的留痕,觀照心靈的返影,輕吐歲月的喟嘆,其深邃的歷史感和豐厚的文化感都是令人回味的。廣播新聞似乎從未這樣大規模地突進文化領域,呈現出如此廣大的文化視角。這反映出,文化已經成為新聞內容的自然深化與延伸,也說明,文化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和必然要求,它將進入新聞報道領域,成為一個宏大的主題。因此,《印記》是文化的,更是新聞的。雖然有歷史的檢視、文化的反思,但仍是現實的視角、當代的意義。立足現在,回顧過去,瞻望未來,以現世的思考,醒察歷史的余波與回瀾,報以悠遠的會心,生發切要的體認,其價值取向直指當下。也正因為如此,《印記》的主題普遍具有“內涵深刻,表達困難”的問題,如果只是對種種印記作感性層面的展示與介紹,自然容易,但《印記》具有新聞性的要求,又不能直白地表露,“印記”之上還附加著諸多意味深長的約限,所以困難。我們做“職業季”“習俗季”,這方面體會尤深。總體看,《印記》諸篇均需要以歷史和人文的視角進行準確的、全局性的把握,體現出代表國家電臺立場的認知與判斷。無論是惋惜惆悵于過往,還是寄語企望于未來,都要透射出強烈的正面導向。可以說,新聞性的文化紀錄要比藝術性的文化紀錄困難得多。所以,《印記》的意義不是讓新聞進入文化,而是讓文化進入新聞。
如此說來,《印記》或將成為一個開端,廣播的內容生產或將開辟新的領域、產生新的動能。筆者因此也認為,《印記》的難度雖高,但不能據此就認為只能偶爾為之,反而恰恰說明廣播新聞內容生產的標準需要大大提高了。自然不能要求日常都如《印記》,但更高的標準、更高的要求將成趨勢。唯其如此,廣播才能有新的傳播價值。
二、形式探索:豐富體裁樣式,提高廣播表現力
以《印記》的立意、主題,很自然地選擇了紀實、紀錄的樣式,這是允當的。優中選優,我以為《誰還在唱二人臺》《婚禮禮之本》諸篇,故事獨立、完整,已相當符合“紀錄片”的標準,有望作為“聲音紀錄片”的佳例。這樣大規模地采用藝術類的樣式、手法制作廣播新聞節目,好像也是第一次。
或許會覺得有些突然,但《印記》的成功說明,在形式意義上,廣播積極探索表現手法的多樣,或者說把廣播非新聞類別的采制理念和手法引入新聞生產,不僅可以重塑比較優勢,也被證明可行,且具有相當的合理性。
廣播新聞的體裁分類源自報章,慢慢又結合了廣播的特點,近些年漸趨簡化。廣播新聞的體裁雖有更迭,但始終限于新聞領域。為適應國際評獎,偶爾也會有一些藝術化的制作,但通常被認為不適合日常播出。一些精心制作的節目往往純粹為了走向世界,并沒有國內播出的機會。因為沒有適配的節目去容納這樣的“陽春白雪”。事實上,形式的固化同內容一樣,也已經被習慣。
《印記》嘗試了突破,其體裁樣式雖然還不統一,但顯然已經沖破了傳統新聞樣式的界限,呈現出聲音紀錄樣式、聲音紀實風格的特征。擷領大要,巧布針線,造微入勝。聲音創造了畫面,聲音構筑了場景,突破了純線性架構,注重時空的跳躍轉換、場景的分解組接。新聞的、文藝的、技術的,多種手法的運用,大大增強了廣播節目的表現力和感染力,使《印記》獲得了全新的收聽體驗。
事實上,新聞引入紀錄手法,也有其內在的邏輯聯結。新聞產品和紀錄影片雖分屬不同領域,但有一致性。二者都以真實性為原則,盡管紀錄片表現真實的手法一直存有爭議,但真實、準確、客觀的原則與新聞相通。二者又都強調傾向性,都有影響社會輿論的宣教功能。新聞是報道真實,紀錄片是表現真實,作為藝術的紀錄片在真實性的表現上無疑更細膩、更精致。廣播新聞生產融入紀錄片樣式,不失為一種增強表現力的好辦法,可以促使其在形式技巧上更加講究,生產出更加精致的產品,提高在傳播市場上的競爭力。紀錄片在傾向性表露上一般都曲折迂回,隱匿于故事、細節之中,這也值得廣播借鑒,寓教于情,寓理于形,潛移默化。這些,在《印記》中都已有所光大,所以才感染人、感動人、感化人。精心的策劃、精準的立意、精細的采訪、精致的寫作、精微的制作,這樣的經驗對于日常都有直接的意義。
三、優勢強化:探尋聲音表達規律,傳播廣播好聲音
《印記》是典型的廣播產品,是聲音的一次熱烈展示和華美回歸。聲音可以如此之美、如此富于感染力,這樣的感受,于傳受雙方都是不約而同的。尤其是一些年輕的創作者們,乍然面對這樣豐沛的聲音世界,忍不住驚喜:原來廣播還可以這樣!
也許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印記》將推動廣播迎來一個重新發現聲音、研究聲音、創造聲音的時代。倘如此,廣播的表達可不可以再跨一步,把聲音再強化,用聲音構思,用聲音統領,讓自身獨有的特色極致化?發展往往就是發展本身在推動,根本動力自然是技術進步,而其表征是各種要素的改變。新媒體帶來的改變正在倒逼進一步的改變,廣播的發展也將源于改變所帶來的新動力。廣播的表達始于讀 《人民日報》社論,長期以來因循的是文字邏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廣播正是在傳媒市場發生改變的情勢下改變業態、大力推動音響表現的,廣播從此走向真正張揚自身特點的獨立自覺之路。但時至今日,面對傳媒市場新的、更大的改變,我們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把聲音放到一個更高的戰略層面去認識,讓聲音真正形成廣播的“專業特質”,形成不可替代的優勢。今天看來,二十多年前聲音的解放仍然是在文字的框架中“增加”音響,聲音的進一步解放則是要以聲音為邏輯起點,探尋的已不是聲音與文字的關系,而是聲音與聲音的關系。這個聲音將包括采訪對象的聲音、記者的聲音、旁白的聲音、場景的聲音、行為的聲音、自然界的聲音以及音樂、效果,還有對上述聲音創造性、藝術化的合成、組接及強弱處理,從而產生更具感染力的效果。聲音的世界變幻莫測,聲音的創造奧妙無窮,《印記》只是開啟了一扇窗,而聲音的創新余地是窗外的千秋雪、萬重天。
應當說,受制于諸多因素,《印記》尚未完全做到“用聲音構思”,或者說尚有不足。但顯然,在一個主題嚴肅、思考理性的背景中,聲音已被充分地調動,進入到了一個新的境界。由聲音構成的一個個場景和畫面,成為邏輯線索,形成相因果、相映照、相銜接的種種關系,決定了表達的順序和節奏。當然,文字仍然起著很大的作用,有時是為了彌補采訪音響的不足,有時是點題、過渡、升華的需要。“方言季”“工匠季”“戲曲季”“職業季”“習俗季”等都盡可能不把理性部分的表達交付專家,而是讓其隱約閃爍于字里行間,目的仍然是突出聲音的紀實感,避免讓直白的說理公然沖淡特定場景中的敘說。
如果我們回顧的時間上溯于近百年,便會發現早在無聲電影時代,就曾有過一個對聲音表達專注而癡迷的時期。聲音在無聲電影中承擔了舉足輕重的藝術功能,推動敘事,感染觀眾,成為直接的審美對象。而早期的有聲電影,由于驚喜于對白而冷落“聲音”的藝術創造,以至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即使有聲電影已形成相當規模的產業,有識之士仍然一致認為低俗的有聲片毀滅了高雅的無聲片。這在今天看來不免執拗,但給我們的思考是,視聽之娛相伴相生,人們曾經對聲音如此執著過,當訴諸視覺感官的愉悅到了一定程度,聲音是否又會回歸到它應有的位置呢?
四、深度追求:讓廣播產品擲地有聲、行穩致遠
新型廣播產品還應當解決一個深度的問題。《印記》立意高邁、境界雄闊、內涵深刻,要表現出這樣的深度,委實不易。首要的是思考要深,然后才是如何調動各種手段,尋求表達之妥善。“職業”“習俗”兩季力求準確把握總題,塑造典型人物、典型語言,并置于典型場景、典型環境之中。同時開掘歷史的縱深,升華其畫外之境、象外之意,表達出深切而悠長的主題。這一主觀意圖,兩季中有些篇目似乎做到了,有些尚有不少遺憾。縱觀《印記》各季諸篇,對廣播的深度表現,或多或少均做了積極的探索,在深度的表現方法和實現路徑上,也都有啟示。
廣播是表達通俗化的媒體,回顧廣播的傳播歷程,深度雖也偶有彰顯,但始終形不成總體氣質。廣播業態很難形成追求深度的內在機理。除了介質的局限以外,廣播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由于占據著傳播迅捷、接收可伴隨等比較優勢,對深度的追求似乎顯得動力不足。廣播的接收情境大不同于紙媒,若只從報章文體層面和紙媒比拼深度,終顯出天然的短處。即使某個時期涌現出足堪與紙媒比肩甚至有所超越的作者與作品,也難以形成整體業態的深度取向。
《印記》的啟示在于,在深度思考的前提下,廣播的深度追求與路徑依賴不能只是因循紙媒的思維邏輯,而必須仍從廣播自身出發去探尋規律。天地廣闊,手法多樣,倘運用得當,廣播會呈現出具有自身特質的深度。既可以情感,又能以理究。這種深度更符合廣播的接收情境,更具有感人的力量。
新媒體環境下,所有的媒體、所有的生產、所有的內容,事實上都被置于一個平臺,流通分享,相對優勢削弱,絕對優勢也被改寫。猶如大壩傾頹,水面等高,若想再露崢嶸,只有提高標準,做優做精。追求品質、追求深度因此變得迫切起來,深度將成為品質的重要因素,追求深度的內生動力勢必增強。品質的提升不再只是一個獲好評、獲獎項的問題,而是事關傳播力、競爭力甚至生死存廢的大問題。
《印記》有著相當的深度要求、文化要求、審美要求,它是在尚不很具備某些機制條件的情況下大范圍強力推動的。這種推動不能僅僅視為組織的力量,也須看到適時順勢的內在驅動。對于深度(思想力)、文化(大視野)、美感(感染力)的追求已如此迫切,本身也說明問題。還有一個背景應該是,互聯網加諸廣播的沖擊似不同于當年的電視,經過初始的震蕩之后,人們日益感受到,可能恰恰是互聯網帶給廣播更多的可能性。工具意義上的互聯網使廣播的便捷性有了新的定義,即更加便捷。盡管這種便捷性并非廣播獨有,但廣播與網絡具有更多的兼容性,在便捷均沾的情況下,廣播仍顯示出一定的比較優勢。而理念意義上的互聯網,更是給廣播帶來更為廣闊的想象和創新空間。內容拓展、形式創新,也為調動更豐富多樣的表現手法提供了可能,為深度的多渠道、廣播化呈現開拓了路徑。由于廣播在聲音特質上仍具有相對優勢,深度的呈現將伴生美感體驗、情緒帶動、思考延伸,無疑,這將是廣播傳播的新境界。
以這樣的方式實現深度雖然投入較大,但也恰恰是互聯網催生的新理念、新規則、新邏輯,使我們可以對生產效能做出新的考量。比如分眾的趨勢、獨家的消解、共享的特征,都使廣播迅速確立新的傳播理念與章法。廣播重新需要精品化,重新允許重復播出、多路推送、平行分享。越是精品,重復率、分享度可以越高。在大量碎片化的情況下,精品化價值凸顯。《印記》雖然投入很大,但大范圍、大規模的平行共享、反復重播,實際對沖了高投入。倘若再進一步延長生產鏈,增加附加值,進一步考量由于重播而節省下來的生產同質內容的無效勞動的成本,又或再進一步想到這樣的精品生產所帶來的生產者綜合能力的提升,那么就總體而言,收益將遠遠大于投入。
無可否認,移動互聯網時代,資訊已如空氣,必需而又平常,獲取新聞已相對成為低價值需求。傳者之于受者,已不再僅僅是一種功能需要,傳受雙方將建立起更高境界、更高層次的互動關系。這種互動不只是體現在淺層次的表達,而是深入到心靈、影響到情緒,表現為參與、體驗、共鳴與享受。這就要求新聞生產必須創造更高的價值,從功能價值向情緒價值、藝術價值提升。就廣播而言,就是不滿足于實用性的收聽,更要追求情感性的共鳴和藝術性的享受。《印記》的創新意義和樣本價值,我以為當作如是觀。
(本文編輯:呂曉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