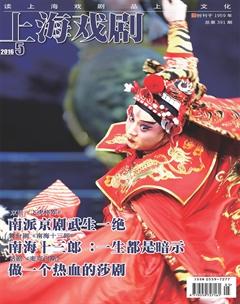大圣年說大圣戲系列之瀟灑大氣的北派悟空戲
嚴慶谷
介紹了兩個南方的悟空戲流派后,筆者再來談談北方的流派。北派悟空戲的演法與南派相比有很大不同,講究規范嚴謹,注重人物氣度,雖然少了一些花哨的噱頭,但是人物的神韻就凸顯出來了。表演上以武生的形體動作為基礎,略微收小一些幅度,通過曲膝、端肩、縮脖等手段來表現悟空的各種形態。
北派悟空戲當屬素有“武生泰斗”之稱的楊小樓最具代表性,因其父楊月樓有“楊猴子”之稱,所以他也就有了“小楊猴子”的諢名。父子倆都曾是升平署的內廷供奉,深得老佛爺慈禧的賞識。
楊小樓擅演《水簾洞》,年輕時跑碼頭,三天打炮戲,必貼此劇。聽老先生講,他人未上場,一聲悶簾兒的“開山吶!”,就能贏得滿堂的彩聲。頭場在高臺的羅圈椅上有許多驚險的身段動作,彰顯出威風凜凜的猴王風范。
其《安天會》授自張淇林,這是一出昆腔戲,相當難演。按照武生的路數,那時還有拿棍“起霸”的演法,不過現在的舞臺上已經看不到了。楊小樓對待這出戲的態度非常嚴謹,先學了三個月,又練了三個月,還是覺得不夠瓷實,最后請張淇林幫他排了三個月,才敢上臺見觀眾。原來這出戲在業內有“唱死天王累死猴”的說法,即托塔李天王在派將時,要滿宮滿調地唱昆腔套曲,孫悟空則與天兵天將車輪大戰,幾乎沒有喘息的機會。據李洪春先生回憶,以前演《安天會》出場的天神人數要比現在多得多,既要詼諧地表演,又要火熾地武打,沒有一定的功力,根本演不下來。難怪楊小樓不敢有絲毫懈怠。
楊小樓天生嗓音華美,一聲叫板“呀!”,仿佛天籟之音,余音繞梁,不絕于耳,在《安天會》中唱【醉花陰】【喜遷鶯】等曲牌時,滿宮滿調,響遏行云,蕩氣回腸。雖然他的身材偉岸,但是扮演悟空時,身段輕盈靈巧,氣度不凡。在武打時,他腳下的步法極快,如風馳電掣一般,與之配合的演員稍有差池,便會露出破綻。他還根據自己的臉型,創造出了“一口鐘”的臉譜。
楊小樓還首倡了“猴學人”的藝術觀點,追求形神兼備的境界。
繼楊小樓之后,李萬春和李少春二人的悟空戲也是各具特色。他們是革新派,在繼承楊派的基礎上,都發揮出了自己的藝術特長。
李萬春的臉譜叫“倒栽桃”,形同倒置的桃子,紅色的臉膛與白邊銜接處,由內向外漸淡,過渡得非常柔和。他注重表演,善于刻畫悟空的神態,很少翻騰。他對盔帽也做了一定的改良。通常《安天會》悟空戴草王盔登場,但他認為悟空在“花果山”的身份是大王,戴草王盔合適,可現在被玉帝封為齊天大圣,要去天上桃園上任,身份變了,理應調整,就專門設計了改良猴紗帽。
李萬春演“偷桃”時,吃真桃子(沒有桃子的季節,以其他水果代替),先啃皮,并保持皮不斷,然后從嘴里拿出一條完整的皮,這種演法很獨特,頗受觀眾喜愛。
以前,北派只演《安天會》和《水簾洞》,而李萬春則向南方學習,增添了《石猴出世》《五百年后孫悟空》以及《骷髏山猴王擊尸魔》等劇目。
李少春的悟空戲集南北各家所長,他將“倒栽桃”的臉譜調整為“倒栽葫蘆”,在兩腮勾勒精美的細紋,增強了悟空的靈動感。面部肌肉一動,整張臉立刻會變得鮮活起來,確立了自己“美猴王”的風格。
在武打方面,李少春不斷改良,有了許多新的突破,讓觀眾始終保持一種新鮮感。他主演的《智激美猴王》《十八羅漢斗悟空》深受觀眾歡迎。
上世紀50年代,為了配合出國演出的需要,由著名劇作家翁偶虹執筆,將《安天會》改編成《大鬧天宮》,打破了“唱死天王累死猴”的傳統格局,強化了天宮的陰謀,反襯出悟空的機智勇敢,使全劇的藝術性和思想性有了全面提升。后來,該劇成為李少春的代表作。
我們知道李萬春和李少春是郎舅關系,雖然是至親,但在舞臺上卻各不相讓,形成“二李爭春”的局面。當李萬春看到李少春排了《十八羅漢斗悟空》,不甘示弱立刻推出《十八羅漢收大鵬》作為回應。后來在上海貼演此劇時,讓張翼鵬產生了誤會,以為李萬春要收自己這只“大鵬”。于是,即興編排了一出《孫悟空棒打萬年春》,表示公開對抗。在刊登的廣告中,特意把“年”字縮小,乍一看好像“棒打萬春”。這一事件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成為一段梨園趣談。
最后,還要提一下北昆的一位老伶工郝振基,他的悟空戲追求本真的表演。據說,他身材瘦小,平日就飼養一只猴子,觀察它的行動坐臥。因此,他的表演如同真猴一般活靈活現,尤其是演《安天會》中“偷桃”時的神態幾近亂真,令人拍案叫絕。他也是勾“一口鐘”的臉譜,扮相非常古樸,只可惜這一流派的演法已經失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