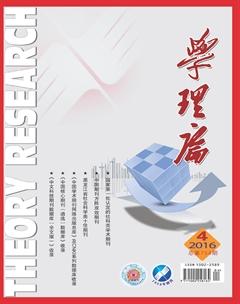淺析新制度主義及其對國際政治學的啟示
陳邦瑜 彭金星
摘 要:新制度主義在舊制度主義基礎上,更加注重對個體偏好和行為的分析,同時又對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主義進行了批判性的反思,逐步形成了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和社會學制度主義三個流派。新制度主義有助于國際政治學中的新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的產生和理論闡釋,對分析國際政治中的制度規范有一定幫助。
關鍵詞:新制度主義;理性選擇;歷史;社會學;國際政治學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6)04-0053-02
二戰后,新制度主義逐漸成為政治學比較推崇的研究方法,它認為即使制度對政治行為和政治抉擇有一定的約束作用,但并不是起決定性作用。新制度主義認為需要深層次地考察和分析制度對個體行為的影響,并將個體行為放在歷史條件中進行考慮,通過運用歸納法形成較成熟的理論,然后再對國際政治展開研究。新制度主義拓寬了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和領域,特別是對國際政治學學科研究領域具有重大啟示。
一、新制度主義范式的興起與演進
19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科學從對制度的普通研究轉向對制度主義的研究。彼得斯認為,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屬于舊制度主義研究,經過行為主義流行的30年后,新制度主義在政治學中開始興起。新制度主義學者反對把行為界定為政治分析的基礎,用行為去解釋政治現象是不具備說服力的,所有的行為都是發生在某種特定的制度環境之內的,這種行為才能充分地被理解。因此,有學者大聲疾呼“重新發現制度”“回歸國家”與“回歸制度”,但“回歸國家”似乎并無特別新穎之處,人們不應該簡單地接受制度的一般定義,而應該使其發展成為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途徑。
二戰結束后,西方社會科學逐漸以美國為重心,歐洲失去了傳統的學術中心地位,在歐洲盛行的歷史分析范式、制度—法律分析范式及哲學思辨傳統也逐漸被重視實證、數量分析方法的科學主義所取代,定性研究和價值判斷在研究中被最小化。經濟學隨著日益強大的經濟領域力量凸顯了其顯學地位,并逐步得到確立,它對其他學科的影響推動了崇尚個人主義和以市場原則的自由文化擴張,并使這種文化發展為新理論范式的基本框架。理性選擇范式就是在這種學術背景下產生的,并發展成為社會科學的主流范式。20世紀中期,行為主義興起并迅速主導了整個社會科學領域,其研究方法形式客觀、中立,論據實證并能近乎精確地解釋政治活動,這是傳統的研究方法無可比擬的,行為主義因其獨特的優勢取得了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話語權。行為主義是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重大革新,但其用科學標準來衡量社會政治現象似乎脫離了實際,暴露出了對社會價值觀的忽視,研究的形式主義和數理語言難以表述的困難,導致其會容易遺忘對歷史與現實問題的研究。20世紀70年代,各種研究范式開始盡顯其能,取長補短,交叉與融合,逐漸打破了行為主義在各學科尤其是社會科學領域的絕對優勢地位。新制度主義是在新制度經濟學在經濟領域巨大成功的影響下,為了矯正行為主義方法中過于關注政治個體及其行為,忽視宏觀和中觀層面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環境因素對結果的影響而產生的。實際上,新制度主義并沒有完全放棄舊制度學派的一些合理“內核”,和舊制度主義學派用靜態眼光看制度不同,新制度主義用動態的眼光綜合分析經濟運行理論、政治行為和制度的作用。因此,新制度主義的興起不是制度分析范式的簡單回歸,而是其向現代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發展。
二、新制度主義的解析
新制度主義最早從經濟學中興起,由于有學者不滿意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主義對于“政治”“國家”“制度”的輕視,將政治的分析片面地建基于個人主義之上,才被引入政治學研究。新制度主義是對行為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反思,其主要內容有:
首先,在解釋社會現象時,在制度因素中結構與人哪個更重要?行為主義強調“人”的重要性,而新制度主義認為對人的獨立影響作用的研究應該放在對社會結構分析的基礎上,這樣才能獲取有力的解釋論證。新制度主義著重分析制度對人的行為、對政策結果的影響,并認為制度約束人類的行為可以促進行為的規律和規范,增強解釋和預測的可靠性。新制度主義認為人類接受制度的約束,同時制度又是人類行為的結果,所以新制度主義必須解釋作為個體的人接受制度約束的原因,不同的解釋促成了新制度主義不同流派的產生。新制度主義各流派認為政治的核心要素包含制度,制度是政治管理和解釋政治現象的有效工具;個體及其行為雖然很重要,但必須把個體放進一定的制度背景中進行分析。
相比舊制度主義,新制度主義在強調制度重要性的同時,更注重分析個體偏好行為,這增強了新制度主義的解釋力。新制度主義豐富了“制度”內涵,制度還包括非正式的結構、慣例和觀念。舊制度主義在方法論上普遍以整體主義為主,而規范制度主義類似整體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是典型的個體主義,歷史制度主義則居中。與舊制度主義相比,盡管新制度主義在發展研究的可傳遞性、可重復性、量化等方面還不完善,但新制度主義更加重視理論的發展和方法論。
按影響力不同,可將新制度主義分為以下三大類范式。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發端于以羅納德·科斯和奧利佛·威廉姆森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科斯認為在制度選擇中交易成本權衡很重要,引起了經濟學中的新制度主義革命,威廉姆森則提出了將交易成本推理操作化,他認為制度環境是政治制度存在的表現形式。政治學中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源自于對政治制度本身進行交易成本分析。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認為每個政治個體都有固定的偏好,實現偏好最大化是政治行動者的最大目標。理性制度主義視行為為導致政治結果的關鍵因素,建立了理論來解釋制度的產生:相關行動者能從中獲得比其他制度更多的利益。理性選擇范式認為理性個人的選擇和行為動機是自我利益最大化,也是社會運行的基本動力。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最大特征體現在理性策略算計的行動者行為上,強調政治人的理性和穩定的偏好,認為政治的過程是集體行動陷入困境的過程,行動者通過制度安排達到共同獲利的目的。
歷史制度主義是在比較政治學中發展起來的,它保留了舊制度主義對正式制度的重視,接受了關于集團理論的觀點。豪爾和泰勒認為歷史制度主義有四個特征:歷史制度主義廣泛地界定了制度與個體行為之間的關系;強調了與制度的運作和演進相聯系的非對稱的權力分配;在分析制度演進時強調“路徑依賴”和“意外結果”;注重將制度分析和能夠產生某種政治結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來。歷史制度主義將現場制度融入歷史環境,強調既有制度中的權力對比關系對新制度的產生所帶來的不公平的壓力,它認為政治結構和制度安排可能導致政治社會生活中的不平等。歷史制度主義重視將制度分析和觀念等因素結合起來分析問題,在分析微觀現象時缺乏有效性,它不能解釋制度與行為間是否存在因果聯系,不及它在分析宏觀現象時的效用性。
社會學制度主義是從社會學中發展起來的。不少社會學家認為西方的世界文化強調韋伯的理性觀念,即將理性看作實現正義和進步的手段。這種世界文化規則構成了包括國家、組織和個人的行為體,并為其確定了合法的追求目標。世界文化規范也使全球范圍內的組織和行為變得越來越相似。由于他們將這些文化規范和規則稱為“制度”,他們的研究路徑被命名為“社會學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的制度概念打破了把基于組織結構的“制度分析”與基于共同價值的“文化分析”分裂的做法,促使兩者交融,強化了宏觀解釋力。社會學制度主義者有效地解釋了無效率制度長期存在的現象,這是前兩者所不及之處。制度不是簡單地規定人們做什么,而是指出在特定背景下人們覺得該做什么。制度不是直接影響個人的策略性計算和行為選擇,而是為行為提供了必備的認知版本、類別判斷和行為選擇模式,影響人們偏好、認同和自我形象的形成,從而間接指導人們的行為。
三、新制度主義對國際政治學的啟示
正是在新制度經濟學的學理支援下,基歐漢在《霸權之后》中發展出了國際機制的功能理論,這部著作“提供一種以制度經濟學為基礎的新的理論視角”。基歐漢的功能理論有力地論證了“制度是重要的”,但仍有其缺憾性。有學者批評說,國際機制的功能理論并沒有解釋為什么一些機制發展為正式的組織,而另一些機制卻沒有。基歐漢的不足被后來的學者們彌補,他們認為,國家在國際關系中所面臨的集體行動問題不止“囚徒困境”,必須創設不同類型的國際機制以滿足不同的集體行動所提出的功能性要求。由于采用了與微觀經濟學相同的行為假定,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能夠從微觀經濟學中輸入理論和方法,如博弈論、公共選擇理論、集體行動理論、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委托—代理理論等。盡管理性假定受到了認知心理學、期望理論和社會建構主義等多個流派的質疑和批判,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裹挾“經濟學帝國主義”之威,迄今仍是國際制度理論與經驗研究的主流,有助于開拓國際政治學理論研究的新視角,有助于國際政治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發展。
社會學制度主義和國際政治學中的建構主義有某些共同點。社會學家認為社會結構并不是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社會所構成的,而是由正在擴張和深化的世界文化所構成的。現代國際體系被以韋伯的理性觀念為核心的文化規則所主導。這些西方的、理性化的規則通過兩種方式將國家塑造為國際體系下的單位,一種是為國家確定“理性的”目標,如追求“現代性”和“進步”,另一種則是確定“理性的”制度以實現這些目標,如市場和官僚制。社會學制度主義是在美國社會科學傳統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理論假設明確,方法是實證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者通過強調社會規范在國際生活中的力量,為國際制度的獨立價值提供了更具剛性的論證,國際制度會增強,不僅是因為它便于達到帕累托最優,有助于國家以最小成本實現目標,而且認為參與日益增多的國際組織網絡在文化上是必要的和適當的。
國際制度研究在早期階段打上了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義烙印,在研究方法上屬于舊制度主義范疇。行為主義革命的發生和“國際機制”概念的提出為新制度主義取代舊制度主義創造了必要條件,同時又在國際政治學領域形成了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和歷史制度主義。新制度主義就解釋國家、國際組織及國際體系運行的基本邏輯而言,理性選擇屬于“預期結果邏輯”,社會學屬于“適當性邏輯”,但就歷史觀而言,理性選擇和社會學都認為歷史總是有效率的,歷史制度主義則將無效率的歷史帶入研究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