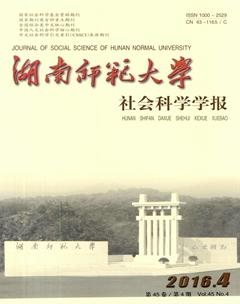李云麟與左宗棠關系考
趙維璽
摘要:李云麟為晚清時期一位名士,才識兼具,為左宗棠等諸名流所賞識。左宗棠督師西北后,將其調赴軍營協助西征事宜,李云麟在收復新疆和辦理中俄交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李、左個性都較為剛烈,彼此難以含容,加之在收復新疆的戰略方針和新疆建省問題上政見分歧甚大,故二人關系迅速惡化。對李、左二人關系由正常到交惡的過程進行了詳細考述,并從性格因素和政見相左兩個方面分析了其交惡原因,進而揭示滿、漢官員在新疆問題上的權力博弈。
關鍵詞:李云麟;左宗棠;塔城;新疆建省;《西陲事略》
一、李云麟與左宗棠的交集
李云麟,字雨蒼。道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34)生于直隸永平府盧龍縣。先世為山西洪洞人,明初遷至河北永平。清初以糧差得隸內務府漢軍,遂著旗籍。李云麟天性聰穎,以讀書勤奮聞名鄉里。除精通經史子集外,舉凡兵書、戰冊、天文地理乃至《奇門遁甲》等也無所不覽。18歲補博士第,后因“三赴秋闈不第,遂棄而從戎。”
考究李云麟與左宗棠的最早交集,應始于左宗棠主講淥江書院之時。李云麟叔祖父之子李恩緯擔任醴陵知縣,與左宗棠相交甚契。通過李恩緯的關系,李云麟得以結識左宗棠并為其所用。關于左宗棠對李云麟才識的確認,《灤縣文史資料》中摘錄了一段其后人李樹軍的說法:
李云麟從軍以后,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士兵。有一次出征,云麟自言自語的說:“今天打仗,一定不能取勝。”這話被一個伙夫聽到了,告誡他說:“軍隊中不能說泄氣的話,否則要殺頭的。”但結果確實打了敗仗。伙夫把云麟的話告訴了上司,上司又轉告左宗棠。左宗棠就把李云麟找去,仔細詢問:“你怎么知道這次出戰要失敗呢?”李云麟有條有理地分析了這一仗失敗的原因。左宗棠認為很有道理,就把李云麟留到了身邊。
這段文字出自李云麟后人之口,當然不是左宗棠賞識李云麟的有力證詞。史籍中也沒有相關佐證,故僅供參考而已。
不久,左宗棠將其舉薦于湘軍統帥曾國藩。李云麟“初謁國藩,適遇其子不為禮,云麟怒批之。國藩延入謝過,使獨領一軍。”《清稗類鈔》中更是有一頗具喜劇性地描述:
“公子以李衣敝而風塵滿面,有慢色。雨蒼直前而毆之曰:而父以禮士聞天下,若慢士如此!公子謝之。始已,文正歸,奇之,留幕下,授以一軍。”
李云麟入幕湘軍后,“論軍略得失,將領賢否,曾公嘉納。”曾國藩在給曾國荃的書信中評價:“李云麟氣強識高,誠為偉器,微嫌辯論過易。弟可令其即日來家,與兄暢敘一切。”又說:
余生平之失,在志大而才疏,有實心而乏實力,坐是百無一成。李云麟之長短,亦頗與我相似。如將赴湖北,可先至余家一敘再往。
李云麟赴湖北前,曾國藩急切與其商討軍旅之事,足見他對李云麟的器重。
左宗棠也曾致信胡林翼:“李云麟擬即日到尊處,可與談之,加以歷練,大材也。”
咸豐十年(1860)夏,清廷諭令湖北巡撫胡林翼統率東征軍,李云麟奉調赴鄂,任胡林翼部總兵,守松子關兩路口。又隨楚軍克復安徽之潛山、太湖、桐城等縣。曾國荃曾致書表示祝賀:
久不晤叔度,懷想日深。前于里門得手書,欣悉太湖之捷,卓著勛勞。此為吾弟發軔之始,即建懋功,將來事業必有遠勝于時流將帥者,為吾弟幸,更為吾弟祝也。
左宗棠擔任浙江巡撫后,因軍事、吏治急需人才,上奏請將李云麟調赴浙江委用。疏稱:
浙江列郡淪胥,大局糜爛,吏治、軍事需才孔殷,非加意搜羅,量才器使,不足以宏濟時艱,共持危局。以臣所知,漢軍正白旗兵部候補主事李云麟,剛明耐苦,在湖北帶勇有年,曾立戰功,毫無軍營習氣,質地實堪造就……請敕下正白旗漢軍都統、江西、湖南、安徽各撫臣,迅速催令前赴臣軍,聽候差委,將來即請留于浙江,按照資階酌量委署序補。
此次李云麟赴左宗棠軍營,是兩人闊別已久的再次會面。李云麟赴浙后,即因增募新軍,由浙赴鄂,同時為了籌集軍餉、招募士兵,來往于湖南、浙江、湖北之間。曾國荃對其才干有所贊譽:
夙維閣下槃才碩畫,足以宏濟艱難,此次鞠旅浙中,同人無不拭目以觀雄才之建樹。惜王事鞅掌不及東來,鄙人未得一聆方略,為悵悵耳!……握別兩年,耿耿之衷,無日無之。倘明年得會于浙杭之間,共平吳亂,天緣會合,亦快事也。
同治元年(1862),因收復湖北襄陽府有功,清廷“賞郎中李云麟、守備葉培等花翎”。并奉調任新招募的毅建五營統帶。同治二年(1863)二月,湖南巡撫駱秉章以陜南軍務吃緊,保舉候選員外郎漢軍旗李云麟督辦陜南軍務。三月,清廷簡派江西布政使李恒接辦陜南軍務,李恒在長沙致書駱秉章,稱三月中旬起程赴陜。駱秉章以陜南軍務須人代統,復又上奏保舉李云麟。疏稱:
查有湖北派防鄖西之郎中李云麟,曾經遍歷各省軍營,曉暢戎機,經臣奏調在案。近接該員來稟,自愿率所部二千八百人,再增募五百人,由興安約會川兵而進,以剿為防。
李云麟率部抵達陜西后,與多隆阿、張集馨等人關系不睦,且因軍務積勞成疾,上奏請求回籍調理。清廷下諭將其革去四品京堂。即行回旗。仍以郎中候補。
同治五年(1866)五月,李云麟署理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因伊犁將軍榮全未到任,兼署伊犁將軍之職。他會同烏里雅蘇臺將軍麟興上奏,請求設立布倫托海辦事大臣。在“布倫托海適中之地,建置治事,妥為安置。”李云麟任布倫托海辦事大臣。因倡捐引發布倫托海民變,被清廷革職查辦,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
同治十二年(1873),賦閑在家的李云麟被左宗棠重新起用,奉旨赴甘肅軍營效力。在奏疏中,左宗棠對其也是贊譽有加。他說:
前布倫托海大臣李云麟,因事獲咎,臣不知其詳。惟該革員實臣所深知。咸豐十一年,臣初任浙江巡撫,曾以該員剛明耐苦,質地實堪造就,列保具奏。嗣后只見過一次。迨臣入秦度隴,聞該革員前在漢中剿賊,頗有聲績,士民猶稱頌之。后在烏里雅蘇臺被劾,臣因未悉其原委,不敢妄有論列。然其為人,實耐勞苦,性不好利,而有恤民之心,則臣至今猶敢具保。至其侈論大局,喜言奇計,有時未免視事太易,則由其閱歷來深之故。就其質地言之,實亦一時罕有也。合無仰懇天恩,俯準敕下漢軍正白旗都統,查明該革員現在何處,飭令速赴臣營差委,臣當加意磨礱,俾去其短而成其長,于西事冀有裨助。
此外,左宗棠還在書信中流露出了對李云麟的急切懸盼之心:
臺從西來,正慰遐想。西事漸轉,如餉糧足資敷衍,尚可措手。弟自閩浙移節,即人窘鄉,各省關積欠協款已至二千七八百萬,任是掀天揭地手段,亦何所施。閣下曾經布倫托海,當已飽嘗況味。書來,顧盼偉然,固征烈士壯心,亦可謂不擇地而蹈矣。聞舊部將棄多愿從行,行至西安,則從人益眾,囑致糧臺設法接濟。
此時的左宗棠,對李云麟的優點比較看重。“實耐勞苦,性不好利,有恤民之心”的特質對于向有實干精神的左宗棠而言,無疑是其選拔官員最注重的一點。至于“侈論大局、喜言奇計”的缺點在左宗棠當時看來,僅是閱歷不深而已,無關大礙。故對其存有包容之心,欲用所長而磨其所短,力圖培養成自己的得力助手。
光緒元年(1875)李云麟丁憂期滿后,由北京趕赴左宗棠軍營。此時,左宗棠親自駐守肅州,已做好了用兵新疆的準備。劉錦棠出關前,為了發揮李云麟的特長,左宗棠派其協助劉錦棠作戰。李云麟果然不負厚望,配合劉錦棠西征大軍“偵查賊情,諏稽地利,一切資其贊劃。”為收復新疆北路作出了貢獻。
北路底定后,西征的軍事重心移至新疆南路。左宗棠慮及軍事和地方政務均須料理,上奏請求開復李云麟已革副都統職銜,仍試圖將其刻意雕琢成一位能干的邊疆大吏。他在奏折中說:
現在新疆北路肅清,規復南路,不但軍務需才,以后經理地方,亦正需指臂之助。李云麟質地實堪造就,早經陳明。合無仰懇天恩,準將李云麟開復副都統銜,并賞還翎枝,由臣加意磨礱,消其躁志矜情,歸于穩實,隨時差委,冀可成一人才,于西事不無裨益。
可見,左宗棠西征期間,因軍務乏人,李云麟作為左宗棠以前的部屬,才干素著,故頗受左宗棠所看重,曾先后三次上奏舉薦,倆人關系處于正常狀態。
二、李云麟與左宗棠的交惡
李云麟與左宗棠關系的惡化,始于其二次入疆之時。
西北地區歷來貧瘠,而且兵多餉少。自清初以來即依賴東南各省協餉解決軍費。李云麟人疆前,曾致信左宗棠,言及招募勇丁出關之事。左宗棠曾就兵餉問題提示過李云麟,勸其勿帶勇丁。信中說:
竊維西事之壞,由于勇丁太多實餉太少,弟度隴后,費盡心力,裁汰歸并,乃稍有眉目,而前任楊、穆兩公未完之件,始稍了妥。辦賊之功無可言,潛銷勇患之功竊足自許。閣下曾嘗帶勇之苦,從前漢中欠餉未清,茲復各處張羅為帶勇計,何耶?克庵幫辦軍務,弟請其募帶親軍一千,渠固辭不允。此時想已行抵西安,聞其騶從幕客不過百人,此外則兩哨耳。各省肅清,方以去兵節餉為事,即陜甘亦然,閣下乃從新招集耶?@
而且,左宗棠認為現在招募的士兵,大半成為游手。一旦入伍,遣散不易。所以向李云麟明示:“總以不帶勇丁為是,如隨從太多,可速資遣。此間無餉發也。”
盡管左宗棠業已致信加以提醒,但李云麟并未聽其勸告,依然帶勇行進。對此,左宗棠深表不滿,曾致書沈吉田:
近日連接李雨蒼信,知已西來。此公本舊雨也,弟前此曾薦過兩次。其勤明耐苦,本為難得,然舉動輕率,實所不免。來書擬帶勇丁度隴時,弟已飛信止之,恐從者如云,又添一累。過西安時,如需盤費,可由尊處給之,若在陜招募,則斷不可耳。
在這件事上,左宗棠對李云麟的做法比較反感,成為兩人關系惡化的先奏。
李云麟入疆后,左宗棠派其辦理了一件事關中俄交涉的案件。
光緒二年(1876)四月,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英廉拿獲一名騎馬行劫的哈薩克人綽蘭。經過審訊后,準備立予正法。俄國駐京使臣布策及翻譯官柏百福聞訊后赴總理衙門辯論,聲稱該哈薩克人為俄國所屬,中方無權懲辦。清廷因關系中外交涉,需經查證后,方能制定應對之術。遂令左宗棠等人查實辦理:
此案哈薩克是否中國所屬,私投俄國?抑系分歸俄境之人?亟須查有實據,毋稍欺飾,方足以資辯論。著左宗棠、金順、英廉即行確切查明,會同核議,據實覆奏。仍即查照約章,設法區處,就近行知俄官,妥籌辦結,以彌釁端。
左宗棠選派李云麟和候補直隸州知州劉詳匯赴瑪納斯、塔爾巴哈臺一帶調查。臨行前,叮囑李云麟等人將各案情節查訪確實:
凡有地址、時日可考、有數目可據、證輔可憑者,均逐一詳細稽查,務得實在證據,以資辯論,不必預存成見,徑下斷語。蓋委查之件與承審不同,若著論斷,便于體制不同,且慮因而失實,致事理不得其平,轉貽口實也。
李云麟一行于光緒三年(1877)九月十六日抵達塔城,傳喚額魯特旗總管孟可吉勒嘎爾和佐領以下官員,詢問行劫之哈薩克人綽蘭一案。問及綽蘭投俄的確切時間及是否原為塔城所屬?之后自投俄國諸細節。額魯特官員據實回復:
塔城所屬之哈薩克,舊有三種:其一、阿吉公所部之哈薩克,分十二柯類,素稱良善,現經隨地分歸俄國者三柯類辦,其八柯類半現屬塔城;其一、黑宰哈薩克,舊有中國所設頭領,年遠無考;其一、為拜吉格特哈薩克,即綽坦汗所屬者。此兩者人數眾多,各以數萬計。自塔城變亂時,即投俄國。同治十一年塔城分界后,隨人與地俱歸俄國,而此兩種人時常越境滋事。其拜吉格特哈薩克,曾勾結漢回,攻陷塔城,尤為不法。前經呼圖克圖棍噶札拉參帶兵剿辦,稍為斂跡。近日恃俄國之庇,復益猖獗。正法之綽蘭一名,實系拜吉格特哈薩克部內之人,于同治三、四年間塔城變亂時,自投俄國者也。
李云麟等獲取確鑿證據后,總理衙門將左宗棠所列憑據呈送俄國使臣,俄方無詞以應,此事方才了結。
此次俄方借英廉正法哈薩克人綽蘭越境搶劫一事,向中方發難。意在拖延交還伊犁,左宗棠對此詭謀早已洞悉。事后,他在給總理衙門的函件中力主對俄采取強硬態度。他說:
俄人屢次無理取鬧,令人憎厭,無非為遲還伊犁作勢,早在洞鑒之中。李云麟等取有憑證,彼欲挑拔,無從置喙,亦在意中。過于含容,恐無以戢其貪心,仍然不奪不饜。所喜尚知顧惜體面,啖之以利,或借此定其界畫,可斬斷葛藤,免致重煩唇舌也。
李云麟赴塔城調查之行,盡管取得了預期結果,但左宗棠對其頗有意見。
首先,李云麟和劉詳匯于光緒三年(1877)十一月十七日調查取證完畢后,途徑烏魯木齊時,將復查公文先行呈送左宗棠。李云麟歸途中因風寒感冒,沿途調治,并滯留關外。劉詳匯只好一人趕赴肅州,向左宗棠面陳調查情況。李云麟卻以生病為由,遲不出關,令左宗棠大為不滿。他說:
李雨蒼好發議論,狂而不直,舉動離奇,弟屢加訓誡,望其有成,毫無悛改。前委赴塔城查中外交涉各案,諄囑其論而不斷,伊并自言案而不斷,乃回程逗留不進,兩次信來,議論風生,荒謬頗甚。聞近在古城,不遽入關,不知有何意見?昨次檄行古局令劉詳匯先入關回銷,可即傷催,不準違延。李雨蒼則暫置不理可也。
其實,左宗棠派李云麟赴塔城調查,是有其考慮的。一者,李云麟為漢軍旗人,通蒙古語,此次訪查者為額魯特旗蒙古官兵,李云麟較為合宜;其二,李云麟有新疆從政的經歷,擔任過布倫托海辦事大臣,熟悉邊疆情形。盡管如此,左宗棠仍對其心存疑慮,故派劉詳匯與其同行。調查行程中,李云麟和劉詳匯因意見不合時有齟齬。對此,左宗棠在給金順的信函中流露出了對李云麟的嗟怨之聲:
李雨蒼之為人,麾下所知也。弟念其性氣伉爽,潦倒半生,頗思有以振之。近復因其熟悉邊塞情形,委赴塔爾巴哈臺查辦事件,恐其未能周密詳慎,或有率忽粗疏,以致蹉跌,故復委劉牧祥匯與之同行,可資裨贊,亦實所以愛之。雨蒼未能體會,出關以后,聞即分道揚鑣,大有同役而不同心之意,殊所不解。
其次,李云麟赴塔城調查途中,曾致書曾國荃,論及光緒二年左宗棠向山西催餉一事。時任山西布政使林壽圖曾因境內旱災嚴重,協餉未能如數按時運解新疆。左宗棠曾上奏參劾其紊亂餉章,請求予以處置。清廷下旨:
山西布政使林壽圖不遵照戶部奏定餉章,蒙混具詳,非尋常貽誤軍餉可比,著交部議處。前山西巡撫鮑源深僅據林壽圖詳請具奏,不將歷屆成案詳為查核,亦有不合,鮑源深著一并交部議處。
左宗棠參劾林壽圖的奏疏曾給李云麟閱看,李亦未表示不同意見。但李云麟赴塔城調查時,途經嘉峪關,由嵩武軍委員送信于曾國荃,書中言及“晉省旱既太甚,何堪當此虐政?愿閣下棄曲從直,早為地步,此間兵事秋冬之交必有變動,以天時人事均未協也。”信至肅州時,因封函并未粘固,左宗棠得以閱知書信內容,一笑置之,并隨手焚燒。盡管此信未至曾國荃之手即毀于左宗棠,但在左宗棠看來,李云麟有意挑撥其與曾國荃的關系。他給劉典的信中說:
沅浦與弟本無齟齬,昨因餉事似不免芥蒂,蓋由雨蒼造語有以致之,沅浦尚未覺其詐忠耳。
還有,李云麟奉命赴塔城調查期間,左宗棠派其與劉詳匯同行,而且明定劉詳匯皆為派員,并非隨員。但李云麟出關后,為自己刻制了一個“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營務處李”的銜條,知行各處,結果所到之處,都呼為欽差。此事連伊犁將軍金順也得以蒙混,對其敬畏有加。李儼然以欽差自居,隨行劉詳匯居然成了委員。左宗棠認為李云麟不無招搖撞騙、越權行事之嫌。
可見,李云麟二次人疆之初,即與左宗棠之間已產生了裂隙。而李云麟的塔城之行則加劇了二人關系惡化的進程。
三、從《西陲事略》透視李、左關系
李云麟辦理完塔城事宜后,與左宗棠的關系已經惡化,他亦深感難以在左宗棠手下從事,故于光緒四年(1878)二月稱病辭職。左宗棠向清廷上奏:
查該員自光緒二年四月來肅,臣引居營幕,朝夕晤對,加以箴砭,冀其稍有成就,以備器使。上年六月,因其熟悉北邊情形,委赴塔城查事,并委候補直隸州劉詳匯與之偕行,幸無違誤。然察看李云麟言語舉動,已成心疾,不僅寒暑之為災也。茲既因病請假,應即資遣回旗。
李云麟卸任后,于光緒四年(1878)九月著成《西陲事略》,呈遞清廷。分為《論往七則》、《述今十二則》、《察來六則》三卷。書中縱論晚清新疆史事、人物功過、新疆局勢等。其中對左宗棠督師西北的功過則論述尤為詳細。
《論往七則》中有一篇《相臣功過》,系李云麟專對左宗棠的評價。書中說:
今東閣大學士湘陰左公,以積功致高位,其勛名著于當時,無須贅言。其性情人品,暇瑜互見。其遇事也,堅韌強毅,獨任艱巨,是其所長。而能伸獨斷不能集眾思,又好是己非人,以致人言不進,是其所短。不辭勞瘁,巨細躬親,是其所長,而疑忌性成,決不肯以事權假人,每每顧此失彼,舉近忽遠,是其所短。
這一點評,指明了左宗棠為人行事的優缺點,還算是較為中肯之語。左宗棠喜歡遇事獨斷的特點,從其書信中亦可見一斑。他曾給胡林翼的信中說過:“辦賊非有大權不辦,使我以數千人獨擋一路,何嘗不可有成?”
李云麟認為,左宗棠在湖南人幕期間和擔任浙江巡撫期間功多過少,督辦陜甘軍務時功過參半,而辦理新疆軍務則過多功少。他指出:
至于辦理陜甘軍務,則功過相半,何也?左相承楊、劉諸人辦理失當后,驅南軍用之北方,風氣未宜而能驅任策力,殄除強寇,其調兵遣將、籌劃布置俱有可稱。卒清疆圉還之職方,是其功也。而亂平后安插降眾,未能協宜。終貽后患,其過猶小。西北大患在兵丁,額餉仰給南方,匱則生亂。
李云麟認為左宗棠督辦陜甘軍務有兩大失誤,一是鎮壓回民起義后,將楚軍客勇分防兩省境內,導致他人難以接手。“外亂雖平而客兵不能撤,本兵不能復。”另一失誤即是軍餉艱難:
甘肅境內專恃外省協撥,有兵無餉即是為亂根。及大亂初平,諸務草創,正可興利除弊,改弦易張,使境內能養兵,無需盡賴協款,建經久不易之謀,乃不次之務,而惟竭海內之力供支楚軍,日不暇及,饑匱時虞。
李云麟對左宗棠在新疆的軍事及善后活動非議更大。主要集中于三方面:
一是坐失兵機。首先,收復新疆的占線過長,而左宗棠卻遠在肅州遙度,貽誤軍情;排擠金順,不許幫辦金順節制湘軍和蜀、豫各軍,導致西征軍漫無統屬。攻打古牧地、瑪納斯和烏魯木齊的戰役中湘軍與金順部爭功,導致金順部隊久困瑪納斯城下。復調湘軍,又因號令不一,久攻不下。攻克后濫殺降卒,損威失重;收復吐魯番后,白彥虎與阿古柏部隊棄城向西逃竄,本應一鼓聚殲。但湘軍因爭糧爭功,以致白彥虎繼續逃竄;帕夏自盡后南八城內亂,未能及時進兵,喪失了迅速收復南疆的機會;進剿南路時,欲使湘軍獨占全功。未能抓住戰機。清軍抵達阿克蘇后,伯克胡里求獻白彥虎之時,因前方將領不敢決斷,導致首逆竄逃俄國,失去了獲得全功的機會。
二是虛靡帑項。左宗棠用人喜諛而惡直,舉近而忽遠。所設糧臺、轉運各局,東自上海起,西至關外南北兩路止,東西長達一萬多里,防勇從潼關到新疆,東西將近萬里。后勤、戰線之長,非左宗棠一人所能周詳,但不肯他人與聞其事,故而百弊叢生。李云麟列舉了其中六條:一曰局員之侵漁也;一曰運腳之浩繁也;一曰楚軍之虛耗也;一曰湘軍之浮濫也。李云麟認為收復新疆只需實餉一千多萬兩即可著有成效,但左宗棠辦理四年之久耗費兵餉三千多萬兩,而且“根本之圖,絲毫未立,中外皆為之困。是否虛靡,至明且顯,受任責成,咎將誰歸歟?”
三是籌劃乖方。李云麟認為關內外虛空凋敝,收復烏魯木齊后關外藩籬已固,即應罷兵,以休養生息為重。但左宗棠“不卹人言,競以地不可棄,兵不可停,且議建行省,設郡縣,此皆鋪張揚厲之謀,當務美觀,不求實濟。”而且認為:“烏垣守備不固,則伊犁雖得難守,南疆雖得必失,與其墮成功而啟后患,莫如慎終于始。”
除枚舉左宗棠新疆軍事活動中的以上失誤外,李云麟還是新疆建省最激烈的反對者之一。在《西陲事略》中,他提出了八條新疆不可改建行省的理由:
1.新疆建省,窒礙難行。宜郡縣者,惟內地遷居之民。今關外數千里,所余戶民,不及五千戶,合計不抵內地一縣。郡縣之制,以民為本,現在郡縣根株已絕,而言建省適得其反。
2.舊設有兩州、六縣、三廳。經此大亂后,已苦官多民少,無可為治,更無添設之必要。
3.欲徙民實邊,則中隔大戈壁,皆橫亙千余里,水草缺乏,難以舉辦。
4.南路纏回,非郡縣所能治。
5.北路旗盟各部,亦非郡縣所能治。
6.曠日持久,致北路善后事宜,延擱不能舉辦。
7.南路八城,留兵少則備多力分,不足彈壓,留兵多則耗餉難支。
8.回疆雖多饒沃,然無堪建為重鎮者,就地取資,則斷斷難行。
綜觀李云麟抨擊左宗棠的數條失誤,姑且不論是否全部屬實,僅就當時西北邊疆的局勢而言,收復新疆一百多萬平方公里淪為異域的國土,左宗棠的功績無論在當時還是后來皆少有非議。而且,李云麟所列失誤中,所謂湘軍不許金順節制而欲獨占全功之類的論調,可能反映了部分事實。但如果反觀新疆變亂后歷任滿人將領景廉、榮全、成祿、金順等均未能遏制新疆糜爛之局的情形后,恐怕很難認同李云麟的觀點。其次,虛耗帑項之說,也值得推敲。作為一支龐大的西征軍隊,倘無充足的后勤和餉源,實在難以支撐。即或如李云麟所列舉的數端情況,清政府的八旗和綠營兵中又何嘗沒有侵漁、浮濫之狀?李云麟所說辦理新疆事務僅需一千多萬兩白銀即可,左宗棠卻耗費了三千多萬兩。即便情況真如所說,退一萬步講,用兩千萬兩白銀換回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也無可厚非。況且西征將士在疆場上浴血奮戰,戰死者、傷亡者又何止數百上千,其愛國之情又豈能用金錢折算。至于李云麟所言籌劃乖方,更是令人費解其用心。收復烏魯木齊后即刻罷兵,置廣闊南疆地域和百姓于不顧,任由阿古柏匪幫及其勢力踐踏和蹂躪,新疆一分為二,西北關內屏障全失,其后果何堪設想;新疆建省之議,眾所周知,左宗棠是力倡者,李鴻章是反對者之一,但李鴻章的意見大多是在給同僚們的信函中表示的,更多的是一種個人見解。其影響度尚屬有限。而李云麟反對新疆建省的意見是直接上奏給清政府的,其重要出發點是認為建省會限制甚至大大減少八旗官兵的某些特權,并以“歷來西陲用兵,皆以旗員為帥”為由對左宗棠及一批漢族將領的任用表示異議。其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影響了清廷的決策,使清政府在新疆建省問題上舉棋不定。關于新疆建省的可行性及左宗棠決策的正確與否,學術界成果甚多,早有定論,本文不再贅言。
總之,《西陲事略》中李云麟對左宗棠個人的評判及其縱論新疆史事,可知,兩人關系已經急劇惡化,而且其恩怨已經上升到事關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了。《西陲事略》作于光緒四年九月,是在李云麟和左宗棠分道揚鑣之后,故其書中對左宗棠所持成見在此已是暴露無遺了。
四、李云麟與左宗棠交惡原因
李云麟與左宗棠二人交惡,具體原因前已述之。但若仔細考究,主要在于性格因素和政見不同所致。
就性格方面而言,李云麟性格狂蕩且浮論甚多,為湘軍諸人所深知。李云麟赴湖北前,曾國藩在給曾國荃的書信中說:
李雨蒼于十七日起行赴鄂。渠長處在精力堅強,聰明過人。短處在舉止輕佻,言語傷易,恐詠公亦未能十分垂青。
王閩運在給友人的書信中說:“有狂友李雨蒼手書,諄諄約閩運游河北。”左宗棠也曾多次談及李云麟的狂蕩之性。他給總理衙門的上書中說:
“至李云麟為人,宗棠本亦知之,因其質地尚堪造就,意在加意訓勉,俾有所成。近觀其舉動輕浮,語言誕妄,較前尤甚,實為廢材。
在給譚鐘麟的書信中也說:
李云麟為人,弟素所知,不圖近日語言、舉動尤多出人意表。因其請假,準請放歸。……弟素以豐鎬舊族不耐勞苦為憂,故于旗員之能掃除結習者冀其有所成就,稍備器使。李云麟開復副都統銜花翎,亦欲獎掖成人,或猶可晚蓋,乃競至大謬不然,私心殊難自釋@。
日人沃丘仲子也曾論曰:
云麟居轉兵間,艱苦卓絕,而好先事計利害,自明遠識,竟以是敗。
與李云麟性情相似的是,左宗棠也是志大言大。“自小有夸大狂。每寫成一片文章,必自鳴得意,夸示同學。”“喜為壯語驚眾,名在公卿間。嘗以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左宗棠不僅以諸葛亮自許,還大言“今亮或勝于古亮。”
左宗棠秉性率直和狂傲,而狂傲尤為顯著。他曾自夸日:“當今善章奏者三人,我第一。”這種性格直到晚年亦復如是。據秦翰才在《左文襄公在西北》一書中的敘述:
文襄公從陜甘回來,每和人家談話,還是總要夸張他經營西北的功業。這一點很使人家不喜歡。相傳文襄公新到軍機處,恭親王把一個海防的折子請教他,文襄公每看一頁,因海防而說到塞防,表白他在西北的措施之妙,看了幾天,還沒看完。又有一位紳士間文襄公于兩江總督任上,要談公事,見了三次,沒有談成。因為一見,文襄公就自己談他西北的事,使人無法插嘴。
左宗棠除性格狂傲外,個性剛烈和遇事專斷也是一個重要方面。
《郭嵩燾日記》記載了咸豐八年(1858)十二月初三日咸豐皇帝和郭嵩燾的一番對話:
上曰:“汝可識左宗棠?”曰:“自小相識。”上曰:“自然有書信來往。”曰:“有信來往。”上曰:“汝寄書左宗棠,可以吾意諭知,當出為我辦事。左宗棠所以不肯出,系何原故?想系功名心淡。”曰:“左宗棠自度賦性剛直,不能與世合,所以不肯出。”
正因為左宗棠的剛烈個性,和諸多時人關系均不偕洽。曾國藩、郭嵩燾等皆與之嫌隙甚大。即便與其最信任的老友劉典、下屬劉錦棠之間也曾一度幾至分手。此外,左宗棠遇事喜歡獨斷,事必躬親,不許旁人插手。入幕張亮基和駱秉章期間,“先后專任之。”郭嵩燾也說:“季高才氣橫絕一世,而用人專持意見。”
由上可見,李云麟和左宗棠在性格方面都有狂狷和剛直之處,但二人也有不同點。李云麟在有關軍國重事上多是浮論,很多不切實際,有些言論甚至足以誤國。左宗棠雖然狂傲,但存有實干之心,其戰略構想亦能切中時弊。性格上有共通之處,彼此若能包容,尚可求同存異,共謀國是。但不幸的是,左宗棠以惜其才、鑄其才的目的兩次起用李云麟,而李云麟卻未能深悉左宗棠的一片良苦用心,在新疆期間,依然我行我素,舉動、言語離奇,最終導致雙方關系破裂。
李云麟和左宗棠交惡原因中,除上述性格因素外,二人的政見分歧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方面。
首先,政見分歧體現在收復新疆的戰略方針上。
早在左宗棠督辦新疆軍務之前,李云麟曾在《挽回西北大局》的奏疏中已經陳明了自己對新疆事務的意見,也就是他一貫主張的收復烏魯木齊后緩圖南疆的計劃。他說:
現今三路之兵,果能會剿,則烏魯木齊必能克復。既復之后,延議必將分兵剿辦,用兵太多,力有不及。若僅有二三萬人分剿,各路所得之城,又須分兵防守,兵力單薄,終必因一路之壞諸路皆壞。是徒務剿辦之虛名,而失致勝之實。臣以為當烏魯木齊克復,即置重兵居守,修備糧儲,然后揀練馬步精銳萬數千人,合成一軍,審度賊勢之強弱虛實,相機雕剿,務使我之力聚,賊之勢散,此股既平,續剿彼股,聲威益妝,剿撫兼施,則南北兩路可望次第削平,如是則用兵之綱領得。
李云麟的這種戰略計劃和左宗棠的收復新疆的方針大相徑庭。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戰略方針是“先北后南”。收復北疆后,即迅速移師攻取南疆。李云麟卻力主鞏固北疆城池,然后徐圖南疆。赴塔城調查取證完畢歸途中,李云麟曾致函左宗棠,認為烏魯木齊城守空虛,與其“以數百萬餉打南城,不如以重兵巨餉注烏魯木齊。”李云麟到達烏魯木齊后,劉錦棠在一月內連續克復新疆東四城。對于這一重大勝利,李云麟仍持非議,左宗棠未予理睬。但在給譚鐘麟的信中流露出了對李云麟極大不滿:
上年克復烏垣時,弟于當食,正接捷書,滿座均歡,獨李云麟一人神色沮喪,殊不可解,蓋忌嫉之心所迫致然。宜此次南疆克復,非所樂聞,而預為緩南急北之說,妄思阻撓也。
其次,新疆建省問題上的意見相左。左宗棠鑒于有清一代治理新疆的得失,力主放棄原有的治邊之策,收復新疆后改建行省,使其與內地的行政機構接軌。這一主張對于新疆的穩定和發展,無疑是當時切實可行的治邊方略。但李云麟卻激烈反對新疆建省,并提出了八條新疆不可建省的原因,更多考慮的是新疆建省后滿族將領權力的縮減。作為反對新疆建省的主要代表,其觀點完全是從私利出發,而置國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顧。
綜觀李云麟和左宗棠的關系,可以發現,左宗棠由賞識李云麟之才,到最后兩人交惡,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李云麟的缺失所致。左宗棠作為李云麟故交,深悉其才,但亦對其缺點早有洞察。用兵西北期間,因軍務乏人而起用李云麟,本想將其多加歷練、磨礪,成為國家的有用之才。李云麟復出后,在收復新疆的戰斗中亦曾用心籌劃,并積極辦理中俄交涉的調查,也取得了圓滿結果。但因天性使然,其狂狷之氣未改,時常浮論新疆時勢,侈言新疆戰事。尤其是關于新疆軍事計劃的論述和阻撓新疆建省之議,不僅沒有大局觀,而且還存有私心;這就不是性格方面的缺失所能解釋的了。總之,李、左關系由正常到交惡的過程,明顯地反映出了晚清時期滿、漢官員在新疆問題上的芥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權力博弈。
(責任編校:文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