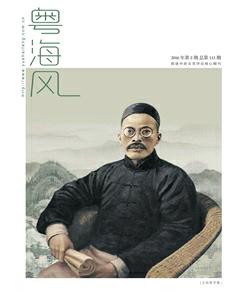從“農民小品”到“公民小品”
徐海龍
趙本山自1990年首登央視春晚舞臺到2011年的二十二年里,共獲得十六次“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我最喜愛的節目評選”一等獎。如今“趙本山小品”在熒屏上經歷了過山車式曲線,更應該對其進行歷史反思。在以農村社會為基礎的中國,趙本山小品中的農民形象有著龐大的收視基數,趙本山進一步將傳統農村生活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和都市化進程結合起來,塑造一個個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經受巨大沖擊的“新農民”形象,直指經歷社會轉型的所有國人的心聲。但是,各個教育水平、社會階層的觀眾對其接受、反饋形式,是不同的。
一、農村觀眾和底層城市居民對趙本山小品的認同
農村觀眾和底層城市居民在趙本山的小品中看到的是大眾傳媒對農村人的“再現”,盡管本山大叔的形象不能代表全部農民,但是該形象所具備的“淳樸”、“安貧樂道”、“軟弱又蔫壞”、“好面子又講情義”、“重輩分又攀附權貴”等性格,基本抓住了中國農民和底層城市居民的典型特征。
例如小品《拜年》中趙本山和高秀敏飾演的老兩口為了繼續承包魚塘,去給既是鄉長又是遠房侄子的范偉送禮。剛進家門時,老兩口一副敬官畏官的狀態,但又拼命以攀親戚、立長輩的方式來套近乎、求平衡。而在得知鄉長已經“下來了”之后,態度立刻180度轉變,高秀敏開始以“三胖子”稱呼范偉并以長輩身份訓導他的“腐敗”作為。但趙本山此時凸顯了重情重義的傳統美德,一起喝酒來安慰侄子。在小品《捐助》中,趙本山與王小利飾演一對親家,他們共同的勞動收入被趙本山誤捐給了孤兒寡母。在電視采訪中,趙本山謊說自己自愿捐出,并一再阻止親家王小利說出真相,充分表現了農民“打腫臉充胖子”的心態,最終兩人從分歧到和解,都不再討回錢款,而接受捐助的寡婦愿意讓自己的兒子將來贍養二老。小品《心病》里,趙本山飾演的鄉村醫生趙大寶為了開導因中大獎而抽風的村民(范偉飾),用通俗又富含比喻修辭的語句表述了普通百姓的生死觀和財富觀:“在歲月的長河中,人好比天上的流星,來匆匆,去匆匆,刷——說沒就沒啊”、“人生在世屈指算,一共三萬六千天,家有房屋千萬座,睡覺只需三尺寬。……房子修得再好那只是個臨時住所,這個小盒才是你永遠的家”。
《拜年》《捐助》《心病》等一系列小品,自然而然地讓鄉土社會固有的善良淳樸和代際關愛沖破了官僚等級和金錢交易而表現出來。普通百姓看到了自己的真實生活和人物狀態,而不是“遠遠地”觀看琴棋書畫、美女豪車、高樓大廈等媒體景觀。這種真實性更在于對農民性格缺陷的展示和諷刺。《拜年》里,當得知范偉已經升為縣長時,老兩口回到了畏官狀態,驚恐和奴性的狀態比之前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以轉折的劇情引發人物狀態的逆轉,是趙氏小品常用的技巧,類似的還有《心病》,趙本山在病人面前表現的淡泊名利、寵辱不驚,而范偉坦白自己以前的女友就是趙大寶的妻子時,趙大寶也犯心病了,最后范偉決定將100萬分給趙大寶時,趙大寶直接抽風倒地。敬官畏官、順從懦弱、小富即安,這是農耕文明中最深沉的底色的另一面,普通觀眾觀看《拜年》《心病》這樣的小品,印象最深的就是農民這些雙面性格,小品“再現”了這類性格造成的各種矛盾心態、處事缺陷和人際關系錯位現象,這些現象又因為商品社會的浸淫而更加鮮明。
農村觀眾以及進城務工群體對趙本山認同的另一個方面是其作品包含了對城市時尚、權貴階層的諷刺、戲謔和貶損,與此同時宣示了都市外鄉人的身份回歸——這讓受眾體會到自身主體性的增強。《牛大叔提干》、《三鞭子》等作品不約而同地以諷刺官場、造福百姓作為主旨思想,揭露官員腐敗、不作為,為底層百姓宣泄情緒,撫慰心靈,因此引起強烈反響。《牛大叔提干》中的臺詞:“上頓陪、下頓陪,終于陪出了胃下垂”,“扯淡、扯淡,就是從這來的”一時成為坊間的流行話語,反映出社會普通民眾的共性心理。在《不差錢》里,盡管趙大叔為了讓孫女丫蛋上《星光大道》而招待、“賄賂”電視臺編導,但是大叔在熱情和無知的外衣掩飾下,卻不斷調侃北京來的編導。例如他對電視臺編導說:“你不是找爹么?找對了”,并且把對方當作丫蛋的已故姥爺的遺像來跪拜,村里的歡迎儀式是:“弄了個大房間,給你弄個大照片掛中間,周圍全是花,白的、黃的都有……鄉親們拿著筆都哭了”。《紅高粱模特隊》里,趙本山飾演的模特隊長(兼裁縫)接待城里來的服裝設計師的時候,更是在尊敬、學習的姿態下,把時尚界的浮華、高傲、不接地氣的一面大大嘲弄了一番:“頭上包個綢子,露個肩膀頭子,一身玻璃球子,走道還直晃胯骨軸子”、“沒有廣大勞動人民,吃啥?沒有廣大勞動人民,穿啥?沒吃沒穿了,你還臭美啥?”
可以看出,趙本山塑造的“都市外鄉人”形象實際上是徘徊于農村與都市之間、無法融入都市的個體,其身份經歷“原生態進入——弱化、迷茫和扭曲——再強化和反擊”的軌跡,這種軌跡與農村受眾(包括留守的和進城的)是一一對應的。盡管“土文化”對城市時尚文化的反擊是短暫的爆發,但農村受眾確實在此刻體驗到身份回歸和價值充盈,并且這種價值不是商業價值而是人性化的。就像“白云、黑土”系列小品里說的:“我們就是農村普通的小老頭、小老太太”,老兩口經歷了上電視、出名、出書等人性畸變之后、在“二人轉”中終于找到(回歸)了屬于自己身份的歡樂。
不過,現實是,時尚服裝設計界并不僅是《紅高粱模特隊》里表現的樣子,而趙本山的日常衣著也是名牌集于一身。在當代中國城市化進程裹挾每個個體的現狀下,外鄉人的教育程度、生活狀態、文化品味都不可能倒退回去。所以受眾對趙氏小品的接受只能在媒介文本中實現,從這個意義上,似乎可以說受眾自發的懷舊情結成為趙氏小品利用和引導的目標,農民受眾獲得了回歸的假象。“趙本山春晚小品中的農民常通過對其他階層的戲仿而發泄心中的不滿和諷刺,……將他們裝大款、奢靡無度、狐假虎威、自命清高、打官腔、熱衷炒作等缺點二次曝光。……在一定程度上讓農民階層獲得了某種心理平衡”。①
二、都市白領和知識分子對趙本山小品的認同
趙本山塑造的“徐老蔫”、“趙老蔫”、“趙大寶”、“黑土”大叔等人物具有的性格特征和生活態度符合絕大部分國人共同的價值觀。但相比較而言,農民受眾從生活真實感、身份回歸感、權力(暫時)優勝感等方面接受了趙氏小品;而都市白領和知識分子面對趙本山的小品,通常進行一種費斯克所謂“生產性消費”——他們憑借較高的教育水平、較大的知識含量和較豐富的符號體系,更多的是從喜劇表演技藝、審丑、自嘲、符號隱喻、針砭時弊等方面認同了趙本山。
首先,趙氏小品乃至很多春晚小品慣用的文明與落后的反差、話語歧義、父子關系錯位、夫妻關系誤認、網絡段子改造等等幽默設計方式,已經讓教育水平和文化鑒賞水平較高的受眾產生了審美疲勞,但是趙本山的臺詞把握、肢體動作以及整體節奏控制等各方面的表演能力,以及劇情結構安排,讓作品表現出高超的喜劇技巧,很多受眾愿意反復地欣賞和品味,這也是趙本山小品曾經無數次重播、本人多次被封為“小品王”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趙本山的小品形象始終是一身老舊的中山裝搭配一頂帽檐耷拉的“錢廣帽”,一張“鞋拔子”臉上掛著既樸實又圓滑的笑容。彎腰駝背、雙手插袖、不小心摔倒、脫鞋盤腿坐、背著農副產品去大酒店用餐……這些狀態讓都市觀眾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審丑視角來觀看這個“鄉巴佬”。“看趙本山已經形成一種習俗,一種儀式……他的可笑是因為他走不進今天這個時代,這是趙本山小品快感的非常重要的來源”。②
第三,趙本山的22部春晚小品涉及8個明確的職業:六級木匠、藝術室主任、種植戶、生產隊長、養殖戶、鄉村心理診所醫生、送水工,也就是集中在土地勞作者、農民工、農村知識分子和個體工商戶等階層。“忽悠”系列已經基本變成了市民形象。小品中再現的農民形象實際已泛化為中國整個草根階層,因此其諷刺的對象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了都市白領和知識分子所要諷刺的對象。例如《紅高粱模特隊》對時尚界、模特界華而不實的指責符合了很多都市觀眾的觀念。沒有什么文化水平的“白云”大媽非要出書的情節,暗合了一些媒體、商界人士紛紛出版文學價值不高的自傳的風潮。把村頭廁所用紙等同于暢銷書,用農村老婦影射暢銷書作者,這讓文化水平較高的觀眾(讀者)產生極大的戲謔和批判快感。教育水平較高的都市受眾具有超強的學習能力和解讀隱喻的能力,更喜歡、也更善于從隱喻、反諷的角度來接受趙氏小品中針砭時弊和批判社會的內容。《牛大叔“提干”》里的“扯淡(蛋)”之說;《賣拐》里的“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能把蔫的忽悠邪了,能把奸人忽悠囁了。今天賣拐,一雙好腿我能給他忽悠瘸了。”這些話語在都市受眾之中流行,這并不是說受眾都具備了知識分子的反思、自省的能力,而是受眾能夠在這種話語中生產出屬于自己的意義和話語權力,用來拆穿都市商品社會的蠅營狗茍、徒有其表、裝腔作勢諸現象和人物。最為都市白領和知識分子津津樂道的是小品《策劃》,里面正是充滿了大量對文藝圈、廣告營銷和大眾傳媒的隱喻。
對于身處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的都市觀眾來說,《策劃》中白云大媽自創(化用)的廣告詞:“下蛋公雞,公雞中的戰斗機——歐耶!”經過東北腔調的重復演繹,以半土半洋的形式銘記在受眾腦海,進而被演變出多種版本,如“LV,品牌中的戰斗機”、“Dior,品牌中的戰斗機”,沖淡了高端品牌與人的距離感;“小米手機,垃圾中的戰斗機”,一語雙關,既調侃了國產手機不穩定的質量,又贊揚了小米手機的“出淤泥而不染”,諸如此類的商業化挪用和拼貼,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策劃》還在“公雞下蛋”事件中,映射了文藝界乃至整個社會的荒誕之處,例如公雞隱喻文藝界的男明星、劃雞爪子意味練簽名、決心下蛋意指堅定信念。這樣的隱喻方式產生的幽默是高級的,可以非常迅速地讓教育水平較高的受眾心領神會。對趙氏小品隱喻式解讀,使該受眾群體產生了一種藝術審美和文化讀解的優越感,鄉土味的話語更增加了批判的力度,趙氏小品從而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潛臺詞色彩。
三、知識分子群體對趙本山小品的批判
普通白領觀眾更多是在娛樂中批判、在抵抗中娛樂,用“趙本山語系”來形容自身與職場環境、大眾媒介的權力關系;而知識分子群體則關注趙本山的小品是否表達了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是否揭露社會真實矛盾、解剖國民劣根性,是否能對人性進行藝術深度刻畫、提高文化趣味而不是膚淺笑料堆砌。知識分子群體意識到趙氏小品對一些弱勢群體的丑化式娛樂,比如《不差錢》中女性化的小沈陽、“忽悠”三部曲中愚蠢的廚師范偉,特別是“忽悠”三部曲里趙本山的表演技巧已經爐火純青,但同時也毫不掩飾地對殘疾人的丑化。“憨厚老實、別人說什么就信什么的范師傅接連上當受騙,然而他不僅沒有得到觀眾的同情,反而成為人們取笑的對象。相反,坑蒙拐騙的‘大忽悠即使不能說被塑造成了值得學習的榜樣,至少也是一個相當機智可愛的角色。這樣的作品無疑會給觀眾帶來一種暗示:如果你在生活中像范師傅一樣老實,那么就活該上當受騙;相反,只有像‘大忽悠一樣耍奸弄滑,才能夠如魚得水”。③
更進一步說,趙本山小品中農民形象的“異化”不止是把人的生理殘疾當做笑料,而缺乏農民在“歷史進程中本質的真實”;④小品中的農民形象與大眾傳媒一道,表現出了一種功利化價值觀。“黑土”和“白云”這兩位老人在《策劃》和《昨天、今天、明天》《說事兒》《火炬手》三部系列作品中,為了塑造自身的正面形象,獲得社會的認同和尊重,處心積慮地“采用虛假語言、巴結行徑來諂媚媒體、欺哄受眾;而具有高度社會話語權的大眾傳媒也為二老提供了滋生謊言、助長奉承的溫床與鼓勵機制”。⑤媒介失范既違背了新聞真實性的要求,也不符合公眾的健康向上的信息需求。雖然最后二老意識到回歸本質的重要性,但是作品的全部笑點都集中在他們與媒體的“合謀”過程中。這就使公共媒體成為一個虛幻的擬像空間,鏡頭前的“白云、黑土”與真實世界的“小老頭、小老太太”越發割裂,加劇了受眾對媒體公信力、社會誠信度的懷疑。
四、“公民小品”對趙本山小品的歷史替代
趙本山小品為了凸顯自身主體性和營造文化差異“笑果”,其塑造的農民形象基本上是與城市人、城市生活呈現對立狀態:要么互諷(如《紅高粱模特隊》)、要么是懷舊和鄉愁(如《鐘點工》),要么與城里人勾心斗角(如《賣拐》)。如今,伴隨著趙本山典型形象淡出舞臺,以“開心麻花”團隊為代表創作表演的小品開始在央視春晚等平臺上嶄露頭角。這些小品與趙本山小品的最大區別就是,前者表現和探討了在以“陌生人社會”為主體的城市之中,不同職業和階層的人如何信任、互助,建設一個平等和諧的公民社會,這樣的小品可以稱之為“公民”小品。
社會調查顯示,城鎮居民認為一個“好社會”需要“誠信”的人所占比例為24.7%,比農村居民中相應比例19.7%高出5個百分點。在所有職業群體中,農業勞動者選擇“誠信”的比例最低(18.9%),最高的是專業技術人員(28.8%)。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者對誠信理念認可度為31.5%,而教育程度最低的初中及以下者的認可度僅為20.6%,兩端相差約11個百分點。可以說教育程度越高,越看重“誠信”。另外,對于 “公正”、“平等”、“民主”等理念的認可情況調查結果是,當下中國各個教育水平的群體都非常認同“公正”,農民群體、藍領和體力勞動者更為看重。年輕世代對“平等”、“民主”的認可明顯大于年長世代,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公眾將“民主”列為最重要的價值觀,認同率在60%左右;而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者的認同率僅有35.9%。⑥ 另一項調查的數據顯示,對“人與人之間是互助的”選項的認同率,也隨著文化程度升高而升高,而對于“人與人之間是相互利用”的認同率則隨著文化程度升高而下降。⑦受眾教育程度越高,越認同“反權威、崇尚包容創新、言論自由,認同職業技能、契約交往、社會福利、慈善公益”等內容。⑧因此,更多體現這些價值觀的文化產品會得到教育程度較高受眾的喜愛。
公共精神、公民意識體現為對平等、公正、民主、互助、法治等價值觀的認同。從這個維度看,從2013年伊始,央視春晚上的《大城小事》《扶不扶》對趙本山小品的替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受眾教育水平和文化趣味的提高,也代表了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歷史聲音。
例如2013年的小品《大城小事》,常遠飾演的角色具備了主流文化給予男同性戀的多個符號標簽:服裝設計師、粉色緊身褲加小西裝、女性化的身姿和語氣、眼光挑剔、愛慕虛榮、“毒舌”等等。長期以來,春晚小品中對于“性別錯位”慣常采用丑化戲謔的表現方式,也讓全國主流觀眾形成了刻板認識。但《大城小事》里這個服裝設計師打電話向物業反映小區設施的問題,催促模特公司工作要準時,當他得知發放小廣告的兩兄弟的生活難處,用“你們來到這個城市,這兒就是咱們共同的家,你們不拿這里當家,這兒怎么能把你當親人”的話語,表達了都市本地白領與外來務工人員的互相包容和理解,也感化了兩兄弟。不僅如此,這個服裝設計師還為兩兄弟提供了更好的工作機會。一個“Gay”氣十足的角色傳達出敬業、講公德、平等互助的現代文明理念,終于突破了以往鞏漢林、小沈陽等在小品中被丑化的“偽娘”的形象,成為了整個作品的靈魂人物。
消除潛規則和信息不透明,保障公平正義,維護公民權益,杜絕諂媚權貴、實現群體互助,這些價值觀得到了知識分子、都市居民的一致認同。“引領時代新風尚,傳遞社會正能量”也成為近年來春晚的指導理念。2013年的小品《你攤上事兒了》里面,方清平飾演的有些女性化的男青年形象盡管依然擺脫不了傳統道德的戲弄,但他也閃現出來的現代公民的文明守規的素養。孫濤飾演的大廈保安不畏權勢、不開后門,不怕“攤上大事”,堅持“持證進門”的職業準則,更體現了法治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觀。2014年的《扶不扶》與其說是弘揚“做好事”、“助人為樂”的風尚,不如說是探討了公民之間如何信任的主題;它不僅是揭露和批評道德危機,更是提供了一種在法律體制的維護下公民合作的方式。遇到有口難辯的公共事件,小品中的郝建不僅僅是恪守“自己無責、任人評說”的信念,還要借助于街頭監控攝像頭拍下的證據,而攝像頭卻壞掉了。郝建假裝被老人騎車撞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又回到了趙本山小品式的“忽悠”、“勾心斗角”,但是終究在交警(執法者)處理下真相大白、好人得好報。在小品結尾處,“大媽有醫保!”為雙方達成諒解提供了一種皆大歡喜的新方案。這樣的處理讓觀眾反思:公共設施的缺失、法律不健全、執法不公正、以及不完善的醫保體系,也是導致當前社會出現“見死不救”、“扶老人反被誣陷”的原因。在“做事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之外,法制和秩序是重塑道德、重建信任的社會途徑。2015年的《社區民警于三快》更是以片警“于三快”和邵警官為視角,展現整個社區各個階層身份的陌生居民之間的矛盾關系。可以說,從2013年的《大城小事》、2014年的《扶不扶》到2015年的《社區民警于三快》,央視春晚開始有意識地揚棄《賣拐》、《賣車》、《不差錢》中的小農和小市民的圓滑世故和等級攀附內容。“公民小品”更倡導國家公民精神,呼喚社會正義和法治的完善,開始獲得更多教育階層和文化陣營的認可,將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央視春晚的舞臺之上。
參考文獻
①趙曰超、徐陳琛、周永康:《趙本山春晚小品中的農民形象再現研究》,《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9)。
②師力斌、劉巖:《春晚30年:我們的記憶與反思》,《文藝理論與批評》2012(2)。
③陳國戰:《“春晚”小品應體現正確價值導向》,《中國文化報》2014-12-2。
④參見《教授曾慶瑞真說出“壞話”時,趙本山竟“沖冠一怒”》,《北京日報》,2010-4-12。
⑤閆偉:《從真誠載道到虛浮狂歡(下)——趙本山春晚小品之創作流變與文化表征(1990-2010)》,《聲屏世界》2011(3)。
⑥參見李煒:《社會公眾的“好社會”價值標準調查報告》,李培林等主編,《社會藍皮書:2015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125頁。
⑦參見龔群:《當代中國社會價值觀調查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165頁。
⑧參見趙孟營:《跨入現代之門:當代中國的社會價值觀報告》,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109,122-123,190-191,202-2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