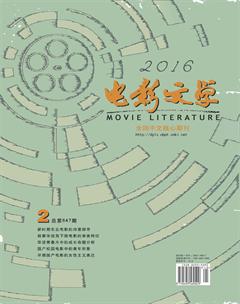《臥虎藏龍》敘事動力解析
王穎怡
[摘要]敘事動力是指能引起、維持、控制、調節敘事主體(作者、敘述者、人物)進行敘事的各種力量。“青冥劍”是電影《臥虎藏龍》的主要敘事動力。影片中,導演以“青冥劍”作為敘事的切入點,情節始終圍繞“獻劍——盜劍——尋劍”展開,人物的行為動機因“劍”而生,“劍”推動著情節的發展、演變。寶劍既控制著故事情節的干枝,又連綴起影片中的眾多人物,并折射出復雜的江湖人心,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同時又彰顯著深刻而多元的主題。
[關鍵詞]青冥劍;敘事動力;情節;矛盾沖突;主題
武俠電影早已有之,可以說武俠片是中國特有的一種電影類型。中國的《電影藝術詞典》將這一類型稱為“武打片”,是以動作伸張正義,使之戲劇化,寓教于樂,增加接受性及教育性。[1]對于武俠電影來說,“武、俠、傳奇”是其敘事的三大元素,因此傳統的武俠片特別注重“武”的成分,甚至不惜犧牲“故事”以“炫技”來取悅觀眾贏得票房。隨著此風的蔓延、興盛,觀眾對于武俠的敘事期待日益減弱,武俠片的發展逐漸步入困境。
2000年,李安執導的《臥虎藏龍》的上映,讓所有觀眾眼前一亮。不僅西方電影觀眾對中國武俠片有了更大的認同,而且無數導演也開始探索武俠片的不同發展途徑。《臥虎藏龍》中,導演一改傳統武俠片注重“武”的外在表現的敘事風格,由單純的“技術”外顯轉向人物內心的深層挖掘。敘事的著眼點不在于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而是表現人物復雜的內心世界、人物不同思想觀念的撞擊。影片因此具有豐富的人文意蘊。
《臥虎藏龍》的成功,給低迷期的武俠電影提供了嶄新的敘事范式。其中,影片的敘事動力十足,故事情節環環相扣,故事結構縱橫開闔。導演以“青冥劍”作為敘事的切入點,人物的行為動機都是因劍而生,情節因劍推動、演變。寶劍既控制著故事的干枝,又聚合著眾多人物,并折射出復雜的江湖人心。無疑,“青冥劍”是《臥虎藏龍》的主要敘事動力,本文以此為視角來進行探析。
一、敘事動力推動故事進程
所謂敘事動力是指能引起、維持、控制、調節敘事主體(作者、敘述者、人物)進行敘事的各種力量。[2]小說的敘事離不開故事,電影也不例外。探討故事就得從事件入手,因為人物與行動構成事件,而相關事件的序列性聚合就是故事。所以,有關人物與行動的各種邏輯規定,就是形成故事動力的內在機理。[2]“敘事一經開始,事件就獲得了自身的動力展開規定性,它本身存在一系列邏輯規定著由開端向結局的演進。”[3]《臥虎藏龍》中,“青冥劍”成為電影敘事的主要動力,成為推動故事進程的重要因素。
(一)展開故事的主體
導演以“青冥劍”來組織故事,敘事以“劍”為切入點,隨著青冥劍的出現,整個故事緊鑼密鼓地展開。青冥劍本是大俠李慕白的兵器,這把有著四百年歷史的寶物沾染著不少江湖恩怨,為了遠離江湖是非,李慕白把佩劍獻給了貝勒爺。寶劍的重現江湖,引起了江湖的動蕩、人心的搖曳以及覬覦寶劍之人的紛爭。在人人都想得到寶劍的利益驅使下,電影的敘事張力得以形成,電影的敘事動力得以激發,整個故事的框架和背景就此形成。而在眾多期望得到寶劍的人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九門提督府的嬌小姐玉嬌龍出現了,觀眾不禁愕然,一個斯文嫻靜的大家閨秀要這兵器作甚?懸疑的產生,使敘事動力蓄勢進一步地鋪展故事。隨著寶劍在貝勒府的失竊,尋劍也就成為情節發展的必然,因此,整個故事就圍繞著“獻劍——盜劍——尋劍”這條主要線索展開。
(二)展開故事的枝節
一部主題意蘊豐富的影片,其敘事線索往往不是單一的,除了主要情節線索外,還會纏繞不少細枝末節。在青冥劍這一敘事動力的驅使下,影片除了展現與“劍”相關的主要情節外,還連綴起其他的人物,穿插了他們的故事,拓展了影片的表現內容,進一步豐富了電影的主題。
如玉嬌龍懷著猶豫的心情竊取寶劍后,對于她竊劍的動機導演并未直接點明,相反,采用插敘的手法,詳盡地刻畫了玉嬌龍與羅小虎浪漫離奇的愛情。這種自由浪漫的愛情是玉嬌龍所向往的,也讓觀眾明白了她為何盜劍,因而“劍”也就成為進一步推動玉嬌龍這一支故事發展的動力。
又如在追尋寶劍的下落時,貝勒府拳師劉泰保意外碰見陜甘捕頭蔡九,并誤之為盜劍之人,緊追不放。蔡九無奈之下只好亮明身份,并說明來京的緣由是為了捉拿碧眼狐貍,而此重犯正好藏身于提督府。在“尋劍”這一情節的支配下,次要人物紛紛出場,碧眼狐貍的出現又為故事“節外生枝”,牽扯出眾多昔日恩怨。至此,影片中的關聯人物逐一展現,而故事也繼續向縱深發展。
因此,青冥劍的出現不僅推動著故事的主要情節向前發展,也引出了故事的旁枝末節,且多條線索相互纏繞、相互推動,大大地擴展了影片的表現內容。
二、敘事動力展現矛盾沖突
托多羅夫曾指出:“故事,就是一種平衡開始通過不平衡達到新的平衡。”[4]這種不平衡指的就是矛盾沖突。矛盾沖突是演繹故事的基礎,沒有矛盾沖突便沒有故事,影視作品尤其需要矛盾沖突。隨著敘述過程中敘事動力的產生及加強,故事情節往往不是平穩順暢地發展,而是表現出起伏動蕩、一波三折的局面,此種起伏動蕩也即作品中人物與人物之間、人物與其內心及人物與環境之間各種因素彼此消長的過程。
(一)展現人物之間的矛盾沖突
人物因性格差異,需要、目的、動機等因素迥異而產生各種沖突,影片中人物之間的矛盾沖突主要體現在“獻劍”與“盜劍”中。
青冥劍是李慕白的隨身佩劍,寶劍的獻出吸引著眾多的江湖人士,人人都希望得此寶物,成為江湖至尊。因此,寶劍無形中成為身份與名望的象征。與此同時,這把有著四百年歷史的寶物也沾染著無數的江湖恩怨,正如俞秀蓮所說:“再好看也是兇器。”作為一名武德高尚、自我修為高深的俠士,李慕白深受武當派道教文化“虛靜”觀的影響,認為一切都是“虛名”,都是人心的作用。一切的“為”都是為了達到“無為”,“無知無欲、舍己從人才能我順人背”。在道家思想的引領下,他閉關修煉,獻出寶劍,希冀達到道的最高境界。也正因如此,他是一名嚴苛的道德自律者,在封建禮法制度所規范的位置,不敢越雷池半步。所以,對于自己的感情他模糊而無法自視。
玉嬌龍是生長在大漠邊陲,養在深閨的將門小姐,其性格既有大家閨秀的穩重端莊,又有將門之女的果敢潑辣。但在封建禮法森嚴的時代,任何女性都逃不了被擺弄的命運。因此,她無比地向往小說中所描繪的無拘無束、傳奇驚險的江湖,并希望以此來逃避現實中被掌控的命運。既然要闖江湖,自然離不了上好的兵器,而青冥劍此時的出現,正好滿足了她“仗劍走江湖”的愿望,于是,“盜劍”順理成章地發生。在玉嬌龍看來,江湖是一個隨心所欲、恣意妄為、快意恩仇的地方。“盜劍”及“闖蕩江湖”的這些舉動,體現了玉嬌龍對自由的生命狀態的極度向往。對于愛情,玉嬌龍有自己明確的認識,她渴望自由美好的愛情,厭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憎惡婚姻成為父親進階的手段。
因此,“獻劍”與“盜劍”使清靜無為、恪守禮法的李慕白與恣意妄為、隨心所欲的玉嬌龍碰撞在一起,讓觀眾看見了兩種不同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引起了人們深深的思考。
(二)展現人物自身的矛盾沖突
《臥虎藏龍》在某種程度上又可以看成是思考人生的影片,而這種對自我、對人生的思考在影片中主要通過人物自身的矛盾沖突來體現。
在感情與理智之間矛盾的李慕白,是一位武藝精深、修為深厚之人。作為武當派的高足,除了謹遵師父的教誨外,更是時刻銘記整個封建禮法制度規范。雖然他與俞秀蓮相識多年,但在封建禮法的束縛下始終不敢向她表明心跡,并深深地壓抑著自己的情感。在感情與理智面前,他摒棄感情,閉關修煉,希望能達到“道”的最高境界。可是感情的火花一經擦出,是很難熄滅的。在修煉的過程中,他開始困惑了,“我并沒有得道的喜悅,相反的,卻被一種寂滅的悲哀環繞,這悲哀超過了我能承受的極限……有些事需要想想……一些心里放不下的事。”感情已在李慕白的心里死灰復燃。隨著寶劍被盜,在尋劍過程中偶遇玉嬌龍,青春年少、任意妄為、率性執拗的玉嬌龍以及玉嬌龍的感情故事,更是強烈地沖擊著他的內心,喚醒他直視自己的情感。經過長期的自我矛盾,李慕白終于承認了自己的感情,“我也阻止不了我的欲望,我想跟你在一起……生命已經到了盡頭……我只有一息尚存……我已經浪費了這一生!我要用這口氣對你說——我一直深愛著你!”
在“本我”與“超我”之間矛盾的玉嬌龍,就像一塊未經打磨的玉石,棱角分明、個性十足,體現著人生命最原初、本真的狀態。所謂的“制度”“規范”在她心里沒有留下半絲痕跡,她愛憎分明、率性而為,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對于怎樣去追求這種自由,她并不明了,因此也常常陷入自我矛盾之中。在她的想象中,“江湖”就是一個隨心所欲的所在,而“闖蕩江湖”就是對現實境遇的逃避與反抗,她以這種恣意妄為、不加約束的“本我”闖進了復雜、兇險、多變的江湖,非但沒有得到她期望的自由,反而讓她陷入了另一個更大的、完全無法控制的江湖漩渦之中。此時她更為矛盾了,究竟怎樣才能達到生命的自由狀態?李慕白惜才,一心想要調教她,教她為人處世的道理,要求她潛心修煉武德,這些其實都是以規范、條約來約束玉嬌龍,希望其能從“本我”轉變成“超我”。當李慕白為救玉嬌龍而死時,她終于明白了,人生除了自由、隨心所欲,還有必須遵守的規矩、信義。
三、敘事動力深化主題內涵
主題是由一系列的人物和情節來展現的,敘事動力的產生除了控制著情節的發展變化外,還豐富了主題的深層內蘊。在《臥虎藏龍》中,表面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與“劍”有關的故事,但是細究其深意,會發現文本所表達的內容遠不止我們所見到的。
(一)“劍”的象征意義
影片始終圍繞著“青冥劍”來敘事,“劍”的出現,吸引著眾多居心叵測之徒的目光,不僅大批的江湖人士希望得到它,就連大家閨秀玉嬌龍也對它下了手。正如李慕白所說:“江湖里臥虎藏龍,人心里何嘗不是?刀劍里藏兇,人情里何嘗不是?”在此,“劍”不單單是指實物,更成為世間人心的一種折射,成為人性中欲望的代名詞。江湖人士覬覦它,是對權勢欲的追逐;玉嬌龍竊取它,是其自由欲的體現;李慕白視“劍”為“虛名”而放棄它,是對內心欲望的壓制。因此,在這些形形色色的人身上,充斥著名目眾多的欲望,自然也就演繹出一個“臥虎藏龍”的江湖。
(二)影片的深層意蘊
通過與“劍”相關的系列矛盾的展現,以及對李慕白與玉嬌龍這兩個耐人尋味的
人物形象的塑造,影片已具有超出一般武俠片的深意,其主題是開放而多元的。正如前面所分析,“劍”成為欲望的象征,那么對待“劍”的態度也就意味著人們的價值取舍。李慕白長期以來壓制著內心的愛欲,尋求得道的最高境界——虛空,然而在孤寂的修煉過程中,他不但沒有得道的喜悅,相反只有寂滅的悲哀,內心深處的欲望開始復蘇萌動,到底人生的真諦是“克己復禮”追求這縹緲無形的虛無?還是應聽從內心的召喚率性而為?他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玉嬌龍恰好是李慕白的另一面——率性真實、任意而為,對自由的渴望使她蔑視任何規矩約束,為了反抗現實的束縛,她沖出豪門以自己的方式闖蕩江湖。然而結果并不如她所愿,自由離她越來越遠。到底是該隨心所欲,還是要接受規矩的制約?她也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影片并沒有解決這些矛盾,也沒有明確的答案,片中李安采取了折中主義,讓壓抑已久的李慕白在彌留之際終于聽從了內心的召喚,向俞秀蓮表明了愛意。心高氣傲的玉嬌龍在李慕白舍身救己后,以跳崖的方式接受了信義、規矩,完成了“本我”向“超我”的轉變。誰對誰錯,影片并不做評判,而是讓觀眾去思考,因此才讓主題有了多元的解讀,如“理智與情感”“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等,因而影片顯示出深刻的人文意蘊。
[參考文獻]
[1]葉永勝.電影:理論與鑒賞[M].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8:98.
[2]郭明玉.論敘事動力的流程和類型[D].南昌:江西師范大學,2008.
[3]王純菲.談史詩《江格爾》的敘事動力[J].民間文學論壇,1997(02).
[4]黃昌林.敘事結構的語言學模式[J].成都大學學報,20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