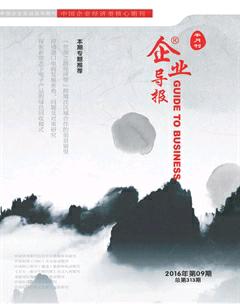評析張學英訴蔣倫芳遺產繼承案
李雅迪++李明
摘 要:張學英訴蔣倫芳遺產繼承案一審二審判決結果已經塵埃落定。或許說,法院的判決暫時解決了一個糾紛。然而,一審判決在學界引發的爭議,卻使有關民法基本原則的討論再度熱烈起來。其爭議的焦點是:基本原則在民法的適用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其能否排除具體法律條文而直接適用于具體的民事案件。
關鍵詞:公平正義;婚姻;繼承
民法的基本原則最基本的價值理念,就是實現公平正義。然而,正義的含義從來就是抽象和不確定的,不同的社會、不同的利益集團在不同的時期有著不同的理解。由于利益的復雜性和利益主體的多元性,在一個大的集體里,要實現正義,這種深蘊的價值理念就只能是要法律最大限度地滿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不合理的法院判決總也能滿足一部分人的利益,即在個案上迎合了他們對公平、正義的期許。但,這樣做的直接惡果是:法的安定性遭到了極大的破壞。
法律在人們心中卻從此變得模糊起來,因為對大多數的普通民眾來說,他們對法律的理解,不可能做到像法官、律師等職業人員那樣,從復雜理論的高度去看問題。讓他們學習具體的法律條文,掌握基本的法律常識,才是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走向法治的有效途徑。
在本案中,實際上有兩種不同的法律關系:遺贈法律關系和侵害配偶權的法律關系。前者為《繼承法》規制的內容,也就是當事人在法庭中爭執不下的東西。而后者傳統屬《婚姻法》管轄的范疇。當然,有關配偶權為抽象的人身權,則只能從《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四條中尋找依據了。[1]
我國《繼承法》規定得十分明確具體:第三條規定,“遺產是公民死亡時遺留的個人合法財產。”第五條規定,“繼承開始后,按照法定繼承辦理;有遺囑的,按照遺囑繼承或者遺贈辦理;有遺贈扶養協議的,按照協議辦理。”第十六條規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規定立遺囑處分個人財產,并可以指定遺囑執行人。……公民可以立遺囑將個人財產贈給國家、集體或者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問題的關鍵在第二種法律關系上。與第一種法律關系不同的是,張學英此時變成了受譴責對象。不論張學英對黃永彬的愛是建立在一種什么樣的基礎上,也不管她對他有多少的愛憐和照料,他們的同居行為是有違社會主義公德的,也和《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抵觸。既發生抵觸,依很自然理解,那她就得低下頭來接受大家對她的責難,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令人遺憾的是,在如何承擔法律責任的問題上,1980年的《婚姻法》并沒有作出相應的規制,修訂后的《婚姻法》雖說在第四條確立了“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的義務,但也不至于說要剝奪不忠者的財產權,頂多也只是在離婚時無過錯方有權向對方請求損害賠償而已。既然是這樣,人們的期許變成了失望,一個應受懲處的人竟還可以從一個受同情的人那里獲取利益!這也就是人們為什么堵在法院門口,以渲瀉其不滿與憤懣的原因。法官也認為,“如果我們按照《繼承法》的規定,支持了原告張學英的訴訟主張,那么也就滋長了‘第三者、‘包二奶等不良社會風氣,而違背了法律要體現公平、公正的精神。”從而作出了如此判決。
首先,此判決有悖于繼承法的基本原理。試想,本案中的黃永彬將受遺贈人換成另外一個人,那還會有什么爭執發生嗎?或許那樣,大家也就覺得沒什么討論的必要了。而本案之所以釀成糾紛,原因只有一個:黃永彬和張學英此前的不道德行為。那在《繼承法》中,對受遺贈人的道德水準是否有強制性的規定?是否受遺贈人道德水準的低下就可以排除其依法所享有的繼承權? 其次,在物權法上,這個判決也遇到了難題。繼承權為財產權,這是法學界通說。而這種財產權利乃是建立在所有權基礎之上的,為所有人對其財產處分的一種當然結果,體現了所有權神圣。我們的《民法通則》第七十一條也規定了“財產所有權是指所有人依法對自己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在本案中,如果不能實現遺囑的內容,那所有人(黃永彬)享有的具排它性的處分權又體現在什么地方?這樣,社會上還有誰會去殫心積慮創造、積累財富?那社會還談何發展?再次,以利益衡量論,本案判決實際上剝奪了一個“二奶” 的財產權,表明了對不良社會風氣不妥協的態度,這是其有積極意義的方面。但其本身并不能起到抑止“第三者”、“包二奶”現象的作用,作奸犯科者完全可以通過生前贈與來達到其目的。然而,由本案判決而引發的公眾對公權的畏懼以及對法律的迷茫和不信任,卻將使中國的法治之路蒙上陰影。從社會整體利益來考慮,得失孰大孰小盡在不言中。
中國要實現法治注定充滿艱難,它前行的路上還有很多的曲折,《民法通則》所倡揚的“保護合法的民事權益”要為社會普遍遵從,還須我們實實在在去努力。但往往真理也就是從如此種種爭議中開始的。
參考文獻:
[1] 第一百零四條規定,“婚姻、家庭、老人、母親和兒童受法律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