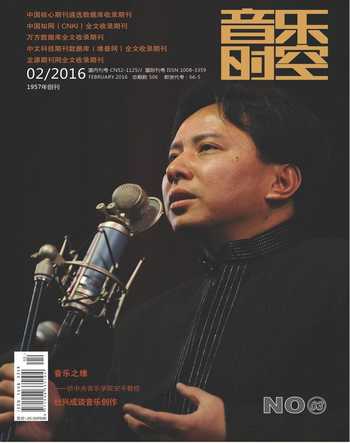探徵簫的演奏形式變革
孟曉潔
摘要:簫作為我國(guó)古老的吹奏樂(lè)器之一,從古至今都是以獨(dú)奏與合奏的形式演奏,其表演模式的單一化及曲目量匱乏等問(wèn)題一直存在。我國(guó)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音樂(lè)文化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發(fā)展趨勢(shì),從早期單一的表演形式逐漸開(kāi)拓到近現(xiàn)代的多聲部重奏、電子音樂(lè)與多元化融合的演變,使得簫在演奏形式上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使其與中國(guó)傳統(tǒng)民族音樂(lè)以新的形式走向世界。筆者將通過(guò)時(shí)間軸將本文分為五個(gè)部分:獨(dú)奏、琴簫合奏、簫與電子音樂(lè)、多聲部簫重奏與多種形式的融合來(lái)切入分析簫演奏形式的重要變革,并以《鬲奚梅令》與《簫魂》兩首作品為例,介紹現(xiàn)代簫演奏形式的音樂(lè)文化內(nèi)容與變革。
關(guān)鍵詞:簫 演奏形式 變革
一、一支簫的獨(dú)白
簫是一種非常古老的中國(guó)古代吹奏樂(lè)器,它的產(chǎn)生,其歷史可以追根溯源到遠(yuǎn)古時(shí)期的骨哨。在河南舞陽(yáng)縣賈湖村東新石器時(shí)代早期遺址中發(fā)掘出十六支豎吹骨笛,據(jù)測(cè)定至今已有八千余年的歷史。相傳在唐宋時(shí)期,單管簫出自于羌中,四孔,豎吹,漢代也稱(chēng)“羌笛”,后經(jīng)京房加一孔,為五孔。魏晉時(shí)期,西晉樂(lè)工列和中書(shū)監(jiān)荀勖所改革的笛為六孔(前5后1)其形制與今天的簫已非常相似了。唐代出現(xiàn)了前面六孔、旁邊一孔,加有竹膜的笛子,此時(shí)笛簫概念基本分開(kāi),橫吹為笛,豎吹為簫。故在此前的簫和笛常被后人所混淆,為了區(qū)別二者,樂(lè)家常稱(chēng)今天的簫為“笛”,排簫為“古簫”,宋·朱熹《朱子語(yǔ)類(lèi)·樂(lè)》:“今之簫管,乃是古之笛,云簫方是古之簫,云簫者,排簫也。”直至宋元以后才逐漸把排簫、洞簫、橫笛三者較明確地區(qū)分開(kāi)來(lái)。如清代以前的簫多指排簫,漢代的陶俑和嘉峪關(guān)魏晉墓室碑畫(huà)上,已可見(jiàn)吹洞簫的形象。至清代后,簫的形制完全一樣。
簫在中國(guó)古典音樂(lè)的演奏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在魏晉時(shí)期已用于獨(dú)奏與合奏,并在伴奏相和歌的樂(lè)隊(duì)中使用。從蘇軾的《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余音裊裊,不絕如縷。”或黃景仁的《綺懷》“幾回花下坐吹簫,銀漢紅墻入望遙。”等詩(shī)句中可以看出,簫早期是多在文人手中以抒發(fā)個(gè)人情懷為主的樂(lè)器。簫的音色圓潤(rùn)輕柔,幽靜典雅,它清麗孤傲、深邃沉郁的特點(diǎn)使得大量文人對(duì)其青睞不已。在當(dāng)時(shí),獨(dú)奏與室內(nèi)樂(lè)合奏是簫最早的演奏形式。
(一)“簫來(lái)天霜,琴聲海波”
琴簫是簫的一種,它的直徑略小與洞簫。由于它的音量較小,在音樂(lè)的表現(xiàn)上比較典雅幽靜。古琴是漢族傳統(tǒng)的撥弦樂(lè)器,琴簫合奏自古以來(lái)就被認(rèn)為是絕配,古琴與簫的結(jié)合,有著在藝術(shù)表達(dá)上令人回味悠長(zhǎng)、婉轉(zhuǎn)惆悵的特點(diǎn)。如“歘如環(huán)轡玲瓏搖佩旌,鏗如鳴球拍琴九奏簫韶聲”,“琴簫合鳴起鳳鸞,月宮嫦娥寂寞寒”等詩(shī)句,都把古琴與簫相提并論。千百年來(lái),中國(guó)音樂(lè)史上形成了一個(gè)經(jīng)典的表演形式,古琴渾厚、莊嚴(yán)、低沉的音色與柔美、纖細(xì)、悠長(zhǎng)的簫聲融為一體,呈現(xiàn)出極其典雅的東方色彩與氣韻。因此琴簫合奏的演奏形式自然而然的成為中國(guó)古典音樂(lè)文化的代表之一。如著名的古典樂(lè)曲《漁樵問(wèn)答》《梅花三弄》《平沙落雁》等,琴簫合作的默契程度已然達(dá)到天衣無(wú)縫的效果。
(二)簫與電子音樂(lè)的碰撞
20世紀(jì)初,有著“圣手簫王”之稱(chēng)的著名笛簫演奏家張維良先生,他是位集創(chuàng)作與演奏于一身、極具個(gè)人魅力的音樂(lè)家,在1992年推出了第一張簫與電子音樂(lè)的專(zhuān)輯《天幻簫音》,在音樂(lè)界引起空前影響。極具東方神秘色彩的簫音在極具魔力的MIDI等多復(fù)合音色的襯托下,讓其細(xì)而悠長(zhǎng)的音色和音樂(lè)氛圍烘托出悠遠(yuǎn)蒼涼之感,使其結(jié)合的渾然天成,令人贊嘆。音樂(lè)家們?cè)诒A粼械慕?jīng)典民間傳統(tǒng)曲目及演出形式的同時(shí),也在探索更多的可能性。而電子音樂(lè)追求的正是以人性博愛(ài)的精神與世界大同的觀念為出發(fā)點(diǎn),從而消除社會(huì)中的隔閡與冷漠,這也正與中國(guó)儒家及道家的思想不謀而合。電子音樂(lè)的出現(xiàn)也是中國(guó)民族音樂(lè)走向世界的試金石,同時(shí),簫與電子音樂(lè)的碰撞,讓簫的演奏形式與作品更加多元化,使其既不失東方音樂(lè)的色彩又為簫打開(kāi)了一扇新的探索之門(mén)。
電子音樂(lè)與簫的碰撞,完全突破了傳統(tǒng)音樂(lè)語(yǔ)言及表演形式的束縛,極大程度上的豐富了音樂(lè)表現(xiàn)力及想象空間。在給予聽(tīng)眾無(wú)與倫比的聽(tīng)覺(jué)感受的同時(shí),也呈現(xiàn)出作曲家的所思所想,從一定意義上來(lái)講,它們的組合讓人們重新的構(gòu)建了一種聽(tīng)覺(jué)美學(xué),電子音樂(lè)與簫的交融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并完善了中國(guó)傳統(tǒng)民族樂(lè)器簫演奏形式的單一化及曲目量匱乏等問(wèn)題,在保留傳統(tǒng)的前提下,創(chuàng)造更多的發(fā)展可能性。
(三)《鬲奚梅令》--簫的對(duì)話
從獨(dú)奏到琴簫合奏再到與電子音樂(lè)的交融,簫的演奏形式在不斷的被后人拓展、變革。中國(guó)的傳統(tǒng)音樂(lè)文化講究“中和之美”,“中和之美”是為相濟(jì),即演奏者將各種不同的要求,甚至是對(duì)立的音樂(lè)現(xiàn)象及情緒進(jìn)行相對(duì)的協(xié)調(diào),達(dá)到主客一致,而其美學(xué)觀點(diǎn)與簫的特質(zhì)不謀而合。西方現(xiàn)代音樂(lè)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手段和可能性,但最終我們要表現(xiàn)屬于中國(guó)傳統(tǒng)民族音樂(lè)的內(nèi)容,儒道文化就是我們的根源。簫的多重奏表演形式是極具東方文化思維理念的,其演奏形式并非為了走向國(guó)際而在形式上模仿西方的,而是要以人性的角度出發(fā),從而引起人類(lèi)共鳴的音樂(lè)。
眾所周知,簫的音色擁有圓潤(rùn)、柔美、穩(wěn)重、含蓄等特性,使其具有極強(qiáng)的融合性,這是其他的民族樂(lè)器所不具備的特性,從而簫的多聲部重奏形式便是從中脫胎而來(lái)。我們以張維良先生再度創(chuàng)作的簫四重奏《鬲溪梅令》為例,此曲根據(jù)古代宮廷的演奏形式為設(shè),力求展現(xiàn)古代風(fēng)采。在張維良先生的筆下四支簫在唯美的旋律及和聲織體下,此起彼伏、相互交錯(cuò),如同四位年長(zhǎng)的老人,在相互訴說(shuō)著以往的故事那般,娓娓道來(lái)。簫的多重奏表演形式無(wú)疑是成功的,2014年在英國(guó)伊麗莎白女皇音樂(lè)廳引起國(guó)際上的巨大反響。
(四)《簫魂》——多元化演奏形式的融合
《簫魂》是張維良先生在2015年為中國(guó)竹笛樂(lè)團(tuán)所創(chuàng)作,簫與多元化的形式相互交融,在簫多重奏的表演形式下又增添了童聲合唱,這在簫的歷史演奏形式上來(lái)說(shuō),有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張教授曾說(shuō)道:“要追求音樂(lè)創(chuàng)作本身,去探索出前所未有的聲音與搭配!這次,把古老的笛簫與天籟般的童聲合唱結(jié)合在一起就是我們嘗試之一。”確實(shí),這樣的組合使人感受到一種無(wú)以言喻的“天地神韻,和樂(lè)齊鳴”之美!并且在其基礎(chǔ)上再加入舞美、燈光、道具、服裝、人作為“陳設(shè)背景”,把表演藝術(shù)視覺(jué)意境化,場(chǎng)景藝術(shù)化使得與觀者一體化,在視覺(jué)與聽(tīng)覺(jué)上給予精神上的雙重刺激,淋漓盡致的呈現(xiàn)出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的當(dāng)代情懷。
多元化的音樂(lè)形式自誕生起就展現(xiàn)了復(fù)雜多樣的特點(diǎn),但其本質(zhì)上還是以傳統(tǒng)民族音樂(lè)文化為基礎(chǔ),應(yīng)當(dāng)取其精髓,去其糟粕。在突出其個(gè)性的民族性下,加以多種手段填充,讓演奏不在局限于獨(dú)奏和多重奏等形式,并進(jìn)一步的拓寬發(fā)展。東方的音樂(lè)文化在中國(guó)整個(gè)歷史長(zhǎng)河中都以儒雅、中和、意境為根源,而《簫魂》的多元化演奏形式,在保留傳統(tǒng)民族音樂(lè)精華的前提下,擯棄了其老套與陳舊的樂(lè)曲及表演形式,使其更加吸引當(dāng)代年輕人的審美情趣。
二、結(jié)語(yǔ)
中國(guó)的傳統(tǒng)音樂(lè)文化需要一個(gè)緊密考究的審美價(jià)值觀標(biāo)準(zhǔn),而學(xué)習(xí)西方音樂(lè)文化對(duì)事物的精準(zhǔn)及思維方式是必經(jīng)之路。可以說(shuō)簫的演奏形式是在近20年才開(kāi)始逐步變革的,從古時(shí)的獨(dú)奏到琴簫合奏這種表演形式一直持續(xù)至今才有了新的變化。70年代末,電子音樂(lè)的出現(xiàn)給音樂(lè)家們提供了更廣闊的創(chuàng)作空間,其豐富多樣的音色增加了更多的表達(dá)手段,極大程度的滿足了作曲家的想象力。電子音樂(lè)與簫的交融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并完善了中國(guó)傳統(tǒng)民族樂(lè)器演奏形式的單一化及曲目量的匱乏等問(wèn)題,為簫的演奏形式與中國(guó)傳統(tǒng)與發(fā)展打開(kāi)了新的一扇窗。20世紀(jì),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文化在流行音樂(lè)大浪潮的鞭策下,也開(kāi)始翻天覆地的變革歷程,無(wú)論是作品的數(shù)量還是風(fēng)格理念,或者演奏形式都在音樂(lè)文化的多元化影響下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簫魂》的多元化形式讓簫的演奏形式變革達(dá)到鼎盛時(shí)期,把多樣化的元素揉為一體,使之交融和諧。這種形式的誕生,解決了中國(guó)音樂(lè)文化中民族性和世界性,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矛盾,使中國(guó)的傳統(tǒng)與民族文化通過(guò)音樂(lè)以新的形式與手段走向世界。我們應(yīng)當(dāng)去探索更多前所未有的聲音與搭配,并思考如何讓深厚的傳統(tǒng)更具有時(shí)代性,這正是我們當(dāng)下值得思考的問(wèn)題。西方音樂(lè)知識(shí)只是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手段和可能性,最終,我們要表現(xiàn)出屬于中國(guó)自己的音樂(lè)文化內(nèi)容,并且在演奏形式的變革中抓住簫本身的特點(diǎn),繼續(xù)發(fā)展其更大的可能性。簫演奏形式的變革,是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文化的必然趨勢(shì),是當(dāng)今社會(huì)的必然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