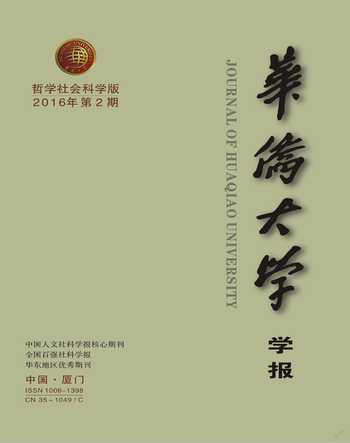“命定”視野下的“治道”:王充治道倫理論
龍倩
摘 要:為駁斥天人感應下的圣人史觀,王充提出了國家的治亂興衰由“國命”決定的思想。但這“國命論”并不是絕對的宿命論,也并未取消政治的積極意義。恰恰相反,在王充“命定”論的視野下掩蓋著系統的治道倫理觀。關于治道,王充不僅提出了包含國家的治亂及疆域的拓展,生產力水平的提升、百姓的安樂及道德素質的提高在內的“以民為本”的治道目標,也找到了“谷食”和“時數”的“自然主義色彩”的治道影響因素,并從國家治理主體及治理之道兩方面提出了“賢君良臣”和“尚德養力”的“人道有為”的治道實現路徑。
關鍵詞:王充;治道;國命;以民為本;人道有為
中圖分類號:B23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398(2016)02-0019-10
“政道”與“治道”是政治哲學領域中的兩個重要范疇,由現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提出。其中,“政道”主要是指社會國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理或法則,諸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道、理;而治道則是管理社會國家政治的基本方法或手段,即“治國平天下”具體方案或達成途徑。王充作為東漢初期一位時刻以“疾虛妄”為己任的特立獨行的社會批判家,對散布于東漢思想天空中的種種讖緯迷信進行了大范圍的抨擊與掃蕩,更是為了反對“天人感應”論下的英雄史觀或圣人史觀而提出了“國命”說。“國命”說,即是指國家的治亂盛衰由國命決定,而與他者無關。對此,許多學者常將王充誤解為一個絕對的宿命論者,認為他取消了政治的所有意義。但事實上,王充“國命”視野下蘊含著豐富而系統的“治道”思想。
一 “國命”論正名
國谷衍奎編:《漢字源流字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第356頁。,會意字,在甲骨文中寫為
從造字的角度來看,“國”中的大“囗” 指的是國境線,土地的疆域或邊界,將“或”緊圍其中,故又意指國家周邊應該設防進行保衛;而其中“戈”處于大“囗”與小“口”中間,它作為古代常用的兵器,暗含對外抵御強敵,對內維護治安之意;而小“口”則代表生活于一定疆域內的人口;“或”字下面的“一”則表示土地,它位于小“口”之下,大“囗”之內,則表示土地、農業是人口或國家賴以生存之基。而王充在提出“國命”的概念時,更多的是在“國”之本義的層面上使用的。他所指的“國家”,指的便是包括人口、領土、軍隊以及統治者的綜合體。因此,王充的“國命”論,便是指一個國家的治亂興衰、人民生活及道德水平的高低、統治者的賢良與否全部由“國命” 所決定。
當時漢儒的“天人感應”說極力宣揚“王權神授”,把君主說成是天命的體現者,認為災異與祥瑞的出現,在于應人君政教之得失,甚至國家的治亂與否全系于國君一個人的德行與意志之上。為了對其進行徹底的批判,王充提出了“國命”說,即認為國家的治亂決定于“命”。許多學者將“國命”說看成是王充思想中最為失誤之處,或以為“王充徹底的國命論果真成立,則賢君和德治以致一切政治必被取消,而且亦必徹底助長暴君和暴政,如是,則人世還有什么政治,教化可說?整個中只是犯濫著暴政而已!……所以這個國命論實在是最惡劣!最荒謬的!”陳拱:《王充思想評論》,臺北: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284頁。然而,這種看法卻有失偏頗。其錯誤之處首先在于誤解了“命”論在王充思想體系中的批判性質,其次在于對其思想不求甚解地應用,因此無法認識到“國命”背后所隱藏的發揮人的主體性的潛臺詞,也就無法承繼其豐富的治道思想。確實,如果不對“國命”論的立論宗旨及其提出的思想背景加以分析,的確容易將王充歸到絕對的宿命論者的陣營當中去。但事實上,在王充生活的時代,在思想界占據統治地位的社會歷史觀是“天人感應”論影響下的圣人史觀或英雄史觀。這種歷史觀極力宣揚“王權神授”,認為“天不變,道亦不變”并把君主說成是天命的體現者,認為其個人的意志、德行及其行動可以決定整個社會歷史的進程。正如王充在《治期篇》中所寫實道,“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不然。”
針對此種如此謬誤卻大肆盛行的歷史觀,王充秉持著“疾虛妄”的精神對此展開了猛烈的批判。他指出,國家的興亡、王朝的昌盛有著一定的規律,“興昌非德所能成,然則衰廢非德所能敗也”(《治期篇》)。國家的興旺昌盛并非由君主品德的優良所決定,同理,國家的衰微廢敗亦非君主的德行敗壞所導致。顯然,王充在這里旗幟鮮明地反對了統治者的個人道德品行的優劣與“天”交相呼應,并進而決定整個國家的治亂興衰的觀點。但是,由于時代的局限性,王充將自己所認識到的模糊的“規律”解釋為“國命”。也就是說,為了反對圣人史觀,王充才提出了“國命”論,認為國家的治亂興衰等一切均由“命”所決定,是上天注定了的。換言之,“國命”論是王充用以反對或批判圣人史觀的一種思想武器,它更多的是在工具而非目的的意義上被使用。更為重要的是,“興昌非德所能成,然則衰廢非德所能敗也”中的兩處“德”并非泛指德行、人的作為或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而是特指統治者的道德品行。因此,王充主要是為了強調國家的昌盛與否與統治者個人的德行無關,而非抹殺“德”或個人的作為在社會治亂當中的作用。對此,他在《異虛篇》中提出的“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于政之得失”思想便是另一個證明。國家的存亡與否,在于“期”的長短,而非政治的得失。這里的“政”與前文中的“德”一樣,均不能從一般意義來解讀,它們都是特指與統治者相關的政治舉措及道德品行。因此,“國命”論的提出,僅是對圣人決定歷史觀的一種駁斥,并沒有否定人的作為,更不會取消政治的意義。故而從這一視野下去挖掘王充的治道思想的路徑是可行的。
二 “以民為本”的治道目標
自董仲舒采用類比的方式對《公羊春秋》進行發揮與重釋,將天人感應思想系統化為一種神秘主義學說后。“天人感應”論雖然適應了漢代政治一體化的需要,但董仲舒在發展天人感應學說時所采用的宗教神秘主義的方式,發展到后期逐漸與讖緯迷信相結合,導致了封建迷信的泛濫,成為了一股反理性的思潮。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唯心主義的圣人史觀不斷得到強化,“原來兩漢政治,在深受陰陽思想影響的儒者鼓吹之下,人人醉心符瑞;以為自命不凡既至,就可坐致太平,國富民安了。于是施政得失,一以自命不凡之有無為斷。”陳叔良:《王充思想體系(一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98頁。
針對這種本末倒置的錯誤觀念,王充首先擺正了政治的目標與方向,以糾正當世之失。他首先告誡統治者及當局迷者,“夫治人,以人為主。”(《宣漢篇》)以治理一個國家而論,“人”或百姓是其中最主要應考慮的因素。與《尚書·泰誓》中“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之語相似,王充對“人”的強調也顯示出極強的人文主義色彩。而后他在《宣漢篇》中將政治的正確目標具體化,“夫太平以治定為效,百姓以安樂為符。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正如孟子所言,“民為邦本”。具體來講,百姓的安樂便是檢驗太平盛世的標準,也是“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非韓篇》)的政治目的。因此,“圣王治世,期于平安,不須符瑞。”(《宣漢篇》)換言之,政績的優劣,國家的興衰治亂,全在于人民安樂的程度如何。只要人民安樂,國家便會太平,自是不需要各種符瑞的出現來以示繁榮的象征。
具體來講,“以人為本”的治道倫理目標又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從滿足個人的基本生存狀況來講,體現在居住于其中的百姓能保“平安”上。“平安”,是相對于人的生命得不到保證的戰爭年代而提出的,在王充看來,“百姓平安,是國昌也。”(《治期篇》)其二,從經濟基礎的角度來看,則體現在人民的生活水平上。王充曾提出“家安人樂,富饒財用足”(《治期篇》)及“太平以治定為效,百姓以安樂為符”(《宣漢篇》)的思想。即是說,天下能否太平是以社會是否安定作為檢驗標準,而社會安定與否則取決于百姓能否安家樂業。百姓能否安家樂業,又取決于家庭是否富饒,財物費用是否豐富、充足。若人人“家有十年之蓄”,則民定可安樂,而國亦將太平久治。其三,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則體現在選賢任能上。王充指出,扭曲的用人標準,使得“處尊居顯,未必賢”“位卑在下,未必愚”的“德不配位”的現象盛行于社會。這種德才兼備者被長期埋沒在下,而奸佞小人則靠家世、奸詐等不正當手段而身居要職的混亂現象顯示出當時政治的腐敗。這種腐敗又必將導致國家衰亂。綜上,不論是“平安”“富足”還是“選賢任能”,無非是為了促進國家的長治久安及繁榮昌盛,也無不體現了王充將“民”(或“人”)作為立論起點的人文主義致思方式。
然而,王充雖提出以百姓的安樂作為政治倫理的總目標,但卻并不僅僅將目光聚焦在物質財富的滿足上。除了“平安”“富足”以及“選賢任能”外,王充也對“民”提出了道德上的要求。換言之,生活于王充理想治道之世中的百姓,并不是拋棄禮義、“民逆犯上”的殘暴粗魯之民。恰恰相反,王充所期望實現的是一個“禮豐義重”“人有君子之行”的社會狀態。便是“父慈子孝”,人各盡其本分。同時,“民”又是生活于一定疆域內的人,即是國家中一定數量的人口。因此,“以民為本”的政治倫理目標必然與國家整體的治亂興衰有著緊密聯系。這種緊密聯系又可從王充的歷史發展觀中管窺一二:
古之戎狄,今為中國;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商舄。以盤石為沃田,以桀暴為良民,夷坎坷為平均,化不賓為齊民,非太平而何?(《宣漢篇》)
上世之民,飲毛茹血,無五谷之食,后世穿地為井,耕土種谷,飲井食粟,有水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后世易以宮室,有布帛之飾。(《齊世篇》)
在社會歷史領域,王充堅持歷史發展論,否定是古非今論者所持的上世之人講究禮義道德而今世之人背信棄信的今不如古的觀點,并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 了論證:首先,從疆域方面講,曾經的邊遠民族被納入中原的諸侯國。其次,小至生活細節上的穿衣戴帽,大至強悍不馴之人被化為良民,無不顯示著社會文明程度及道德水平的不斷提高。再次,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來看,荒地被開墾,沙地被改造,交通條件也得以改善。因此,他所描繪的疆域遼闊、道德狀況優良、文明及生產力發達的社會便是王充對治道之世的期許與向往。故而,“以民為本”的政治倫理目標并不是一個純粹而單一的概念——僅僅指向人民的安樂,恰恰相反,它亦將國家的治亂及疆域的拓展,生產力水平的提升、道德文明素質的提高等方面包含于內。
三 “自然主義色彩”的治道影響因素
如前所述,王充的以百姓的“安樂”為治道目標,而百姓的“安樂”又內在地蘊含了對百姓的道德要求。同時,百姓的“安樂”與否又受制于國家的治亂興衰以及生產力的提高與否。簡言之,治道目標中內在地包含了財富、道德及國家興亂三個因素。為提出有效的致治之方,王充對影響治道目標達成的因素進行了分析與挖掘,指出“谷食”與“時數”是影響治道目標的兩個重要的自然因素。
關于“谷食”。王充在《治期篇》中提出了“谷足食多,禮義心生”“禮義之行,在谷足也。”的思想。即是說,道德的教化依賴于一定的物質生活基礎,只有當滿足了基本的物質需要后,才會產生更高級的道德需要或要求。這也往往是許多學者用來論證王充的思想帶有歷史唯物主義色彩的最佳證據。
其具體論證過程如下:
夫世之所以為亂者,不以賊盜眾多,兵革并起,民棄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絕,不能忍饑寒。夫饑寒并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然則溫飽并至,而能不為善者希!(《治期篇》)
傳曰:“倉稟實而知禮節,節食足而知榮辱”。讓生于有余,爭起于不足。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如及四鄰。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鄰,善義也。為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于歲之饑穰。(《治期篇》)
王充提出治道目標以百姓安樂為準,而百姓的安樂又取決于能否豐衣足食。因此,在王充看來,“賊盜眾多”“兵革并起”“民棄禮義”“負畔其上”等現象是僅僅只是亂世的一種具體表現,而非其產生的真正根源。“谷食”才是國家治亂與否的真正根源,在國家政教得失、朝代更迭等方面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若一個國家糧食缺乏,那么生活于其中的居民便會饑寒交迫,連基本的溫飽都無法滿足。而溫飽是滿足一個人生存的基本生活條件,此項需求的被剝奪則必將導致不顧禮義,甚至胡作非為以致犯上作亂事件的發生。相反,若一個國家谷足食多,在衣食充足的情況下,人們便會自然有善行并且顧及禮義。正所謂,“谷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治期篇》)而囊括“道德風尚”“禮節榮辱”等在內的“禮義”又是國家立政的基礎。因此,就“谷食”與“禮義”兩者的關系來看,前者決定后者。而就國家治亂與“禮義”兩者的關系來看,則是后者決定前者。依此推論,“谷食”對于國家的興衰具有根本性的決定作用。王充的這一思想,不僅反映出他對現實的深刻洞察,也包含著極深厚的人道情意,不可不謂深刻。
而這一觀點也在對孔夫子的“去食存信”的批判之中得到更為具體的強調。王充先假設了一個糧食欠缺的國家,在這樣一個國家中,百姓饑不裹腹,并且拋棄了禮義,更是無從建立起“信”德。而后王充從理論與現實的角度對他的這一假設進行了證明。從理論層面的角度來看,王充搬出了管子的著名論斷,“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并指出富足之后才會產生謙讓等美德,而貧困或物質資源困乏則會導致爭端等行為的發生。如果說王充的前人,管子還只是朦朧地看到社會物質財富與社會治亂之間的必然關聯的話,那么王充便將這種物質財富具體化為人們賴以生存的“谷食”。并且,雖然管子最早看到“倉稟”與“禮節”之間的必然聯系,但管仲僅僅是從“牧民”的角度而提出,而最早將它與社會的治亂興衰聯系起來并把它看成是其根源的卻是王充。而另一方面,王充又舉出春秋時所發生的現實慘案來例證。他指出,春秋時期由于諸侯國混戰,導致戰火連天、餓殍遍野、民不聊生。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為了生存下去,甚至會發生“易子而食”“析骸而炊”這種史書上都羞于書寫且令人汗顏的惡行。在這種極端的生存條件下,甚至連所有倫理關系當中最根本的“父慈子孝”都無法保證,更遑論其他。也正在《非韓篇》中所強調的,“禮義在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為有益,禮義不如飲食。”顯然,從個體的生存角度來講,關于“飲食”與“禮義”孰輕孰重的問題,王充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
關于“時數”。既然“糧食”具有如此大的功效,那么要想政教成功、朝代永駐,最簡單的辦法便是保證糧食的充足。那為何又會出現糧食“乏絕”的情況呢?許多學者孫叔平便認為王充的“時數”片面把谷食乏絕歸因于自然,公然宣稱“非政所致”,是為商人、高利貸者、地主、貪官、污吏、暴君開脫了罪責!(引自孫叔平:《中國哲學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4頁。)認為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王充又倒退到天命論了。其依據便是王充認為,“案谷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時數也。”(《治期篇》)所謂的“時數”,即自然的力量,非有意志的“天”決定。因此,認為王充倒退到天命論,實則是對其思想的一種誤讀。而這一誤讀的根本原因便在于沒有理解王充的立文宗旨——即廓清天人感應之迷霧;直接原因便在于沒能正確理解“年歲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中的“政”義。所謂的“政”并非是宏觀層面的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而是具體指向君主的言行舉止等行為。如此一來,這句話的意思便可理解為,糧食是否充足,主要取決于年歲。而年歲是水是旱,五谷是收是歉,與統治者的德行并無任何關系,而是取決于自然的力量。換言之,統治者德行優良、奉行天意,并不必然會帶來“風調雨順”;而統治者倒行逆施、忤逆天意,也并非就導致“天降災禍”。統治者與年歲的好壞并不存在任何因果聯系,這便是王充極力要澄清的一個事實。而許多學者卻過分解讀之,并最終得出王充否定了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任何作用而走向宿命論的錯誤結論。殊不知王充為了證明神學思想下的英雄史觀的錯誤等問題,“從各個方面進行廣泛的論證,甚至不惜把自己認為是‘虛妄的一些說法都搬出來作為論據。關于這一點,許多論者不知道王充的苦衷,總以為他在打自己的嘴巴。”鐘肇鵬,周桂鈿:《桓譚王充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425頁。
事實上,王充在宇宙觀上堅持“天道自然無為”的觀點,認為天不過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物質實體,它沒有意志,并不能決定人世間的任何事務。將這種“天道自然”的觀點應用到社會歷史領域中,王充認為國家的興亡、王朝的衰亂完全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客觀過程,總是按照一昌、一衰、一興、一廢、一治、一亂的規律而發展,并不受“天”所干預,也不由圣人所決定。總體而言,王充對于天命史觀及圣人史觀是持否定態度的,認為國家治亂即國之“福”的獲得是自然而然的過程,無關乎“天”,也無關乎“圣人”。具體而言,王充認為,昌衰、興廢,皆天時也。(《治期篇》)
命期自然,非德化也。(《治期篇》)
故世治非賢圣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賢圣不能盛;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治期篇》)
治世或亂世,并非是由圣賢個人所能決定的,國家若是衰亂了,即使你是圣人也無法使其興盛;而若是治世,則即使昏庸至極之人也無法使其衰亂。所以國家的治與不治,并不在于施政者如何,并不在于教化,而是在于“數”。顯然,王充對圣賢與小人在影響國家治亂、王朝更替的作用上是持否定態度的。換言之,在王充看來,勢單力薄的個體無法造就一個盛世,也無法毀滅一個國家。真正賢明而杰出的政治家,只能順時勢而動,不能開歷史的倒車,治亂的循環決定于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或曰客觀必然性——“時數”。對于這一影響因素的強調,與漢儒們所認為的圣賢出而天下治,小人出而天下亂的觀念正相對立。
對于這一點,王充在《齊世篇》中也進行了說明,“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為,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在這里,王充再次駁斥諸如堯、舜禪讓而湯、武征誅之事決定于個人品德優劣的觀點。這種對所謂圣人或英雄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觀點的否定,不論從哪個層面來看都是科學、進步的。然而,“天命”二字又成了王充令人詬病與誤解的理由。蕭公權先生曾因此而指出,“荀子破除天人感應之迷信,意在建立一人本主義之積極政治觀。王充破除感應,其目的在宿命論。”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235頁。但這里的“天命”正如王充用來反對“隨命論”思維方式所使用的“命定論”概念一樣,也僅僅只是一種批判“天人感應”論下圣人史觀的思想武器。此外,若王充果真否定了人在社會歷史中的作用,那么便不會去積極地尋找治世之道,提出“夫圣賢之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能,失其術則事廢”(《定賢篇》)的思想。也更加不會專門為郡國守相、縣邑令長而撰寫《政務》一書以“陳通政事所當尚務”(《對作篇》),并且希望此書所陳意見被君主所采納。因此,與荀子一樣,王充破除天人感應之迷信,也是為了建立一種理性的、人本主義的積極的治道觀。
四 “人道有為”的治道實現路徑
由上文可知,王充雖然提出了“國命”論,而使其思想帶有宿命論的色彩,但他卻并未否定人的積極作為在達成治道目標中的作用。針對影響治道目標的“谷食”與“時數”兩個自然因素來看,王充從國家治理主體及治理之道兩個方面提出了賢君良臣與尚德善力的措施。
1.賢君良臣
如前所述,王充的“國命論”只是用來反對天人感應之下的英雄史觀的思想武器。因此,他所說的“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治期篇》)中的“人力”并非泛指人的主體性或作為,而僅指君主或圣王的德行,所反對的是符瑞所昭示下的圣王出而天下治的思想。就國家的昌盛、興亡與治亂而言,王充十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并且他所強調的“人”包括君主、臣子等不同的治道主體在內。對此,可從王充在《效力篇》中的一番言論可知。他說,“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強矣。”齊桓公能夠多次召集諸侯會盟來匡正天下,靠的是管仲的能力。然而,管仲有能力,而齊桓公又能夠對他予以重用,才共筑了春秋第一霸的偉業。以此來看,在一國的治興中,圣君與賢臣都是不可或缺的治理主體。只有二者攜手共進,才能造就治世的輝煌或國家的德福一致。正所謂“成事……有賢明之君,故有貞良之臣。”(《書虛篇》)“是故塠重,一人之跡不能蹈也;礚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非韓篇》)正如碓重無法靠一個人的腳來支撐,石磨無法靠一個人的手來推,國家的治理的重擔也不能僅系于最高統治者一人之身,而必須有賢君的幫助。只有當賢君有了賢臣的傾心輔助,國家政治才能走上正軌。然而,在王充看來,賢臣才能的發揮是有條件的,其依賴于君主的敏銳的洞察和公正的選拔。因此,賢君需要良臣的輔佐,國家才能大治,良臣須賢君的提拔,故可盡其材。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君主與臣子,兩者相輔相成、不可或缺。但由于時代的局限性,臣子的作用或功勞往往只有一并歸于“君主”才能保其身,否則便會出現“功高震主”的現象。因此,即使“良臣”在促使國家長治久安、政通人和的達成上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歷史史書上更被強調的也往往是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
所謂“賢君”,是指提升君主的才能,完善其德行,使其能夠完成身為統治者的份內之事。而“良臣”則既指臣子本身才能的提升,亦指君主能夠選取賢良之人。在王充看來,君主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最應該做到的便是“選賢任能”與“明時識數”。而要完成這應有之職責,首先應該對自身的才能與德行進行完善與提升,否則除了德不配位之外,還將給國家帶來災禍。王充指出,“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賢,不能知佞。”(《答佞篇》)“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效力篇》)伍子胥與屈原,俱為賢臣,且能力很強。但由于各自所賣命的均為“庸庸之君”,能小力弱,故而無法識別其賢佞與否。因而他們不但未被重用,還招致殺生、被黜之禍。然而,王充之意決非止于此。吳王夫差因不能用賢臣子胥,最后慘遭亡國自盡的下場。而楚懷王由于罷黜屈原,也終逃不出客死秦國之都之禍。吳國與楚國的慘淡下場,無一不在告誡世人,“力不任強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效力篇》)因此,王充認為,一國得治,首重賢君。而又只有自身具有能力強大、德行完美的賢明之君,才能知賢遠佞,使忠良賢臣位皆列于朝廷。唯如此,才可使教化大行,國家得治。
而在“明時識數”方面,王充認為君主作為重要的國家治理主體,必須要有所作為,在國家治亂中發揮一定的作用。然而,君主的作為,并非是指履行被世俗漢儒所神化了的各種不同的宗教迷信儀式,如祭祀、祈禱、雩祭等。這種“作為”在王充看來并非真正的“作為”,而不過是一種非理性的神學迷信,它并不能對國家的治亂帶來任何幫助。在王充看來,國家的興衰治亂在于人而非鬼,在于德政而非祭祀。“祭祀”所起的頂多是將君主“憂念百姓”的形象傳達開來,以利于爭取民心,但卻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對于君主的真正作為,王充在《順鼓篇》中進行了詳細的描繪。他以大禹治水為例指出,
堯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圣君知之,不禱于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醫也。《春秋》上記載,堯在位時曾遭大水。面對洪水之災,圣君堯所采取的措施是派大禹去治水,令其疏通了所有的河道,而非對神禱告,也非改變政治。王充認為,洪水之災猶如人之病也,有病需求醫,有水患則須進行治理。因此,王充十分推崇堯的“不禱于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的積極作為,并將其看成是造就堯舜之治的主要原因。從這個角度來看,在自然災害及社會禍亂面前,人并非無所作為,王充所說的“國命”亦非不可更改。這種對人的實踐的積極提倡與強調,大有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之風范。
由于“賢臣”亦是國家得治的關鍵因素,因此人才的選拔與程量也為王充所重視。他在《程材》《答佞》《知實》《謝短》《超奇》《定賢》等十余篇中專門談到了有關人才的問題。為明確人才的選拔標準,他首先對社會中的人才進行了才能高低的等級劃分。他分儒為四:儒生、通人、文人及鴻儒。其中,“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超奇篇》)就才性高低而論,儒生超過一般人,而通人又勝過儒生,文人超過通人,鴻儒又超過文人。因此,從前至后,才能等級依次遞增,而其中“超而又超”的“鴻儒”又最為王充所推崇。在明晰了不同層次的人才后,王充又提出了判斷人才的兩個標準:“才”與“德”。其中,“才”更多的是從知識力量的層面來講,正所謂“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效力篇》)即人有了知識,才會有力量。王充認為,“知學”及“力”是判斷人才的重要標準。而相似的“知識就是力量”的思想卻一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才為英國思想家培根所提出,足足比王充晚了一千五百年。因此,與其說王充是中國的培根,毋寧說培根是英國的王充。而“德”,即指是否具有一定的道德。就才與德論,王充顯然更為強調德的重要性。因此,道德標準在王充看來是選拔人才的首要標準。
2.尚德養力
“德”即道德教化或教育,“力”即指刑罰、軍隊或實力等,在中國倫理學史上,兩者是關于道德價值與力量價值的重要范疇。德力之辨始自先秦,貫穿于倫理學史的整個過程,它包含著道德和力量、王道和霸道、義與利等廣泛的思想內容。當二者并舉時,往往標志著實現某種價值目標的工具,也稱治道良方,而非標志價值目標本身。從德力的最早提倡者孔子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與“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論語·為政》引自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2頁。并重,到孟子雖提倡“王道”與“仁政”,但也認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引自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62頁。,再到荀子的“全其力,凝其德。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荀子·王制》),雖然在重要性的強調上各自有所側重,但無不把兩者看成是達至理想社會的治道良方。雖然王充受道家及漢初黃老之術思想的影響,在自然觀上堅持“天道自然無為”,并且主張“以不治治之”的“無心于為而物自化,無意于生而物自成。”的無為之道(《自然篇》)。然而,“王充雖標揭無為,表面上似乎一本黃老,實際上依然歸宗孔孟,還是儒家的底子。此點論及致治之方,就更加顯明了。”陳叔良:《王充思想體系(一冊)》,第198頁。
從王充對韓非的“明法尚功”治道之術批判來看,他所主張的致治之方亦是文武張設、德力并重。顯然,王充繼續了儒家的德治精神,主張以德治國、教化興民,持有一種積極入世的政治觀。他在《非韓篇》中指出: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且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
“養德”中的“德”既指宏觀層面的道德力量或德治,也特指一批具有很高道德聲望的儒生,以示對賢者的敬重。“養力”中的“力”既指宏觀層面的軍事力量,也特指士兵,以示國家軍事力量的強大。就戰事而言,既可以以“德”來感化對方,也可以靠武力來征服對方。因此,一個國家外可以靠修行德操來樹立自己的形象,內部又可以靠強大的武力來武裝自己。雖然“德”與“力”異質,但在保家衛國,促進社會繁榮發展上的作用卻是相同的。正如《周易·系辭下》所說,“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因此,此兩者各具功用、不可偏廢,均為王充所提倡。
具體來看,王充十分強調“德”的重要性,并將它上升到影響國之亡廢的高度上。在他看來,“德”雖然不能立即產生十分具體的實際效果,但它卻是“道”,是人們成就任何事都必須遵循依賴之物。正如他所說,“夫道無成效于人,成效者須道而成。”(《非韓篇》)而對于德治的具體內涵,王充則認為是以禮義為本。前文已指出,“禮義”乃國家立政之基,“民無禮義,傾國危主。”(《非韓篇》)然而,與傳統儒家不同的是,王充認為對“德”的片面推崇,將給國家帶來災禍。針對片面推崇“德”所可能導致的惡果,王充以徐偃王以例進行了說明。“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強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非韓篇》)在王充看來,徐偃王雖實行仁義,慕之者如流,但當具有強大軍事實力的楚國前來攻打時,卻毫無還擊之力以致亡國,最后招致“無力之禍”。因此,從徐偃王的教訓當中,王充得出了一個結論:“德不可獨任以治國。”(《非韓篇》)這一結論不可不謂深刻,它不僅體現了王充的辯證思維,也“給時俗之過高估計道德力量同警示危。”陳少峰:《中國倫理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95頁。若以歷史來證明,則明代在異民族滅漢的危機關頭,儒者仍耽于仁義治國,最終走向“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顏元·存學編》)的結局,不幸又言中矣。
如果說王充對“德”的提倡更多的是基于它在促使國家長治久安的積極意義,那么他對于“力”的提倡則更多的是從保衛國家的消極防御角度來說。因此,相比于“德”來說,王充對“力”的強調力度是較弱的。他雖然認識到了軍事實力在防御外來入侵以及征戰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卻更多的揭示了獨任“力”的缺陷及所可能帶來的惡果。王充對“力”的缺陷的揭露伴隨著對韓非治道的批判而展開得以說明。王充指出,韓非所謂的“法度”便是指擁有三軍士兵,賞罰明令,嚴刑峻法,富國強兵。若能達到此種“法度”,便在一定程度上足以為一個國家的穩固與發展提供必要的促進作用。退可守家,進可攻敵,這便是“養力”的積極意義之所在。然而,若如韓非般獨任刑,片面強調“力”,則最終也將給自己招致災禍。因為當同樣兩國的軍事力量進行較量時,終究會有力量的強弱、大小之分。在此情況下,小弱之國終將為強大之國所滅。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對“力”的獨斷推崇在促進國家長治久安的上所起的作用并沒有想像中的大。同時,王充也得出了“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非韓篇》)的教訓,并針對韓非之術不養德推測出其必將有“無德之患”。
因此,最正確的治道之方,應該是將“養德”與“養力”結合起來,如此才能達到以百姓的“安樂”為準的政治目標。大體而論,相對于“當世淺儒既迷于天人感應之說,又泥于耀德不觀兵之言”陳叔良:《王充思想體系(一冊)》,第203頁。的迂闊立論;法家的獨任刑罰以傷恩厚的苛薄之論。王充為實現治道目標既強調以德為本,以禮義教化百姓,又主張以“力”為輔,任刑法以防暴的“尚德養力”的治道之方可謂相當深刻。
綜上,王充雖然認為國家的興亂等由“國命”決定,并以此來反對天人感應下的圣人史觀,但他所持并非是一種將政治完全交由“命”而定的消極宿命論。王充指出,時數及谷食是影響治道目標達成的重要因素。其中,時數的變化能夠影響氣候,并影響到谷食的收歉,進而影響到禮義的生發,并最終影響到國家的治亂興衰。然而,王充卻并非機械的時數(或自然)決定論者。針對時數及谷食所可能起的正負作用,他從國家治理主體及治理之道兩方面提出了“賢君良臣”及“尚德養力”的積極促進措施。而不論是“賢君良臣”還是“尚德養力”,兩者的立足點亦是人或“人力”。質言之,生產力的發展、政治的清明、賢君良臣的積極作為及社會治理手段的完善本身不僅可以促進國家治道目標的達成,同時亦可有效減少時數的變化對旱澇、谷食、禮義乃至國家興衰的負面影響。換言之,如統治者采取積極的措施,在糧食豐收時積極儲存,在欠收時適時發放,則可從一定程度上減少時數對國家治亂的負面影響。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家治道目標能否實現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然力(時數)與“人力”兩方博弈的結果。若“人力”取勝,則“國命”可改。因此,雖云“國命”,但王充卻始終把社會歷史領域中的主動性交還于人自身,提出了“人道有為”的系統的治道觀,體現出強烈的理性主義及人文主義精神。
【責任編輯 陳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