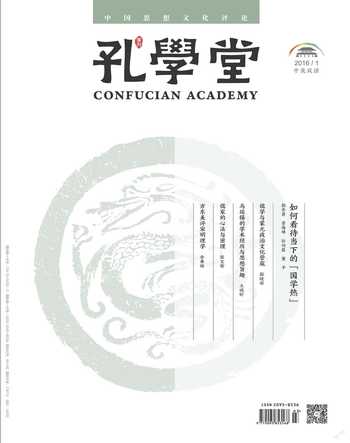正確引導“國學熱”
景海峰
一、何以關注“國學”
很多人會問,一國之學,中國謂之“國學”,比如說美國、日本、歐洲等國,是否也有他們的“國學”,這跟我們的“國學”有什么區別?這樣的疑問,會隨著研究的深入相伴而來。所以我要換一個角度,即從我們今天為什么要用“國學”這個概念或者以“國學”這個詞來代表當下的文化現象,表達大家的普遍關切,因為從政府到民間,從學界到商界,大家都對這個話題表現出興趣,道理何在?
我想從三個方面講:
第一,歷史大視野。1840年以后,中國長期處在落后、被動挨打的狀態,中國的近代史可以說是一部屈辱史,不斷地割地賠款,簽訂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大家在學校學的《中國近代史》,留下的印象差不多就是這樣。中國文化也同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和顛覆,尤其是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幾十年間。在整個世界民族或不同的文明區域中,中國處在一個非常弱勢的狀態,沒有足以代表自己民族優勢的文化,我們基本上是跟著西方的步履在走,很多價值觀念、文化理解都是在依從西方的模式。
隨著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的崛起,文化力量伸張的要求也提到了日程上,就是從上到下大家都有這種強烈的愿望,這種需求是整個民族、文化的內在驅力,不只是簡單的學問或者是某個理念。我覺得,不管用哪個詞匯,它都代表了這一時代變遷的需求,我們每個人都能感受到,姑且用“國學”這個概念來稱之。
第二,文化荒蕪感。從新文化運動之后,反傳統風潮興起,尤其是在革命的批判意識之下,傳統的很多東西都被打翻在地,甚至是踏上了千萬只腳。對最近幾代人來講,傳統逐漸遠離了我們。不僅是遠離我們的日常生活,也遠離我們的話語系統,遠離我們的價值觀念,處在一個陌生化或“間距”化的狀態,即我們對自己的歷史和民族文化已經非常的漠然,而且一講起來,可能腦子里留下的都是一些被妖魔化之后的印跡和概念。我們幾代人都有這樣的記憶。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急需為自己的民族文化正名,要給它平反。過去強加在中國傳統文化頭上的很多不當之詞,在這個新的時代要給它重新的解釋,需要補上傳統文化這一課,因為我們對這些東西已經疏離得太久了,很多東西都需要逐漸地熟悉。民間“國學熱”對中國傳統文化急于吸取的心情,是跟這種心靈貧瘠所造成的荒蕪感聯系在一起的,所以整個社會才有這么強勁的動力,大家都渴望讓過去不了解和已經疏遠的傳統再回到我們的面前。
第三,學科的整合。從學術研究的方式來講,一百多年來的格局也是全盤西化的,我們的研究方式、學科分割的理念,還有一系列做學問的方法都是按照西方的模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分科過于細密,尤其是像人文的這些知識,在今天的學科狀態下,基本上是被切得七零八落。中國傳統的學問和對知識的了解,不是這種模式。我們經常說文史哲不分家,但現在的狀況是嚴重分家,老死不相往來。從知識成長的需要來講,今天是所謂科際整合的時代,西方在二戰之后,科學和人文的整合己是人類進步的一種趨勢。從中國當代來講,尤其有這種深切的感受,即雞零狗碎的研究方式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我們要把人文學科整合起來,用宏觀的知識穿透視域,來解釋和應對我們今天遇到的很多問題。
從學科整合的意義來講,今天在大學或者學術界,不同學科之間需要有一個共有的平臺。所謂“國學”恰提供了這樣一個平臺,因為在這個旗幟下,不同學科、不同知識背景的人都可以來進行一些思想的碰撞、交流和對話,可以來思考共同的問題,這也包括了西方的學問,很多研究西方哲學的人對國學也很有興趣。所以從學科整合的要求來講,“國學”的出現恰恰給我們今天的學術界帶來了一個“熱”的可能性。
二、誰推動“國學熱”
我們姑且承認有所謂的“國學熱”。這個“熱”實際上是由三股力量推動的。
第一股力量來自民間。現代中國的組織動員方式及其程序,一般是由政府或者上面提出,發動運動或者是組織全民的活動,下面聞風而動、樹立典范再普遍推行,一般是自上而下,這是中國現代社會的文化或者其他活動的基本路徑。但是“國學熱”稍微有點怪,因為剛開始政府沒怎么提倡,也沒有什么人設計或提出方案來發動全民都來學國學。恰恰是逆向的,自下而上,民間的許多活動,爆發出驚人活力,倒逼著學界和政府管理部門,怎么來回答這些問題,怎么來應對這種局面,不管是引導或者規范,學界和政府的管理是跟進式的。這個國學“熱”,很大的動員能量是來自于民間,是從民間的活力里面蒸騰生發起來的。這是一種很重要的力量,但這個力量本身也存在很多問題。學界對這種局面有點擔心,認為前景堪憂,照此下去,這個國學不是我們期待的那個國學。
但我覺得對民間可能也要有一個分析,對學界而言,它賦有某種引導的責任。如果隨順著商業的做法而不去引導,這是學者的失職;但如果學者高高在上,那也不對。對民間的“國學熱”,學者要承擔一種引導的責任,因為學者對國學有一種通盤的理解,有比較真切的把握,應該發揮自身的力量去引導民間。
第二股力量來自學界。從改革開放以后,撥亂反正,學術復興,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從知識形態來重新思考,學界同仁這幾十年都在做這個工作,包括國學理論形態的建構,學界都在積極參與和推動。而且這個參與不是少數人,不是某一兩個專業,過去跟傳統有關的就是古典文獻、中國哲學、中國史等少數幾個學科,這些專業會涉及到。但我們今天觀察,學界參與的力度、廣度是很大的,很多學科的學者都有興趣,不光是做西方哲學的,還有很多搞經濟學、社會學,甚至是自然科學的學者,他們對國學推動的力度也是很大的。從學科專業來講,它是一個開放的狀態,不限于某種領域,而是從整個文化復興的態勢里面激蕩起來,這個力量就形成了國學能更好發展的動源。
第三股力量來自政府。過去我們高舉新文化運動的旗幟,要批判孔子,往往挑剔傳統的很多東西,甚至只要是傳統的,就要跟它劃清界限,這種決裂心態造成了整個社會對傳統的疏離和蔑視。我覺得在這二三十年中,國學的興起和各種活動,最大的功績就是把這種情緒給扭轉過來了。政府從主流意識形態來談中國傳統文化,也跟過去的認識、理解和姿態很不一樣了。這是很大的轉變,是對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正面肯定,這在過去二三十年前是很難想象的。國學要說熱的話,這是一種社會現實的形態,政治的力量與新文化運動的情結脫鉤了,和傳統的關系有了某種時代轉向,這一轉變在一二十年中悄無聲息的到來,已經預示著新時代的來臨。
從這三股力量來講,我覺得國學是很有活力的,三者可能各自扮演的角色不一樣,發力點不一樣, 但都可以來推動這個事業。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視角,在自己的領域里能找到相關問題,只要我們從 總體上把這些積極的力量匯集起來,就能夠共同推動國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