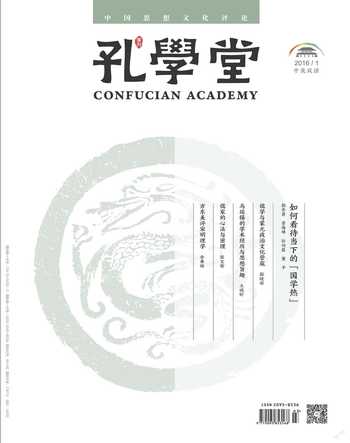試論儒學對中國古代繪畫理論的滲透
摘要:長期以來,人們認為儒家學說對于中國傳統繪畫,似乎沒有形成系統的批評或理論。然而,從基本理念、說教的角度,便不難發現其影響其實是深遠而巨大的。本文從“繪事后素…‘山水比德…‘以意逆志…‘胸中與眸子”及“陰陽和諧”等五個方面對此加以探究,其著眼點在于更為宏觀意義上的人與自然、人品與藝術創作之間的關系,以及中國傳統文化和哲學思想對于中國文人、畫家和中國畫性質、格局的深層次的滲透與影響。
關鍵詞:儒學中國畫天人合一山水比德陰陽和諧
作者林巍,暨南大學翻譯學院特聘教授、博士(廣東廣州519070)。
中國的繪畫藝術有著豐富的文化底蘊和深厚的哲學素養,對其研究不能僅限于藝術與美學的范疇,而須有廣闊的傳統文化視野。作為幾千年中國社會的統治思想,儒家思想對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當然也滲透到了繪畫藝術領域。鑒于此,近年來關于儒學對中國繪畫的影響有著多方面的研究,如儒學的教化功能、移情功能、言志功能、審美功能等。總的講,儒學對于中國傳統繪畫理論,雖沒有直接、具體的論述,卻有著深刻而根本性的影響和奠基作用,故本文在此基礎上,既借鑒他人成果,又另辟視角,深層探究。盡管繪畫與哲學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語言,但繪畫作品中卻不可能不涵有某種思想、意識,甚至哲學因素,因而不可忽視、低估在此方面對于繪畫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與此同時,在這一特殊領域的分析,又可不斷拓展、豐富我們對于儒學博大精深內涵和功能的理解。
一、繪事后素
就繪畫而言,《論語》中關于色彩、裝飾等的論述并不多,但仍可見:“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矣”。在中國古代,對于不同等級中的不同人的衣裝服飾的印染有著嚴格的規定。例如,君子不以深紅色或灰色鑲邊,不以淺紅或紫色做便裝。如孔子所說,“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這里的關鍵詞語是“繪事后素”,即先有素地,再作彩繪,此可理解為是繪畫的基本準則。子夏觸類旁通,并又就此提出了“禮后乎?”——以道德行為作純正的基礎從事藝術,因而大悅其師,受到稱贊。在孔子看來,畫者首先應為仁者,然后方可產生有分量的藝術作品,這可說構成了儒學教化理論的一部分。在其他場合,就“德”與“才”的關系而言,孔子認為,“有德者必有言”,但是逆定理不存在:有才者未必有德。
于是又引申為“文”與“質”的關系:“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而君子要有立足之本,本立才能道生,這其中又包括了孝悌,可見其儒學的任何藝術理論,歸其根源,都是其教化理論的一部分。進而言之,倘巧言令色而失禮之本,則會以文滅質。因而,無仁何以禮?無禮何以樂?由此,傳統儒學逐漸形成其藝術理念:任何藝術作品實則為其人品性情的折射,而仁人是由剛毅、果斷、質樸、謹言四種品質構成的。
其實,在孔子看來一個人的藝術生涯源于其日常的教化生活,“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以此標準而言,孔子的大弟子顏回便是這種“就有道而正焉”“好學己矣”的君子典范:“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以此,孔子也為中國文人(包括藝人)樹立了一個楷模。
同時,一個畫家要是一個體貼、理解他人的人,如《論語》所載,學生問道:“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答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根據儒家的一貫理念,這種素質不可從外部強制而來,而需于內在自覺而生,因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然而,一切從何而始?答案是“正名”——“必也正名乎”。正如歷史證明的,“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白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繪畫之道亦然。
當然,孔子尚“禮”的內涵遠不止于此,不過僅就服飾與色彩之說,對后世的繪畫便有著深遠的影響。具體表現在宮廷、官府及裝飾藝術均有嚴格的制度,而宮廷畫院的畫師創作要遵守法度規矩。因而,由此形成傳統:任何藝術實踐均應合乎禮樂道義。
二、山水比德
在儒家不多的相關繪畫的論述中,“樂”的理念頗為突出,影響著后代的中國畫壇。就中國畫擅長的“山水”而言,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這其實并非是指“智者只是樂于水,而仁者只是鐘情于山”;其實質道出了孔子的一貫理念:文人要修養自己首先成為君子。正如《詩·周頌·般》所頌:“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山喬岳。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這山河既顯周朝開國氣象,亦有“德化”色彩。再如,《詩·魯頌·閟宮》:“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這里并非單純寫景,而是寓景于情。在西方,由此建立了“移情說”,正如黑格爾所說,“藝術對于人的目的在于讓他在外物界尋回自我”。
其實,這又與道家的自然觀相吻合,如莊子認為,“與物有宜”“順其自然”“效物而動”,知能所不能等。山水之后其實別有寓意——自然滋養德性,自然是君子性情的一部分。對此,孟子有過更為生動的描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后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茍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而觀水之術,則更有“比德”的色彩:“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于海者難為水,游于圣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達。”于是,君子之德便以山水絕佳喻之。“以水喻德”的另一高手是儒家的荀子:
夫水,大遍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洗洗乎不派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綽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絮,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同時,“以玉比德”,更有寓意:“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濕潤而澤,仁也;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暇適并見,情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而稱頌君子的品格,孔子曾用比喻“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到了南北朝時,便有了進一步的比喻,如據史料載,當王公(導)品評太尉(王衍)時,用了“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同時,作為文人的一種品格,他們又都有些高雅的偏好。如,王子猷曾暫居一空室,要求傭人在周圍種上竹子,其大為不解:“你不過小住一時,何必煩勞此事?”王指著竹子道:“何可一日無此君!”
再如,簡文帝(司馬昱)游華林園時,對身邊的人說,“情景相通,令人神意相得的地方不必在遠處;置身于幽靜深邃的林木溪水之間,便會讓人產生莊子游戲濠水之上、垂釣濮水之間所具有的情懷,油然感到鳥獸禽魚,造化萬物,自然來和人親近”。
后世文人對此更是有著不斷地拓展和發揮。如蘇軾對于文同的畫竹,有如此評論:“雍容談笑,揮灑奮訊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確,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于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元代山水畫“四大家”之首的黃公望也說:“松樹山腳,藏根蒼秀,以喻君子。”到了明清兩代,此類畫論更多,如文徵明所言:“古之高人逸士,往往喜弄筆作山水以自娛。然多寫雪景,蓋欲假此以寄其歲寒明潔之意耳。”
特別是到了清代的石濤,“山水比德”之論可謂達到了高峰:“山之蒙養也以仁,山之縱橫也以動,山之潛伏也以靜,山之拱揖也以禮,山之紆徐也以和,山之環聚也以謹,山之虛靈也以智,山之純秀也以文,山之蹲跳也以武……夫水汪洋廣澤也以德,卑下循禮也以義,潮汐不息也以道,決行激躍也以勇......④
正是通過這種實踐與感悟,“山水比德”的理念逐漸演變成為中國繪畫基礎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理論上講,植根于“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哲學理念,使得中國文人很容易找到情與景的天然紐帶。由此,逐漸形成了以山水為主題的中國繪畫格局,而梅蘭竹菊“四君子”的文學化技法,又遠不同于西方繪畫的“逼真表現”技法。
三、以意逆志
在“山水比德”的基礎上,產生了中國繪畫批評,而這主要源于孟子。作為儒學的重要經典著作,《孟子》主要由其本人及其弟子所編纂,在儒學發展史中承前啟后,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亦不可替代。《孟子》的主題思想是建立在人性善理論基礎上的“仁政”,而要做到這一點便首先要從我做起,即“萬物皆備于我”。由“我”而強調“思”——“心之官則思”,此種理念對于各種學科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就文學藝術及其批評而言,主要體現在孟子的“知人論世”觀,如“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所以,解釋詩詞時,不要以文字而誤解其詞語,亦不可因詞語而曲解其意,而應以辭會意。此處孟子探究的是“形式”(語言)與“內容”(意思)的關系,而其不僅限于文學,而且適用其他藝術形式。
孟子以《詩經》來闡述其意,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言,孟子問:“如果舜做了天子,瞽叟卻不是臣民,哪有這樣的道理?”所以,要弄清楚語境、對象、原意,才能準確理解其詩意。
就歷史發展而言,“以意逆志”對于后世的藝術批評產生了潛移默化的滲透和深遠意義的影響。
特別是經過儒學大家朱熹這樣的發揮“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后隨著文人畫的興起,主觀意識、思想境界的日益提升,“以意逆志”逐漸深入繪畫批評領域。
較早的見于南朝詩人江淹為《秦女》所寫的題畫贊:“青琴既曠世,綠珠亦絕群。猶不及秦女,十五乘彩云。壁質人不見,珠光俗詎聞。原使洛靈往,為我道奇方”。到了唐代,以“逆志”題畫詩者漸多。如,張佑的《題王右丞山水幛子詩》:“右丞今已歿,遺畫世間稀。咫尺江湖盡,尋常鷗鳥飛。山光全在掌,云氣欲生衣。以此常為玩,平生滄海機。”
宋代,可說是“以意逆志”評畫的高峰。如對于王維的畫,黃庭堅的《題摩詰畫》,“胸中有佳處,涇渭看同流”,強調其_人間無所求”。特別是蘇軾,極大地發揚了“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的精神。例如,同樣是畫竹,蘇軾認為“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白蜩腹蛇蚶,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而米芾在《畫史》中則記:“子瞻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分?日:‘竹生時何嘗逐節生?”然而石濤卻別有高論:“夫畫竹不作節,尚有何法可拘?翻風滴露,觀者正當得其生韻耳”。顯然,蘇軾是主張“胸有成竹”,信筆而落,得其自然;石濤則以遺民而不屈于新朝,以氣節自負,故有“天下之不可廢者莫如節”之說。石濤立于今世論前人,有感于新朝而發,故言畫竹注重其“節”。現在我們對于石濤的畫論,亦離不開“論其事”“知其人”,方能“以意逆志”。
當然,其后中國的畫論又受到其他思想、學派的影響,變得多樣化起來,但儒學“以意逆志”的影響己根深蒂固。
四、胸中與眸子
如上所述,在孟子看來,萬物皆源于人們與生俱來的“性本善”,因而最為重要的便是自我修養,或日“養浩然之氣”。然而,其具體為何物?“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當被問之何為“善”與“信”的時候,孟子答道:“充實之為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啐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廣義而言,自古文人多磨難,從來痛苦出杰作。對此,最有名的,算是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的一段:
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髕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此外,《孟子·盡心上》說:"TL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疚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孟子·告子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趙歧注:“而后作為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故知能生于憂患。”
桓譚在《新論·求輔》中亦言:“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采不發;……揚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趙歧《<孟子>章句·題辭》:“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系志于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鐘榮《詩品·漢都尉李陵》:“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至此!”
即是說,經歷磨難之后,真君子應全力實現其使命:他應住在最廣的宅院——“仁”里,占據最正確的位置——“禮”中,行走在最寬廣的路——“義”上。得志時,便攜百姓同行,失意便獨守自我之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然而,大丈夫還需具有某些超乎生命的可貴品質:“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而評判一個人的品格,又需綜合來考察,就此孟子提出了“胸中與眸子”的概念:觀察一個人,再沒有比凝視他的眼睛更好的了;因為眼睛不能掩飾一個內心的丑惡。心正,則眼明;心不正,則眸渾沌。所以,聽其言,觀其眸,其性情無掩。
世人可能有所不知,該理念最早是針對中國繪畫而提出的(這在儒學中甚為罕見),后多用于揭示人物品格與其作品的關系——視其為素養的外在體現,由此對中國繪畫,特別是人物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東晉的人物畫大家顧愷之,尤其注重“點睛”。據《世說新語·巧藝》載:“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無關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顧長康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為眼爾!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云之蔽日”。可見,融合“胸中”而外化到“眸子”的功夫實屬了得。難怪顧愷之說,“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所以“揮手易”,那是因為畫外部的動作,而“目送難”表現的是“胸中”事。正如蘇軾所總結:“故畫人物最為難工,雖得其形似,則往往乏韻。故自吳、晉以來,號為名手者,才得三十三人。而這種畫人物的準則,最早正是由孟子提出并論述的。
這里的關鍵詞語是“融合”與“外化”,或“融合地外化”,此意在《易經》中得到了升華。
五、陰陽和諧
在中國傳統文化里,因萬物源于陰陽對立面的組合,故藝術品的質量在很大意義上取決于陰陽的和諧的程度。“陰陽”概念最早由《易經》這本凝聚了獨具中國傳統智慧(特別是“易學”)的書加以詳述;該書揭示了作用于世間的基本原則,對后世乃至當今中國人的方方面面產生了深遠影響。
人類如何理解自然變化規律,自早期歷史這便是困擾中國人的問題。他們逐漸意識到,應當理性地觀察天地之變化(領會天意),而不是迷信地供奉以趨利避害。如文獻所載,圣賢們以默默地以卦占卜求得奇跡,即“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同時,用天數和地數(如二、三)來分別代表奇數和偶數,這些數字演變成了六條線,“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系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就其形式而言,不同的組合(雜卦)預示著不同的事物,如《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由此,該書縱論天下至幽艱深的道理,卻不鄙賤輕惡而取象平易;言說天下紛繁復雜的變化又不錯亂乖異違其內涵規律。《周易》作者先擬喻物象,再言說道理;先審議物情,再揭示變動,由此逐漸形成其變化哲學。《周易》認為,如地之厚重,文人的品性亦應博大無邊,與萬物規律合拍。應用到日常生活,則觀形議象,效法乾坤,如此可賜予天命。
無數事實證明,“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從本質上講,“天地缊,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同時,中國文人開始關注詞(形式)與意(內容)的關系,對于萬物的認識,無論是老子的“道”,還是孔子的“禮”,都須合乎自然變化的規律,與陰陽合拍。然而,二者的不相稱,似乎又是永恒的,如孔子所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孔子這種對于形式與內容關系的思考,對于后世作者與其作品的關系,有著長久的啟示。對于這些變化的透徹理解,涉及形象塑造、角度設計、主觀判斷、變幻移情、盈漲消衰等,而陰陽八卦的轉換,以及乾卦的多種組合,呼風喚雨、形態節氣等,都可反映在一個人的作品中。
如《周易》所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可見,只有深層把握陰陽變幻,才能創作出有分量的作品。如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中所言,“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硅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
所以,陰陽的驅動與和諧是藝術創作的基礎。在中國繪畫史上,典型的例子,如東晉時期的大畫家顧愷之把其好友謝幼輿畫在巖石之中,當問起他為何如此時,他說,謝的陰陽情懷全在丘壑之中,超越他人,自有天趣,故當如此著筆。在其他場合,顧愷之畫人像時,有時幾年都不點上眼睛的瞳孔,人們問其原因,他說:“四肢的美丑,本于畫的奧妙所在無甚緊要,而人物的平衡支點、傳神之處,全在眼睛”他為后人留下了許多精品。
結語
就中國傳統繪畫的發展歷史而言,在儒道釋三家中,儒家思想無疑最本位,影響力最大、最持久,特別是在上述五個方面。“繪事后素”主要體現的是孔子的重仁尚禮的思想,散發著教化的色彩,為后代的繪畫打下了重規矩、講章法的“禮”的底色。“山水比德”映襯的是人文高雅的情趣、天人感應的理念、以及以“表現”為主而非“再現”(如西方的藝術理念)的藝術美學特征,同時也促使了中國畫“科”題材分類的進一步形成(如之后的梅、蘭、竹、菊“四君子”形象的確立)。“以意逆志”引發的是繪畫批評中“立意”的意識,從而使得中國繪畫具有了文學化的特點,令其藝術種類和表現形式更加立體、豐厚,藝術與人生更加緊密。“胸中與眸子”則充溢著文人、志士、君子的浩然之氣,形成了“從藝先做人”的傳統,在藝術上又影響了后來人物畫的傳神理論。“陰陽和諧”是將儒家的宇宙觀融入了中國繪畫的宏觀理論,思與神合,天地互動,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攝影藝術式的現實主義(如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領導人民》《希阿島的屠殺》,籍里柯的《梅杜薩之筏》等那樣具有震撼人心作品),而注重人與自然及陰陽間的微妙變化與關聯,既情動于中而“外張”,又節制收斂而“內順”,以求整體上的平衡。
總之,如上所述,儒學作為一種主導傳統思想和哲學意識,對于中國繪畫有著根本性、全面而深刻的滲透,引領了中國文人的情操、氣質和趣味,從而塑造了中國繪畫的基本民族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