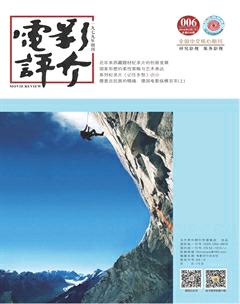文本與影像的交融
陳巖 +周惠萍
近些年來,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成為國產電影的新風尚,尤其是小說和電影的交融更是為導演與編劇所熱力推崇。但由于小說和電影分屬不同藝術門類,從文本到影像的改編面臨諸多癥結;對此諸多癥結處理,電影《一九四二》在國產電影的影視改編中有著諸多成功之處。本文也基于此,從敘事視角的宏觀轉變、人物性格的重新構建以及敘述之于影像的風格轉變三個方面,探析從小說《溫故一九四二》到電影《一九四二》敘事轉換,在為受眾提供多維審美視角的同時,以期為國產電影影視改編提供可行性框架。
一、 敘事視角的宏觀轉變
小說和電影分屬不同的藝術門類,在敘事上呈現著不同的敘述語態;但正由于二者兼具敘事功能,才使得小說和電影有相同之處,“小說和電影文本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二者雖然屬于不同的藝術門類,但是共同完成的是藝術對于人和人生的闡釋”[1];換句話說,正是藝術敘事的共通性,使得小說和電影這兩門藝術有了交融的可能。電影《一九四二》也正是基于此,通過對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敘事視角的轉換,滿足觀者的期待視野,使電影從抽象文字到具體影像變換中顯得更為順暢,主題表達也更為深刻。
首先,相對于小說《溫故一九四二》來說,其最大特點就是發揮文字自由度和靈活性來塑造形象;但要把訴諸受眾抽象思維《溫故一九四二》,具象化為真實可感的活動影像,尤其是小說中著眼于個體敘事與電影對于歷史的宏觀表達,卻呈現著藝術本體上的矛盾,影響著影視改編的主題表達、風格建樹以及基于虛構本質上的藝術真實;鑒于此,在電影《一九四二》中,導演對原作中敘事方式做巧妙處理,消解敘事視角之于文本與影像的敘事矛盾,進而最大限度在尊重原作精髓的同時,盡可能貼合電影藝術鏡像語感。所以,在文本到影像的敘事轉換中,原作原有第一人稱的敘事表達被最大化的削弱,轉為電影《一九四二》中的宏大表達。比如,在小說《溫故一九四二》,第一人稱敘述貫穿全文,但是到電影《一九四二》中,第一人稱這一敘事方式卻只運用在了電影的開頭和結尾,而在影片中間片段的主要篇幅都是以第三人稱來敘述,選取角度也是宏觀視角而非私人化的個體表達。這種影視改編,雖說消解了原作中的私人化視角,但相對于電影藝術而言,在處理觀眾審美與嚴肅主題呈現之間,可以看到導演與編劇都做了自己最大努力。
其次,小說《溫故一九四二》,通過私人化的敘事方式,選取眾多人物,呈現多樣敘述主體,敘事線索也更為多維,這相對于講究戲劇沖突的電影藝術而言有著媒介轉化上的矛盾,也影響著影視藝術的鏡像表達。所以,鑒于電影的宏觀敘事以及戲劇沖突的需要,必須適當地轉換小說中的藝術表達。在原作中,在私人化的敘事視角之下,呈現的是多線發展,除了對于故事本體嚴肅主題的感知外,很難找到真正的敘事主線。所以,在影視改編中,導演在敘事上做了巧妙選擇,立足宏觀視角,對小說的敘事結構做了調整,尤其是削弱以東家老范為代表的逃難鄉親這條線索,轉而把敘事的主線放在以蔣委員長為代表的官僚階級,并由此交代歷史背景,勾畫歷史運行軌跡。也通過這樣的敘事轉化,使得觀者在把握影片故事脈絡同時,深刻思辨生命之于群體毀滅下的的個體涅槃,也以此來消解文本與影像之于觀眾的敘事矛盾。
二、 人物性格的重新構建
“人物,作為小說和電影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是體現主題的載體,更是推動情節發展的動力”。[2]之于小說而言,借用間接的語言媒介,塑造具有典型的人物形象,是小說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但相對于小說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靈活與自由,影視藝術卻只能通過人物的對話和行動來實現。也基于此,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要想塑造出鮮明生動的銀幕典型,必須處理好之于小說與電影間的抽象與具象的問題。尤其是對于由私人視角講述下的調查體小說《溫故一九四二》,缺少鮮明的人物形象,許多人物大都是作者身處家鄉的所見、所感,以及對于各種史料的堆積;再加之作者自身的想象與推斷,附加作家獨特的反諷、丑化、戲謔、戲仿、虛擬等修辭特征語言風格,使得原作中人物不但繁多,而且形象模糊,難以直接呈現于熒幕。也基于此,導演對原作中眾多人物進行了重新定位和確認,利用擴展和移植等改編方法,塑造出了典型的人物形象,使得影片在對于個體生命價值作哲學探討之時,也強化了電影對于戰爭和社會的反思,以及人類之于群體毀滅下的道義準則。
首先就是對老東家的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小說中,老東家老范原型是郭有運和范克儉舅舅的爹,也借郭有運之口說逃荒是為了大家都有一條活命,可正是由于這樣一種求生之路成了所有人的毀滅之路;在這過程中,老東家的追隨者,死的死,散的散,最后借其之口論道“還不如不逃,至少死能死到一起”這一之于生命價值的終極探討。所以,在小說中,老東家老范的人物性格更為單維,具體來說,就是通過私人化的講述,介紹老東家帶領家人逃荒,最后通過自身的人生體驗得出“還不如不逃,至少死能死到一起”這一關乎生命的終極思考。這一單一的人物性格對于講究人物性格要飽滿、立體的影視藝術而言,既有悖于觀者的審美思維,也不利于銀幕典型的塑造以及嚴肅主題的表達。所以,在電影《一九四二》中,導演在原作的基礎之上,對老東家老范這一人物在移植的基礎上進行擴容,使得其在性格塑造上更為立體、飽滿和真實。在影片中,一方面通過其遇到搶食的劫匪就設計報官、為保護閨女大施騙術、借給瞎鹿一碗小米時再三囑咐災后歸還、慫恿栓柱和瞎鹿偷白修德的驢等情節展現其狡詐、小氣、自私自利等性格特征;另一方面通過主動借給瞎鹿一碗小米避免其賣閨女、呵斥小孫子不許吃兒媳婦的奶水、領養失去親人的小孩等凸顯其善良與仁慈。也通過這樣對人物形象的多維塑造,讓影片更為真實、人物性格更為立體、戲劇沖突更為激烈。也正是這樣的敘事改編,使得老東家人物性格趨于多維,讓觀眾在緬懷歷史與反思戰爭的視域下,在深刻思辨國民劣根性的同時,也褒揚關乎文化傳統的民族精神,透視人性光輝。
其次就是對蔣介石的影視改編。小說《溫故一九四二》中對于蔣介石的描寫較多,但大都是同過一些史料和調查來描述,可在全文中的布局較為分散,所以在對其的影視改編中導演一方面是集中處理上的移植,一方面是原著基礎上的擴展。首先,在集中處理上的移植,由于小說中很多關于蔣介石的敘述都是依據事實,所以導演對其處理選擇語言上的轉換,也就是從文本語言轉換到視聽語言。比如在影片中,白修德與蔣介石的會面,因為本就具有歷史真實性,所以在電影中除了由抽象思維到形象思維上的轉換外,內容幾乎和小說相同。比如在小說中反復呈現蔣介石“這是不可能的”講話,在影片中同樣多次出現;此外,蔣介石關于讓《大公報》停刊反省、信仰基督、只喝白開水都與小說相同。其次就是在原著基礎上的擴展,也就是基于歷史真實而呈現的藝術加工,這也是藝術有別于歷史的關鍵所在。在影片中,蔣介石對軍官遺霜的贊揚與承諾、為李培基剝雞蛋、借糧時與張鈁母親臥膝交談情節,都呈現著基于原作和歷史基礎上的藝術加工,也正是由于這樣的改變才使得蔣介石性格刻畫合乎現實可能,顯得更為真實;也讓觀者感知那段不為人知的歷史之時,引起其對貧窮、饑餓、人性等問題作更為深刻的認知和探討。這亦或是亞里士多德《詩學》中所提及的“合情合理的不可能”[3],亦即在合理處理藝術改編的同時,注重切合人性發展的普遍性與必然性,按照人物原有的樣子去“摹仿”;也基于此,通過蔣介石人物形象的內在性格與外在形式的矛盾處理,關乎電影的主題詮釋更為深刻具體,也由此印證黑格爾式哲學思辨下的倫理沖突與正義毀滅。
三、 文本之于影像的風格轉變
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以完整的藝術作品呈現在受眾面前,就帶有各自藝術樣式的特點,呈現出不一樣的藝術風格;尤其是對于小說和電影來說,前者屬于語言藝術,側重于觀者的想象與思考,后者屬于視聽藝術,側重于觀者的感知與體驗,也由此在敘述表達上呈現著不一樣的風格語調。也基于此,優秀的影視改編尋求文本與影像的交融,在保留原作敘事符號精髓的基礎之上,通過小說的敘述語調和之于影像表達的共性邏輯,選擇更利于電影發展的敘事風格。電影《一九四二》正是基于此為轉換基點,通過消解原作中的反諷、丑化、戲仿的語言風格,在滿足觀眾期待視野的準線之上,尋呼更為嚴肅的主題表達和人性探討。
小說《溫故一九四二》中,劉震云的敘述風格更多的是呈現著某種解構本質。尤其是在文中借助自身反諷、丑化、戲謔、戲仿、虛擬等語言,描寫各種身份的人對這段歷史的態度。比如在小說中,當論及被燒死之人時,卻以戲謔的人生態度,借范克儉舅舅這一人物,談論自己后悔當逃兵,以至現在不能當臺胞的事情,而對于災難本身帶給人們內心的傷害與痛苦卻沒有觸及。但在電影《一九四二》中,這種敘述風格就有明顯轉變,導演用鏡像呈現當年災難時,延續對于嚴肅主題的尊重,消解小說戲仿本質,注重災難之于個體的摧殘與毀滅,并由此激發出的人性善良與溫情。比如,在影片中老東家老范借給瞎鹿一碗小米避免其賣閨女、呵斥小孫子不許吃兒媳婦的奶水、領養失去親人的小妮這些情節,透視著些許人性的光輝與溫情;也因此老東家老范的人物塑造極具悲劇色彩,影片也由此更加具有藝術力量與人性張力;也基于此,才把人性扭曲、信念淪喪、命運毀滅的多重探討提升到新的高度,由此生發關乎生命的柏格森式的哲學之思。也正是由于這樣的影視改編,淡化了原作之于影像的戲仿風格,拉近了觀眾與電影審美的距離,使得電影之于社會的情感價值更為真實合理。正如影片開頭所呈現的“Back to 1942”的字幕一樣,其目就是借助小說之于電影風格轉換,尋求合乎自身藝術創作規律的藝術表達,告知人們1942年那段曾經發生過的歷史悲劇。
結語
《一九四二》在保留原著之于歷史真實的基礎之上,把抽象的文字鏡像化為客觀可感銀幕形象,總體說來,還算“夠格”。尤其是通過敘事視角的宏觀轉變、人物性格的重新構建、敘事風格之于人性的多維解讀三個方面的藝術加工,重構了小說之于電影的二維語系,使其敘事基點轉移到對于人性本真的探討之中;雖然還存在些許不足,但這對于當今談及20世紀四五十年代鏡像呈現抗日系列劇的國產電影來說,昭示著藝術創作中社會歷史觀的進步;同時,電影《一九四二》的出現,在為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提供藝術手法上的借鑒之外,也為國產電影乃至世界電影敘事思維轉變提供實踐上總結和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