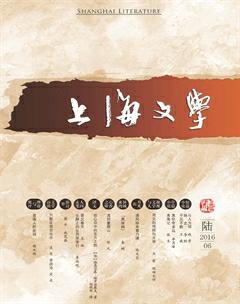遇到董鼎山
這篇文字原先的標題是《探望董鼎山》,開頭這樣寫道:
最近常去探望九十三歲高齡的董鼎山先生。他最近的狀況讓我倍感憂慮。昨天美國《僑報周末》總編劉倩女士來電話說,董先生在洗手間摔倒了,因股骨頸骨折被送進了醫(yī)院。原本約好這個周末隨劉倩,還有《曼哈頓的中國女人》作者周勵女士一起去陪董先生吃晚飯,現(xiàn)在只好調(diào)整計劃,改為去醫(yī)院看望他了。
剛寫到這兒,“咣”地一下接到劉倩發(fā)來的短信:董先生幾小時前去世。我一看短信頓時失去反應,不認識漢字了,什么意思,董先生怎么了,你到底想說什么?我馬上把電話打過去,輸入號碼時錯了幾次,手在抖,心也在抖。可劉倩的抽泣向我證實了一切,董鼎山先生于2015年12月19日上午,在他入住的骨科康復中心,因心臟驟停逝世,享年九十三歲。我望著屏幕上剛剛開頭的稿子發(fā)呆,莫非這是冥冥之中上天對我的暗示?或者說,如果我不開這個
頭,一切都不會發(fā)生?董先生還會像往常一樣給我開門,喊我名字,他喜歡叫我“陳九老弟”,從二十年前我們認識就這么叫。我一下麻木了,說不出話,連哭都不會,只有默默流淚,沒有聲音。
董先生啊!
自董先生夫人蓓琪2015年5月因骨癌去世后,他的情況一直不穩(wěn)定,心情和身體都大不如前。那天我去看他,他對我說,陳九老弟啊,我整夜睡不著,很痛苦啊,滿腦子都是蓓琪的影子,我覺得她肯定沒走,一定跟我捉迷藏躲在什么地方了,我要把她找出來,找不出來我也不活了!他的表情真誠得讓我緊張,不知該如何安慰他。他與蓓琪五十多年相濡以沫形影不離,這我們都曉得。蓓琪是瑞典裔美國人,金發(fā)碧眼,身材苗條,當年無疑是顏值爆表的美女。我聽董先生聊過當年追求蓓琪的情形,在紐約國際留學生俱樂部的舞會上與她邂逅,馬上展開攻勢。先請人家喝啤酒,再請?zhí)琛I蟼€世紀50年代的美妙時光喲,物質(zhì)的潘多拉盒子尚未開啟,人們沉浸在歐洲浪漫時代遺留下來的經(jīng)典純情,和戰(zhàn)后理想主義的夢幻中。董先生每每說到這兒都熱淚盈眶,他懷念自己的青春年華,那個美好的青春年華是與愛妻蓓琪一起走過,共同分享的。
最讓董先生刻骨銘心的是蓓琪的善良忠厚,和完全可與東方式賢妻良母媲美的深情厚意,體貼入微。董先生這樣說道:蓓琪在我眼中就是圣女,她的好心腸令我一想起就禁不住流淚。她經(jīng)常從雜貨店購買食品送給教堂的貧民食堂,也會將罐頭或用舊的羊毛衫放在睡袋里、放在附近小公園的凳子上任窮人選用。一位九旬鄰居老太太告訴我,蓓琪常帶食物探望她,且有求必應。蓓琪去世前,許多不知名的鄰居前來探望她,向她表示感謝和敬意,很多人我都沒見過也不認識。董先生說,我兩次攜蓓琪回中國探親,不懂英文的嬸嬸們都要拉著蓓琪的手同行,毫不掩飾對她的愛惜。一位叔母說,從沒有見過這么和氣善良的“外國女人”。她們驚異于外國女人也有如此溫雅仁慈的氣息,認為我娶洋女沒錯。我大哥和蓓琪告別時還激動得流下眼淚,我弟弟樂山夫婦成為她在北京的導游,稱贊蓓琪不愧是中國人的賢妻,為我祝福。蓓琪為了讓我吃上中餐,專門跑到唐人街的中餐館,向大師傅學炒中國菜,宮爆雞丁、芥藍牛肉,做得有模有樣,這是她的一片心啊。
深知董先生與蓓琪伉儷情深,此刻看到他在蓓琪去世后的痛苦心境,我非常震動,百感交集。我隱約聽說,董先生甚至自殺過,被送到醫(yī)院搶救。當時蓓琪拖著彌留之身看望從死神手里奪回的董先生,兩人緊緊相擁,不忍分別,讓在場的醫(yī)生護士們紛紛垂淚,連我寫到這兒都熱淚盈眶。還有什么比這樣的夫妻感情更珍貴的呢?這種深情厚意只屬于好人、有良知的人、知恩圖報的人,那必是全身心的傾注,不作他想的情感投入,正因為如此才永不疲憊,永遠新鮮。夫妻恩愛的秘訣就在心靈,幸福只屬于善良的性情中人,多少金錢都不換,多少缺點也不怕。
面對這種狀態(tài)下的董先生,我和朋友們一度焦慮,該如何幫他走出喪妻之苦呢?而最終解救董先生的還是愛妻蓓琪。在董先生九十三歲生日過后,也就是2015年初春的一天,他為更多陪伴病中的蓓琪曾一度宣布封筆,結(jié)束他近八十年的寫作生涯。他這篇宣言發(fā)表在美國《僑報周末》和上海《新民晚報》的專欄上,引起很大轟動。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董先生就在中國的《讀書》雜志、《新民晚報》等諸多期刊上發(fā)表文章,近十年來又在美國《僑報周末》上開設專欄。在幾十年的歷史跨度中,他在中國大陸和美國華人社區(qū)贏得數(shù)不清的讀者粉絲。很多人,包括我,是讀著董先生的文章放眼看世界的。我們對他文章的期待不是尊重二字能說盡的,更像習慣和依賴,是我們審美需求的一部分。但他還是休筆了,從那以后的一段時間里再沒發(fā)表過文字,直到蓓琪去世。蓓琪在彌留之際曾叮囑董先生,你此生為寫作而來,離開寫作你就枯萎了,請答應我,我的愛人,堅持寫下去,為那些期待你的人們。董先生向我講述這段往事時再度垂淚,他緊握蓓琪的手向她保證,我一定繼續(xù)寫下去。就在蓓琪去世后不久,董先生的專欄重新開放,他敏銳的哲思像往常一樣再度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聽董先生講述這番話時,我不能不為蓓琪的大愛和睿智深深感動。她了解董先生,就像了解她的孩子。她對董先生的愛遠遠超越她的肉體,繼續(xù)存活在董先生的生命里和文字中。
董鼎山1922年出生在浙江寧波一個殷實的大家族。十四歲開始在寧波《時事公報》副刊上發(fā)表文章。十七歲起為柯靈主編的《文匯報》副刊撰稿。1945年從圣約翰大學英文系畢業(yè),考入《申報》當記者,采寫外交和政治新聞。當時在上海新雅酒店,董先生每天都和作家、記者、藝人交換信息和文稿。后加盟《東南日報》做新聞編輯,同時撰寫小說散文,在文壇上漸漸成名。1947年董先生赴美,先后獲密蘇里大學新聞學碩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碩士學位。在紐約他主持過《聯(lián)合日報》國際版,并受聘于紐約市立大學,成為英美文學兼亞洲部的資深教授。旅美近七十年,董先生筆耕不輟。早自上世紀50年代起他就用英文為《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美聯(lián)社特寫》、《星期六評論》、《圖書館月刊》、《美中評論》、《新亞洲評論》等報刊撰寫評論文章。直到1970年代末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一種把歐美現(xiàn)代思想介紹給中國知識界的使命感燃起他重新用中文寫作的熱望。自1979年為《讀書》雜志開設“紐約通訊”專欄始,他的文章在中國內(nèi)地、港臺和美加的中文報章上頻繁出現(xiàn),造成轟動中外的“董鼎山現(xiàn)象”。近四十年來,董先生出版了《天下真小》、《西窗漫記》、《書、人、事》、《留美三十年》、《西邊拾葉》、《美國作家與作品》、《西窗拾葉》、《第三種讀書》、《紐約文化掃描》、《董鼎山文集》(二冊)、《自己的視角》、《紐約客閑話》、《美國夢的另一面》等書。正如蓓琪所說,他此生為寫作而來,讀書寫作才是他典型的生活方式。
對董鼎山先生的評價已經(jīng)很多。特別在他去世后這段時間,媒體和網(wǎng)上呈現(xiàn)大量文章懷念他,公認他是中美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當之無愧的“美國文學大使”。董先生在幾十年時間里,不遺余力向中國廣大讀者介紹美國文學現(xiàn)狀,幾乎將美國作家和作品“一網(wǎng)打盡”,為中國廣大讀者和作家了解美國文學最新發(fā)展動態(tài),為中美文化交流作出獨特的貢獻,無人出其右。對我本人來說,這些評價都不錯,只是缺乏些情感色彩。歷史是有情感的,當情感被抽空,歷史也就被遺忘了。我開始讀董先生的文章是在1979年,那時我在上中國人民大學。剛剛創(chuàng)刊的《讀書》雜志為知識界吹來一股春風,立刻成為莘莘學子的最愛。最吸引我的便是“紐約通訊”這個專欄,主筆的名字正是董鼎山。這個名字很容易記,鼎像一座鐘,鐘在山上,敲起來像一種召喚,肯定傳得很遠,從紐約傳到北京。當時介紹海外現(xiàn)狀的不止董鼎山一人,還有趙浩生、袁曉園等,但毫無疑問,影響力知名度最大的非董鼎山莫屬。那是個百廢待興的歷史時期,中國的發(fā)展方向在哪里,改革開放的目標是什么,這些問題無疑會折射到每個中國人的思考中,特別是恢復高考后的大學生,像等待雨水滋養(yǎng)的禾苗,他們思想活躍又比較單純,想放眼看世界,對任何來自中國以外的信息格外敏感。《讀書》雜志和董鼎山先生的“紐約通訊”專欄正在這時,踩著歷史的節(jié)拍,出現(xiàn)在新一代知識分子的面前。任何一場社會變革都必須有思想解放階段,就像“五四”運動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礎,改革開放同樣需要思想準備階段。董鼎山先生的文字在客觀上使他成為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啟蒙者之一,他對西方文學和文化的介紹極大開闊了新一代知識分子的眼界,擴展了他們的思考,為他們后來承擔改變中國的重任提供了動力,這些人至今仍是改革開放的中堅力量。中國在那個歷史時刻與董先生相遇,或許是一種偶然,但機會只屬于有準備的人,董先生幾十年逆旅生涯心系祖國思念故園,在深諳美國文化的同時,時刻關注中國的發(fā)展,豐富的知識閱歷和對祖國的向往是他不負機遇的必然。慶幸《讀書》遇到他,也感謝他選擇了《讀書》。
心誠則靈。定居紐約后,我遇到董先生,并與他成為忘年之交。
第一次遇到董先生是上世紀90年代中,在“海外華文作家筆會”的聚會上。關于這次活動我在《夏志清印象》中曾有記載,作家海鷗女士介紹我加入筆會,在那次聚會上我第一次面對夏志清先生、唐德剛先生和董鼎山先生。如果沒記錯的話,當時筆會會長就是董先生。不過當時我心情有些緊張,又不愿打斷他們幾位名家的爭論,他們湊到一起總愛爭論些什么,手里舉著酒杯,興奮的神色像孩子一樣,臉上的表情無比純真。聆聽他們交談本身就是一種享受,哪還顧得上其他。
與董先生的全面接觸始于不久后一次朗誦會。“北大筆會”會長姚學吾教授約我參加在曼哈頓東六十五街“華美協(xié)進社”的中秋詩會。他老說我的詩是“新新月派”,還說老新月派的徐志摩曾在華美協(xié)進社朗誦過詩歌,我應追隨其足跡,也在那里朗誦才對,還特意囑咐多選些抒情的、非政治的,因為聽眾哪兒來的都有,大陸港臺的,新移民老移民,董鼎山先生也會參加呢。記得那是個陰天,華美協(xié)進社的會議廳亮起燈盞,棕色硬木墻板映著古典的黃色燈光,給人恍若隔世的錯覺,仿佛徐志摩的身影,特別是他的圓眼鏡,在燈光下閃爍著。我朗誦了三首詩,《拆秋千》、《女兒》和《紐約午后》。我很投入,我的詩都有韻腳,節(jié)奏感很強,非常適合朗誦。我是從喜歡朗誦到喜歡寫詩的。《女兒》這首詩表達一個小女孩兒面對父母吵架的復雜心境,愛媽媽又舍不得爸爸,深夜起來拖著被子找爸爸,發(fā)現(xiàn)爸爸并未離家出走,她欣慰地在門口就睡著了。朗誦時,我看到有些聽眾擦眼睛的動作,還聽到吸鼻子的聲音。
結(jié)束時我正往外走,只聽一句“陳九老弟”的呼喚,董先生已在我的身邊。我頓感驚訝,完全想不到我仰慕已久的董鼎山先生竟會稱我老弟,且不說年紀,就這份平易的親切感已讓我受寵若驚,不知如何是好。董先生說他很喜歡我的朗誦,“你的口音是標準京片子,我很久沒聽到這么好的朗誦了,你的詩歌是真詩歌,不是矯揉造作的詞匯堆積,我最不喜歡那些用詞華麗內(nèi)容空洞的詩歌散文了”。我被董先生說得不好意思,都開始語無倫次了。我告訴他我早知道董鼎山的大名,非常喜歡他在《讀書》上的隨筆,從未錯過。他則鼓勵我把詩歌收集起來出詩集。讓我最難忘的是,董先生還說,如果出詩集,我愿意為你寫序。真的?那時我在海內(nèi)外華文報刊上發(fā)表了不少詩歌,正琢磨是否出本詩集,一直沒拿定主意。正是董先生的提議促成了我第一本詩集《偶然》的誕生。我至今仍保留著董先生那篇序言的手稿,是抄在一份稿紙上的鋼筆字。他因不熟悉漢語拼音,始終不習慣用電腦打字,他一直堅持手寫漢字直到去世。
此后我與董先生的交往漸漸頻繁。我往往下午去看他,他與蓓琪午休起來,精力比較充沛。他家在曼哈頓東十九街與二大道交口處,樓下不遠有個面包房。每次去我都先在那里買個黑森林蛋糕,那是蓓琪的最愛。我把蛋糕交給蓓琪,她煮好咖啡,再把切好的蛋糕和咖啡擺在我和董先生面前的茶幾上。乳白色的茶具,巴洛克風格的花紋,斜陽穿過窗子照在古香古色的地毯上,那種安詳是令人難忘的。我們一起度過不少這樣的時光,聽董先生娓娓而談,天南地北無拘無束。我注意到他喜歡聊過去的事,比如說起他小時候七八歲第一次從寧波老家到上海,穿著棉布長衫,四下茫然的樣子,他的笑聲完全是有溫度的、暖暖的,讓你感到一個男人的似水柔腸。有人說懷舊是因為衰老,直到遇見董先生,我再不信這個謬論。好記性源于真誠的生活,只有投入真情實感記憶才經(jīng)久不衰。那是人生的財富,滋養(yǎng)著善良的靈魂,只怕有些人想懷也懷不上,因為壓根兒沒有美好的情懷,懷什么呢?懷舊分明是一種特權,好人的特權。當董先生說起上海“孤島天堂”期間,他在柯靈主持的副刊上發(fā)文章的歲月,嗓音明顯帶著彈性,目光放出靈火般的異彩。那是個國破山河在的悲愴年代,每個華夏子孫,尤其年輕人,都必須對命運作出抉擇,是裝聾作啞甘當順民,或出賣良知借機而上,還是發(fā)出吶喊?趕上動蕩歲月,誰也躲不過考驗。董先生無疑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當時柯靈主持的副刊是淪陷區(qū)的一盞明燈,感召和鼓勵著無數(shù)年輕人審視國家命運,投入到救國護種的洪流中,董先生的青春正是這樣度過的。這與后來他在《讀書》上發(fā)表文章頗為相似,也是歷史的轉(zhuǎn)折點,是故步自封走以往老路,還是放眼看世界,為中國融入世界找到發(fā)展的道路,對每個中國人同樣是一種抉擇。董先生那時為中國知識界打開一扇看世界的窗,為時代變革施加了自身的影響,這不是偶然的,只能從他深刻的民族情懷中尋找答案。我們交談時董先生每每感慨光陰飛逝,當年他來美本為短期考察,誰想竟“嘩”地度過四十多年光景。他說“四十多年”時手在空中揮舞,仿佛要拽住時間。身處異鄉(xiāng)時間的確過得快,我自己在美國也快三十年,“咣啷”就消失了,仿佛做了個夢就是一輩子。
最讓我走近董先生的是那次同他飲酒。那是2002年冬末的一天,天空微微飄著雪花。我第一本詩集《偶然》剛出版,我和太太帶著新書到他家表達謝意,董先生寫的序言為該書增色不少。當他得知我太太是上海人,愉悅的神色溢于言表。他們開始用上海話交談,伊伊儂儂,我雖然說不好但聽得來,盡量參與其中。想不到的是,董先生的上海話竟有些遲鈍了。我太太則揶揄我說,儂勿曉得,董先生講的是老派上海話,儂懂啥啦?那個歡樂氣氛喲,止不住漫出窗外。當然,還是黑森林蛋糕,還是蓓琪的咖啡,蓓琪弄好咖啡就躲開了,特意把交談留給了上海方言。她的賢惠絲毫不比東方女性少,讓我感動。
因是上海話起頭兒,我們又隨董先生回到往日的南京路大碼頭。兩件事讓我頗感意外。一是當年他工作的報社就在南京東路的新雅酒店。二是外灘的黃浦公園,因距新雅酒店不遠,他常去那里邊喝茶邊寫作,俯瞰整個黃浦江面。這真太巧了,我1982年在上海畢業(yè)實習時也住過新雅酒店,也總?cè)S浦公園的茶樓喝茶,構(gòu)思論文,瞭望窗外的外白渡橋、俄國公使館,還有遠處海軍碼頭的艦船。我喝的是一種“魁星茶”,幾種綠茶混合而成,味道獨特,五毛錢一壺,不打烊就能一直喝下去。董先生聽后驚訝道,是,那能嘎巧的啦?我們感慨萬分笑成一團,蓓琪都忍不住過來分享我們的歡笑,她會說,你們這么高興,這么高興啊(you are so happy, you are so happy)。雪日的黃昏很短暫,與交談的熱烈相反,光線漸漸暗下來。我們提出請董先生夫婦到樓下一家上海餐館共進晚餐,來的路上我們就選定那里,干凈,東西也不錯。可蓓琪卻說,我不去了,你們接著聊,多難得啊。董先生面露遲疑,蓓琪則勸他,你不是喜歡中餐嗎,去吧,好好享受晚餐(enjoy your dinner please)。董先生欣然從命,歡歡喜喜跟我們下樓,那副輕松愉快的表情,浸透了蓓琪的一片深情。
那晚我們聊得好盡興,先叫了一支紅酒,老板又送了一支紅酒。早就知道董先生喜歡紅酒,頗有酒量,在“海外華文作家筆會”的聚會上就曾領教過。現(xiàn)在能單獨與他共飲,機會難得。我們坐在最里面一張桌子,頗有雅座的味道,看杯中的瓊漿一次次在燈光下閃著瑪瑙色光澤,令人沉醉。董先生漸漸飄逸起來,說起他的青春年華,在圣約翰大學讀書時的愛情經(jīng)歷,他第一部小說與他愛情的淵源,和老友們勞燕分飛不知去處的落寞。說起在副刊發(fā)表愛國文章的激情,憲兵搜查時嘎嘎的皮靴聲。說起故鄉(xiāng),老家的醉蝦醉蟹必須是河里的,淡水的。還有后來的旅美生涯,如何在英文報章上尋找祖國的蛛絲馬跡。他興奮的神態(tài)像個小伙子,絲毫看不出年近八十的樣子。我發(fā)現(xiàn)青春的奧秘是真情,只有用真情生活才能心地坦然,坦然的性情才是青春的本質(zhì)。突然,董先生說,陳九老弟,你不是喜歡唱戲嗎,聽說和楊春霞還同過臺,唱兩句吧,我很想聽啊。我環(huán)顧左右,客人不多,因為快打烊了。我問老板行嗎?沒想到他是個爽快漢子,唱啊,我也想聽呀。那我來段《龍鳳呈祥》如何?好,《龍鳳呈祥》好!“勸千歲殺字休出口,老臣與主說從頭……”當然不能亮開嗓子大唱。老板送的那支紅酒就是這時端上來的,喝吧,還有!我再沒見過那么瀟灑快樂的董先生,完全本色呈現(xiàn)。我唱時他還為我打拍子,在桌上敲擊著,十分投入。他說陳九老弟啊,你臉都紅啦。我也說,董先生,您看看自己,也紅了呀。我們哈哈大笑,時光在幾十年前的老上海與紐約間穿梭徘徊,眼前的情景仿佛變成發(fā)黃的照片,甚至可以聽到汽笛離岸的鳴響,嗚嗚嗚的,我們完全沉浸在往日時光里,享受著美妙的懷舊情結(jié)。這一幕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做夢都夢到董先生打拍子的樣子,輕輕晃著頭。那天他穿著藍色西裝上衣,下面是一條灰褲子,董先生永遠風度翩翩。男人的風采源于偉大的心靈。這話不是我說的,是“聯(lián)大”秘書長瓦爾德海姆紀念周恩來時說的。當時我不滿二十歲,在寒風里聆聽大喇叭播放各國政要紀念周總理的悼詞,便牢牢記住了。此刻想起這句話,用在董先生身上再貼切不過了。關于這次晚餐,我曾寫過一首詩作為紀念:
街燈夜雪
與您小聚淺酌
原想您是
含蓄的學者
此時卻感慨您的
坦誠性格
除學識之外
更有男人本色
年輕的血氣
看盡了破碎山河
恨不能奔赴沙場
躍馬揚戈
誰料渡過太平洋
本想幾周,幾個月
一下竟飛逝了
幾十個春秋寒熱
異國月光下
走過徘徊的身側(cè)
歌特式窗前
流淌深情的思哲
故鄉(xiāng),始終是一個夢
揮之不去的夢
在心中潮起潮落
感嘆您寫下
如此之多的著作
大海般浩瀚的文字
凝聚成童心如火
您對我說
來,唱段京戲吧
你唱我來和
曲輕情重
雪冷心熱
小館子打烊時
老板卻又將新酒
輕輕放上了桌
在與董鼎山先生二十來年的交往中,感觸最深的何止是他的學問和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獨特貢獻及歷史地位,更是他的為人,善良真誠,樸實無華,甚至孩子般的天真。自美國《僑報周末》2007年開設“紐約客閑話”欄目起,董先生和我均為該欄目的專欄作者,他的專欄叫“隨感錄”,我的叫“淺酒微醺”。董先生利用這個專欄,充分發(fā)揮自身特長,對美國文學界重要事件展開評論,并向中文讀者介紹美國文化現(xiàn)狀,格外引人矚目。而我則用一貫的幽默風格,對國內(nèi)和海外華人界發(fā)生的新鮮事發(fā)表看法。此前我從未寫過專欄,心里沒底,為此特意向董先生請教過。他的態(tài)度簡單明朗,一句話將我的猶豫掃蕩一空。他說,陳九你就按平時說話的口氣寫,像跟我聊天這樣寫,千萬不要追求華麗辭藻,別想太多。后來證明董先生這些聽似簡單的忠告并不簡單,而是基于對我個性了解的建言,對我克服心結(jié),形成自己的文字風格很有啟發(fā)。不僅如此,我的專欄文章幾乎每篇董先生都看,還多次來電話談他的感受。比如對隨筆《打哪兒冒出的蘭博基尼》,他問我蘭博基尼是什么車。還說他在密蘇里讀書時買過一輛福田牌轎車,那是他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車,畢業(yè)后來紐約發(fā)展一直住曼哈頓,因停車不便就再沒買過車。還有一次對《追求名牌還是毀滅名牌》一文問道,什么是奧特萊斯?我說就是OUTLETS。哦,是OUTLETS呀,那應注明英文,否則讀者會糊涂,還說他和蓓琪只去過一次OUTLETS,是陪國內(nèi)的朋友,其實曼哈頓的名牌店經(jīng)常有樣品展售(sample sale),價格比奧特萊斯還便宜呢。
董先生再次為我的新書寫序是2014年4月,三聯(lián)出版社欲出版我的隨筆集《紐約第三只眼》,其中收錄了我在“紐約客閑話”欄目上的部分文章。我曾猶豫要不要開口請董先生為該書寫序,因為當時他的生活正進入一個艱難時期,蓓琪被診斷出骨癌,因年紀偏大不宜手術,只能采取化療緩解病情,她的狀況時好時壞,讓董先生憂心如焚。那天下午我去看他們,蓓琪居然還為我做了咖啡,她瘦得很厲害,往日儀態(tài)已改變很多。我和董先生輕輕地談話,說著說著說到這本書上。我當然希望董先生寫序,這些隨筆短章承載著他多少關注,還有誰能代替他呢?沒想到他一口答應,可以,沒問題,你選幾篇比較精彩的給我,我盡快寫給你。可不幸的是,兩天后我接到董先生電話,他竟在洗手間跌倒了,磕破了頭。那段時間我每天給他打電話,問他情況,讓他有問題隨時打電話給我,序言的事就放下吧,不要再寫了。沒想到的是,一周后再去看望他時,他竟將幾頁手寫的文稿交到我手上,并略顯歉意地說,我手有些抖,記憶力也差了,如果有錯別字你幫我改過來。我頓時語塞,看著這些涂改過的鋼筆字不知說什么好。董先生書寫的習慣還是從右至左,從上到下豎排的傳統(tǒng)風格。我特意找出他十幾年前為我詩集寫的序言原稿,對比之下,那時的字體清秀爽快,而此刻已今非昔比,字里行間充滿歲月的烙印。但即使一切都在改變,唯有董先生那顆真誠善良的靈魂始終如一,永遠不變。
我不擬過多描述與董先生在公開場合的交往,盡管這種機會很多。比如2001年“東方文學獎”頒獎典禮,2002年華美協(xié)進社主辦的“董鼎山八十壽辰”紀念活動,2003年燕京論壇的座談會,2004年華美協(xié)進社舉辦的“漫談董鼎山”研討會,2005年人文協(xié)會主辦的“抗戰(zhàn)勝利六十周年詩歌朗誦會”,2010年華文作家協(xié)會為他舉辦的八十八歲“米壽”祝壽活動等,還有海外華文作家筆會每月一次的聚會,這些因涉及諸多名家的共享,像王蒙、夏志清、唐德剛、鄭愁予、哈金等,應擇文另敘。但有件事令我難忘,就是2014年《僑報》作家俱樂部為他頒發(fā)“終身成就獎”的典禮,那是董先生去世前最后一次參加公開活動。他在獲獎感言中提到了與弟弟樂山的誤會,用“情何以堪”描述自己遺憾的心情,讓我非常感動。董先生已去世了,我可以用“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表達我的感受。他對手足兄弟一片深情從未更改,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還念念不忘。
在與董先生二十年交往中,我私下多次聽他談起與弟弟董樂山的感情,深感董先生心底非常看重同袍親澤。他是個重感情的性情中人,對朋友如此,對兄弟姐妹更如此。每當說起那時追求光明進步,與弟弟妹妹一起,毅然為民族獨立和解放奔走呼號,他臉上洋溢出滿足的神情。我記得那是個明媚的下午,他的身影被陽光映得閃亮,在我眼前熠熠生輝。我被他的激情感染著,腦海里映出青春燦爛的董氏兄弟走在上海街頭的情景。還有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他們二人又成為同一戰(zhàn)壕的戰(zhàn)友,樂山大量翻譯西方著作,鼎山則開專欄直接向中國知識界介紹歐美文學現(xiàn)狀,他們再次像年輕時一樣,面對祖國作出相同的選擇。人們老說董氏兄弟都不簡單,為何?非凡的人生源于面對歷史的共同抉擇,人生只有壯麗過才永遠不會庸俗,這種深刻的豪邁感與血乳交融的親情無論怎樣估計都不過分,只有經(jīng)歷過的人才能體會到。董先生即便與弟弟有爭論也很正常,這是他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毫不奇怪。讓他放不下的是,本想像往常一樣,有機會向弟弟解釋清楚,他們畢竟生活在海內(nèi)外不同環(huán)境里,同樣問題只因角度不同,結(jié)論的表述就可能不一樣,所謂爭論大都是誤解,只要有機會說清楚就可以了。可是這個愿望卻因弟弟樂山的突逝而無法實現(xiàn),董先生失去了最終解釋的機會。這才是董先生深感遺憾的原因。很明顯,如果他心里沒有對弟弟樂山的深情厚意,又何至于在自己獲得終身成就獎的頒獎典禮上提到弟弟呢?
凡定居海外,并住過足夠長時間的華人,比如我自己,在紐約生活了三十年,非常理解董先生的遺憾心情。所謂分歧啊不同啊,其實沒那么嚴重。我們與國內(nèi)同胞生活的環(huán)境不同,對事物的側(cè)重肯定也不同,這非常自然,也是經(jīng)常發(fā)生的。我本人就有與董先生類似的經(jīng)歷。比如對國內(nèi)某些問題,像欠薪或野蠻拆遷,我實難接受,認為這是地動天搖的大事,薪水都敢欠,人家住在屋里就敢扒房子,這在美國是聯(lián)邦重罪,要進監(jiān)獄的!可我在國內(nèi)的同學就不同意我的看法,認為我虛張聲勢,什么叫地動天搖,想造反嗎?中國很多人都是改革開放的直接受益者,他們從過去幾十元一個月的死工資,變成起碼幾套房子的擁有者,甚至更多,你地動天搖什么意思,想動人家奶酪嗎?想讓他們重返貧窮嗎?人家當然反對你。可這等于他們覺得欠薪和野蠻拆遷合理嗎?完全不是。本質(zhì)上他們跟我沒區(qū)別,同樣對此非常憤怒,深表不平。只是他們要按自己的方式和時間表解決問題,發(fā)展的過程就是不斷出現(xiàn)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這是當前中國國情,與美國很不一樣。毫無必要對此過度解讀,董氏兄弟如果有什么爭論,不過如此而已。
蓓琪病逝是在2015年5月8日。當時我正在北京探望年邁的父母。當我得知了這個噩耗,心中既有對蓓琪的懷念,更有對董先生的擔憂。回紐約不久,我馬上約作家周勵和《僑報周末》總編劉倩女士到他家探望。董先生一開門我就感到極大的不同。屋里顯得幽暗凌亂,很多書本斜躺在書架和桌子上,如果蓓琪還在,這是不可想像的。董先生的臉上充滿悲傷,提起蓓琪老淚縱橫,我從來沒見過他哭泣,面對這位九旬老人的淚水我無言以對,緊張得不知該說什么。他與蓓琪相濡以沫五十多年,蓓琪的去世給他帶來如此大的打擊,已到生死之地步,這讓我不免慌亂。我本想安慰他,希望董先生好好活下去,繼續(xù)把他的哲思文采展現(xiàn)給世間,可看著他望不到底的悲傷,我啞口無言。
此后幾乎每天我都給董先生打電話,隔三岔五就去看他。那次作家五月,一位浪跡天涯的“游吟詩人”,難得從緬甸趕回來看望董先生,也邀我陪她同往。那是2015年9月一個周六。去前我還電話董先生,要不要從Petes Tavern帶個三明治給他,董先生很喜歡那家的三明治。董先生家位于曼哈頓最悠久的社區(qū)之一,附近有不少紐約地標式的餐館酒吧。這家Petes Tavern算是最古老的,建于1864年,與董先生家一街之隔。著名小說家歐·亨利曾經(jīng)是它的常客,這家餐館至今仍保留著歐·亨利坐過的位子,據(jù)說他就在這里完成他的名作《麥琪的禮物》。我們推開董先生家的門,那張滄桑的面孔再度呈現(xiàn)在我的面前。我突然發(fā)現(xiàn)董先生的書架已空蕩蕩,忙問他那些書呢?他不無感慨地說,陳九老弟啊,我在處理所有東西,這些書都是中文的,我女兒碧雅也沒興趣,我準備把它們都捐出去或送給朋友。董先生的話讓我頓感沉重,這分明是料理后事啊,深深的悲傷不禁漫過心頭。人難道都有這一天嗎?無論怎樣瀟灑過輝煌過,走向終結(jié)的背影都是蒼涼的。在這間客廳里,曾掠過多少文人雅士的身影,董樂山,馮亦代,黃宗英,謝晉,陳翰伯……我根本數(shù)不過來,他們高談闊論伴著朗朗笑聲,透過窗欞飛入歷史的篇章,為一個深情的時代縱情歌唱。還有我自己,多少次在這里聆聽董先生的縱橫才思,品嘗過蓓琪的咖啡,甚至用過他們的洗手間,這一切都讓我倍感親切,貼著我的面頰緩緩蠕動,直到漫及全身。而此刻啊,面對空空的客廳,我仿佛聽到鐘聲已經(jīng)敲響,董鼎山先生的那個時代,或者說海外文人的“名士時代”,包括夏志清、唐德剛等,正悄悄落幕,歷史此刻像一本硬皮的精裝書,已翻到最后一頁,帶著厚重的質(zhì)感,在慢慢合上。
那天,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進董先生的臥房。在與董先生二十年交往中他從未讓我進過他的臥房。他對我和五月說,來,跟我來,我有東西給你們。我們猶疑著跟在他身后,那是間怎樣雜亂無章的臥房啊!我的目光頃刻定格,眼前就像一幅油畫,訴說著董先生的心境和生命狀態(tài)。他顫巍巍舉起一張發(fā)黃的照片,那是他母親和他三歲時的合影,也就是說,這張照片整整九十年了。他對我們說,這是我母親,我快要見到她了。他的語氣十分平靜,充滿深情,甚至可以感到天真的孩子味道。人無論多老,只要說起母親就立刻返老還童,母親是生命的源泉。我們靜靜伴著董先生,只見他從桌上拿起一本書交給五月,說這是送給她的禮物。又從抽屜取出一只精美的盒子,是福建名茶大紅袍,遞到我手上說,陳九老弟,留個紀念吧。我們都很惶恐,不知該感謝還是安慰他。我們在董先生的臥室里合影留念,背景是凌亂的書架,凌亂的床鋪,凌亂的時光。
后來我又多次看望董先生,有時是與朋友同行,比如《僑報》社長游江、女作家周勵,還有與董先生合作多年的《僑報周末》總編劉倩女士。這又回到了文章的開頭,我們都對董先生的狀況放心不下,格外關注。那天劉倩突然來電話,說董先生在洗手間又摔倒了,股骨頸骨折被送進醫(yī)院。本來說好周末陪董先生吃飯的,現(xiàn)在只好調(diào)整計劃,改為去醫(yī)院看望他了。萬萬沒想到的是,就在我們準備去醫(yī)院的前一天上午,在骨科康復中心的病床上,我們敬愛的董鼎山先生,安靜走完了他九十三年的生命,與這個紛紜莫測的世界揮手告別了。聽到消息,我悲痛之余猛然意識到,自蓓琪去世,董先生其實一直生活在“準備”狀態(tài),他的靈魂早隨愛妻而去了。蓓琪肯定看他沒人照顧,太過孤單,于心不忍才接他駕鶴西去的,在那里,蓓琪會像往日一樣呵護他。基于蓓琪的臨終囑咐,董先生承諾把在《僑報周末》的專欄繼續(xù)寫下去。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就在逝世前幾天,他還向總編劉倩發(fā)出最后一期稿件。劉倩在董先生去世前一天收到稿件,并于他逝世當天刊登在董先生的專欄上,緊接著便傳來他去世的消息,一切恍若音樂般合拍。董先生的一生就是一部大調(diào)協(xié)奏曲,激昂奔涌,深情瀟灑。他從十四歲開始發(fā)表文章,一直寫到生命最后一分鐘。我堅信這是個奇跡,九十三歲寫字或許不稀奇,但把高壽、死亡、寫文章、發(fā)表文章配合得旋律般完美,唯董鼎山獨有。如果歲月是五線譜,他的文字便是音符,隨著歲月跳動伸展,一路向前流水般暢響,帶著正直善良和真誠的本性,感染著人們,影響著時代。此刻,曲終人散大幕低垂,我有幸遇到并伴隨董先生走過他人生最后的二十年,看星辰隕落,一片空蕩蕩……
我與董先生最后一次通電話,是他骨折入院的前一天下午。他打到我辦公室,我們像往常一樣聊天。我剛在《僑報周末》發(fā)表了《與吳天明導演在紐約拍戲》,于是我們談到電影,董先生還回憶他與著名導演謝晉的交往,說到高興處他像孩子一樣哈哈大笑,朗朗笑聲純凈得恍若天籟,讓我聯(lián)想到他那顆純粹的心靈。因為轉(zhuǎn)天他就骨折入院,我有理由相信這是他留給人間最后的暢笑,透過那扇熟悉的窗欞飛向藍天,化入空中。董先生的家離我辦公室不遠,地鐵三站地。不管那扇窗戶今后屬于誰,我依然會打此走過,回味與他一起度過的難忘時光。這里的一切都是熟悉的,門衛(wèi)大哥,黑森林蛋糕店的女侍,還有街角公交站等車的人們。只是少了您,董鼎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