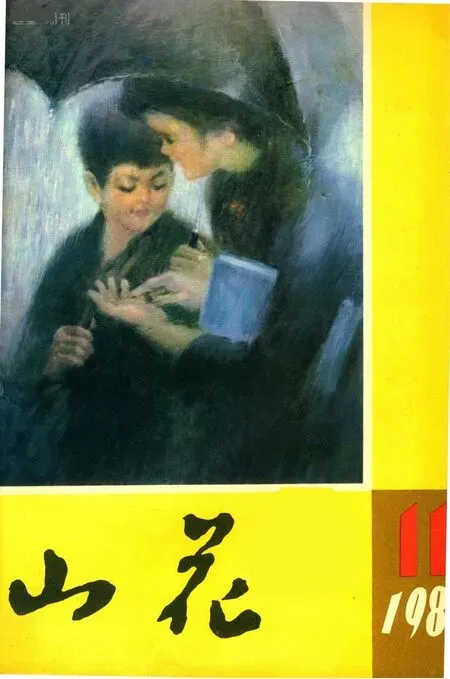散文二題
《玉樹臨風(fēng):品讀何士光》序
感謝朱軍先生寫下了這樣一些關(guān)于我的文字。我們今生今世來到這人世間,都和文字有一些因緣,并因了閱讀和寫作,也在我們之間結(jié)下了這樣一種因緣。如今年光漸漸地過去了,這時(shí)候就讓人不禁要回想,這樣的閱讀和寫作,都是為了些什么呢?
我們生而為人,就背負(fù)著這個(gè)生命,躑躅在年年歲歲的光陰中,沉浮在朝朝暮暮的日子里。每天每天,你固然要面對(duì)著生活,要讓自己能夠存活下去;在生活的后面,就還要面對(duì)著人生,要能夠?yàn)樽约旱纳钯x予一種意義;但在這生活和人生的后面,你始終面對(duì)著的,就還是這個(gè)生命,是這個(gè)生命和命運(yùn)之謎。所以你背負(fù)著的這生命就會(huì)追逼著你,讓你不得不去追尋這個(gè)生命和命運(yùn)的根柢。好比說,一個(gè)人在不知道真話的時(shí)候,就不會(huì)知道假話,你在不清楚這生命和命運(yùn)的真相的時(shí)候,你也就是不知道應(yīng)該拿這個(gè)生命去做些什么的。那么在這個(gè)紅塵滾滾的人世上,在這五光十色的寂寞和忙忙碌碌的荒涼之中,你就不知道該把自己怎么辦才好,不知道該怎樣以終老。佛法里說,文字是一種般若,我們因?yàn)楹臀淖钟羞@樣一點(diǎn)因緣,所以也就會(huì)在這樣的因緣之中,去追尋生命根柢,去求得自己的歸依。
有一種說法我們幾乎都不再懷疑,就是要活到老、學(xué)到老,書也要讀得越多越好。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要一直把書讀下去,至死也讀不完,那我們又還有什么希望可言呢?這生命不就注定了是絕望的?所以閱讀和寫作的實(shí)質(zhì),就應(yīng)該是一種不斷地?fù)P棄。書不能越讀越多,而是要越讀越少。好比把枝葉都撇開了,把泥土都掀開了,根柢就顯露出來了。
我們?cè)谶@里把生命比喻為一棵樹,那么我們的生活就好比是花朵,我們的人生就好比是枝條,而我們的生命則好比是根柢。如果我們總是在生活的花朵之間尋求,在人生的枝條之間比較,自然就會(huì)移步而換景,朝云而暮雨,這樣的燭照就是層出不窮的,我們的感觸、見解和主張也就像我們的卷帙一樣地浩繁了。但是換了一朵花朵,不也還是一朵花朵?換了一片枝葉?不也還是一片枝葉?這樣的忙碌,就不過是在同一個(gè)層級(jí)上不斷地重復(fù),都同樣的高,也一般的矮,要說一步也沒有前進(jìn),又何嘗前進(jìn)了一步?但凡感觸、見解和主張,就是可以任意選擇的,不斷更變的,乃至口是心非的。所以文學(xué)作為一種感觸,就是隨因緣而生滅的,是可有可無的;歷史作為一種真真假假的當(dāng)代史,就是可多可少的;而哲學(xué)作為一種思考,則人們一思考,上帝就發(fā)笑,因?yàn)槭澜绾蜕恼嫦嗖皇强梢钥克伎既?zhēng)辨的,而是要用體驗(yàn)或?qū)嶒?yàn)去證實(shí)的。所以佛門里就有一個(gè)專門的說法,把這一切稱為“不了義”。那么古往今來地,一個(gè)人若是在不斷地尋覓著,最終也就會(huì)從這樣的重復(fù)之中走出來,尋覓到宗教里去,這里說的即是尋覓到道家和佛家之中去。在這個(gè)卷帙浩繁的人世上,能夠?yàn)槲覀冎v說世界和生命的根柢的,就只有科學(xué)和宗教這樣兩個(gè)體系,而科學(xué)是一個(gè)還沒有完成的體系,道家和佛家則都是已經(jīng)完成了的千古不易的體系。
即以道家而言,正如科學(xué)后來用來觀測(cè)世界的模型,是一切復(fù)雜都源于簡(jiǎn)單一樣,道家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就已經(jīng)把世界和生命的模型表述為一二三和三二一。這里的一,就是道,就是如同科學(xué)后來所說的那種把這個(gè)世界化生出來的高密度的物質(zhì)。這里的二,就是有和無,也叫乾和坤,或者陰和陽,若是換成佛家的語義,便是色和空,再換成科學(xué)的語義,則是物質(zhì)和能量。至于三呢,便是包括我們的生命在內(nèi)的一切生命,是陰和陽的聚合體,是第三種“負(fù)陰而抱陽”的存在形態(tài)。可以說老子當(dāng)年在《道德經(jīng)》里,就已經(jīng)為我們把事情講完了。真理是樸素的,這就是“了義”。
那么,道在化生成了三以后,即是三生萬物以后,便化現(xiàn)在了萬物里。我們生而為人,是站在第三的層次上,便是可以從中去見道的,這也就是三二一,在三中見到二,在二中見到一。道家就把這叫做得一,佛家就把這叫做歸一。這就是凡此不二的,無可更改的,知行合一的。一個(gè)人若是得一歸一了,又會(huì)怎樣呢?也就能夠回到一和三的統(tǒng)一,即是道家所說的于無為之中又無不為,即是佛家所說的事事無礙,即是儒家所說的從心所欲而不逾矩,這時(shí)候一個(gè)人又才會(huì)從自為的而走向自在的。要仔細(xì)地?cái)⑹鲞@一切,自然還需要篇幅,這里就不說了,是為序。
去巢鳳寺聽磐聲
貴陽清鎮(zhèn)巢鳳寺,有一只天下無雙的磐。制磐的大師已經(jīng)遠(yuǎn)去了,留下來的磐聲便成了絕響,有緣者即能聽到。一聲磐響之后,便能夠讓人一直難忘,從此伴隨你一生的途程。
磐聲一響起來,便不僅在這個(gè)自然的世界里鳴響,也在你的心靈的世界里鳴響,明亮,精粹,空靈,久長(zhǎng),從有聲的鳴響,漸漸走向無聲的鳴響,直至大音稀聲,大象無形。
當(dāng)年佛陀曾經(jīng)問阿難,鐘聲響了,你聽見了嗎?阿難說聽見了。佛陀又問,如果鐘聲停了,你還能聽見嗎?阿難說聽不見了。佛陀接著又問,要是鐘聲又響起來了,你還能聽見嗎?阿難回答說,還能聽見。于是佛陀就告訴阿難說,這說明什么呢?這不就說明在你的身上,始終有一種能夠聽見的東西,一直在那兒存在著?這個(gè)始終在那兒的,不僅能夠看見聽見,而且還能夠思量和判斷的東西,自然不是別的什么,就是我們的心靈了。可見我們的心靈,本來是智慧、寧靜和圓滿的,是永恒的、終極的和金剛不壞的。至于聲音呢?乃至萬事萬物呢?則是隨著撞擊的因緣而生生滅滅的,你即使想留住它們,乃至更多更大更強(qiáng),便終究也是留不住的。
所以佛法教給我們的,就是要明白這心靈的本相,要保持這心靈的本相。而明白和保持這心靈的本相,自然不是說就空無所有了,而是說聲音來了,就任它來了,聲音走了,就任它走了。你不用去追逐它們,一追逐就煩惱叢生了。這樣的明白和保持,也就是明心見性,就是不離萬物、不住萬物,就是內(nèi)心如如不動(dòng),對(duì)事物則了了分明。如果能夠這樣的話,一個(gè)人也就從必然而走向了自由,從此便能夠常樂我凈了。
那么,到巢鳳寺的聽磐堂去聽一次磐聲吧。去聽一次聲音的生滅,明白了諸行無常,這是理上的事情。去跟蹤一次聲音遠(yuǎn)去的路程,讓這心靈和磐聲一道安靜下來,直至動(dòng)靜二相了然不生,直至回歸這心靈的清凈妙明的本相,然后再把這樣的心境移置到萬事萬物之中去,這便是事上的事情,便是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