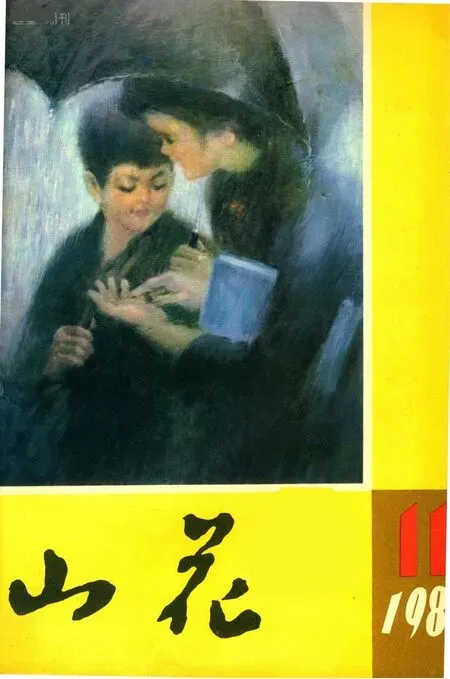“墮落干部”的進城故事
在建國初期的“十七年”小說中,城市的影子總是依稀可辨。那些影影綽綽的負面形象,其實深切照見彼時緊張的意識形態交鋒。比如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便通過一對革命夫婦的家庭悲喜劇,來突顯“革命之后”無產階級與城市的內在矛盾,以及由此衍生的“社會主義危機”,而在此之后,一系列相關作品亦通過講述“墮落干部”的進城故事,試圖不斷涉及社會主義新中國與城市的復雜聯系。
與《我們夫婦之間》相似,俞林的《我和我的妻子》(《新觀察》1956年第11期)同樣將“進城”的矛盾焦點聚集在“家庭”和“夫婦之間”。在這個故事中,“我的妻子”是一位“剛從城市里來的女學生”,有著十足的小資產階級情調,革命對她的吸引僅僅在于“很有意思”。當“我們”一同從革命年代走過之后,在我的“官僚主義”和“私心”的照顧下,她終于“丟掉做醫生的前途”,開始進入平庸的城市日常生活。于是,家庭生活與革命熱情之間的矛盾開始突顯,平庸生活的苦悶開始蔓延。為了消除這種苦悶,“她要在業余時間向機關里的一個干部學彈吉他”,由此而走向腐敗墮落的境地。
從表面上看,“我的妻子”與《我們夫婦之間》中的“李克”比較相似,都是“返城”的知識分子革命者,而且故事本身也是在反省“我”的“官僚主義”和“妻子”進城以后的“變質”,然而此處問題的關鍵卻在于“告別革命”所造成的日常生活的“瓦解”。我的官僚主義在于“不關心自己的妻子”,“不從政治上幫助她”,使“她越來越不像一個從老區來的干部”,而“她”則遭受著資產階級文化——“彈吉他”的致命吸引。這里不僅僅是一個“革命者”進城之后的“日常生活”的焦慮,以及“娜拉走后怎樣”的女性主體性建構的問題,更是一個無產階級文化的“匱乏狀態”和資產階級文化“致命吸引”的問題。這也許才是故事本身所暗示出的城市秘密所在。
面對“妻子”的墮落,“我”深情地回想起“那些曾一度在她身上閃耀過的光芒,體會到她那些曾有過的幻想和希望”,這無疑是革命年代的人性閃光。然而,如“我”所思索的,“為什么這些火花沒有燃燒成火焰就熄滅了呢?”果真如小說所闡述的,“是我把妻子當作自己的附屬品,把她放在身邊,不叫她學習,也不叫她工作。借口‘照顧’她,其實卻是為了自己有一個所謂‘溫暖’的家,讓妻子成為照顧這個家的主婦”嗎?或者,“正是我這種可恥的思想窒熄了她發出的火花,阻擋了她前進的道路”嗎?換句話說,是“政治生活”的缺位所引起的“學習”匱乏造成的后果嗎?事實恐怕并沒有那么簡單。就像小說所揭示的,“妻子”墮落的根源,即那位“彈吉他的干部”不出所料地“與私商勾結,貪污公款”,這是作者俞林為城市資產階級趣味所設置的“合理結局”。結合“三反”之中的斗爭背景,這種“政治無意識”的流露恰如其分地體現了意識形態的焦慮所在。小說最后,“我妻子后來到紡紗廠做工會工作,一開始很困難,但是她沒有退縮,她又恢復了從前的樣子,積極、熱情,很快就入了黨”。盡管這種與《我們夫婦之間》一樣的大團圓結局符合觀眾們善良的閱讀期待,也體現了作者試圖彌合“意識形態創傷”的努力,但社會主義城市在“資產階級趣味”的內在干擾中所呈現的分裂狀態卻是無法挽回的困局。
與《我們夫婦之間》及《我和我的妻子》比較相似,“山藥蛋派”小說家孫謙的作品《奇異的離婚故事》(《長江文藝》1956年第1期)也描寫了一個革命干部“進城”之后的墮落故事。小說主人公于樹德在“革命之后”的城市的所作所為,非常符合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所警惕的對象。進城之后,他不自覺地受到資產階級思想“毒素”的影響,“生活”上開始蛻化變質,不僅變得“愛穿戴,也愛玩兒,還愛跳舞”,而且追求一種“有‘無產階級的思想’,又有‘小資產階級的風度’”的價值取向。他熱衷于物質享受,沙發,小汽車,毛料子制服,喜歡到著名的工商業城市出差,有著十足的官僚主義做派,他的“反省丸”和“自我檢查丹”蒙蔽了許多人。他愛上了“梳著兩條長辮兒的大學生陳佐琴”,每天“坐著小汽車逛公園”,開始嫌棄自己鄉下的“黃臉婆”,并醞釀著與她離婚。
小說的中心情節就是圍繞于樹德“拋棄妻子”的故事展開的,而在孫謙這位農民小說家道德化的書寫之中,于樹德毫無意外地被塑造為一個“當代陳世美”的形象。與此相反,他眼中的“黃臉婆”妻子,那位曾經“臉兒紅紅的,一對大眼睛象是兩顆晶亮的星星”的“救命恩人”,則被塑造為任勞任怨,具有傳統美德的中國婦女。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這位“良心讓狗吃了”的負面道德型干部形象,是通過被敘述為倫理的敵人,從而被認定為階級敵人的。在此,于樹德這個“官僚主義者”是被依附在“拋棄妻子”的民間倫理的“冒犯者”之上的。就這樣,于樹德這位腐敗墮落,貪圖享受的官僚主義者,拋棄“糟糠之妻”的傳統倫理的“入侵者”,毫無意外地被塑造為階級的敵人,等待著被起訴和查辦的命運。這其實也透露出彼時意識形態對城市腐蝕作用的警惕。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于樹德雖然是一位革命者,從戰爭年代走過,但他是“在城市里讀過中學,又在他父親的店鋪學過買賣——有一些城市經驗”,由此而被調到城市去工作的。因此,他與《我們夫婦之間》中的“李克”非常相似,都是作為“返城者”重回城市的。而他本人進城當官后的墮落,也鮮明地體現出“城市經驗”作為一種負面所指的意義。“生活中確實有這種荒誕的事情!”《奇異的離婚故事》的結尾意味深長,也毫無疑問地包含著某種現實主義的批判意味。盡管它順應了“雙百”時期“反官僚主義”的歷史潮流,但至關重要的卻是揭示了城市對于“革命之后”的社會主義政治空間的腐蝕作用。
在“進城者”的眼中,“革命之后”的社會主義城市是一片“解放”的天堂,而社會主義清教徒式的文化匱乏狀態卻終究難敵幽靈般殘存的資本主義文化,這也是解放所呼喚出的“個人”的病癥所在。鄧友梅的《在懸崖上》(《文學月刊》1956年第9期)也是討論“革命之后”城市夫妻關系問題。這篇小說的主人公不再是昔日的革命者和進城干部,而是一位暗示出負面形象的工地技術員、小資產階級青年。于是在他這里,這種“個人主義”與資產階級趣味更加肆無忌憚,因此也極為曖昧地揭示出了城市的“美”、“自由”、“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等資產階級因素對“社會主義城市”的“誘惑”。小說之中,“我”在妻子(“革命伴侶”)與情人,即藝術學院畢業的雕塑師加利亞(資產階級女青年)之間的情感抉擇,被暗示為實用大方與華麗外表兩種不同美學風范的對峙。當然最終的結局無疑是社會主義理想的勝利,但在此意識形態的教益之中,“情感”與“詩意”的吸引終究令人心醉。《在懸崖上》有一段經典的段落,講述“星期六的機關舞會”,“我”和愛人,以及加麗亞相逢在舞場:“我真后悔,不該把她帶到這里來現眼。”“糟糠之妻”令他自慚形穢,這無疑象征著社會主義美學在資產階級面前的自卑形態。緊接著小說描述了“我”和加麗亞酣暢淋漓的舞蹈:“音樂一響,我倆就旋風似的轉過了整個大廳,人們那贊賞的眼光緊追著我倆閃來閃去。加麗亞得意地說:‘我好久沒這么高興過了,跳舞本身是愉快的,被人欣賞也是愉快的’。”這種“個人”陶醉于資本主義文化的欣快感,以及城市的“詩意”與“趣味”,終究是追求道德精神的社會主義所無法提供的,于是“墮落”便顯得不可避免。
在此頗有意味的是,從《我們夫婦之間》到《在懸崖上》,小說都不約而同地寫到了“機關舞會”。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城市的大眾娛樂方式,“機關舞會”被認為是對1930年代營業性舞廳的“重塑”。從四十年代的“延安交誼舞”到建國初期的“機關舞會”,“舞蹈”尤其是“交誼舞”,作為一種資產階級城市娛樂方式,出人意料地被社會主義文化所吸收和改進。這體現了社會主義文化在一種節制的原則中對“身體解放”的認同和對欲望放縱的警惕。然而,就是“機關舞會”這種意識形態規訓下某種“潔凈”的大眾娛樂方式,也在建國初的城市題材小說中釀成了苦果。無論是《我們夫婦之間》中的“李克”,還是《在懸崖上》中的“我”,更別說《上海的早晨》中那位迷戀“機關舞會”的“張科長”,都是在物質欲望的沉迷中沖決了身體解放的適度原則,從而演變為精神墮落的骯臟后果。這種情節設置的原則,已然體現出“機關舞會”這一社會主義城市文化形式的破產跡象。
這其實也體現出“進城”的無產階級政權,不斷面臨一種文化抗爭的命運。城市給家庭帶來的變故,感情危機背后蘊含的意識形態危機,這些都顯示出無產階級文化的匱乏狀態,它似乎難以抵擋資產階級文化的吸引,而資產階級文化的載體便是“革命之后”的城市。《乘風破浪》中的“進城工人”李少祥,面臨著在鄉下姑娘小蘭和上海姑娘小劉之間的情感抉擇。盡管最后,小說在一種無產階級勞動美學的價值評判中選擇了小蘭,但李少祥的“延宕”本身無意間透露出“小劉”這一有文化又有著“摩登”意味的資產階級女子對他的吸引。而在《霓虹燈下的哨兵中》,盡管排長陳喜最后在指導員的教育下幡然悔悟,但他對“春妮兒”的堅守,毋寧說只是對解放區人民的道德承諾,而社會主義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賴這種道德的“超我”結構得以維系的。
在“進城”的故事中,面對城市的誘惑,道德蛻變者往往與政治蛻變者有著驚人的同構關系,這也是城市官僚主義的由來。他們的形象在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劉賓雁的《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以及杜鵬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中有著清晰的呈現。如果說草明《火車頭》中劉國梁的“官僚主義”被認為是照搬農村經驗到城市來的“保守”與“狹隘”,那么劉世吾、羅立正和梁建等人則是“革命之后”安享“和平日子”的落伍者和墮落者。盡管劉世吾這位革命年代的英雄,從戰場和農村來到城市和組織部,作為“經驗豐富”,“心地單純”的“布爾什維克”,并不能簡單地被看成一個官僚主義者,但他的“世故”、“冷漠”,以及安于現狀的“逃避哲學”,卻終究體現出官僚體制中策略性的自我保護,這無疑是與革命理想背道而馳的。而《在和平的日子里》中的梁建作為一個坐享和平的建設者,他絲毫沒有意識到“和平日子”蘊含的嚴峻危機。他的問題在于將過去“忘光”,忘卻了自己作為一位革命者從失敗走向勝利的艱辛,他“要能把經過的一切事情都忘光,好像那些事情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要不,人就永遠不能安然地過日子!”“安然”一詞讓人想到了張愛玲對人生“安穩”的追求,這種日常生活的邏輯幾乎就是城市的秘密,卻是革命的大敵,也是革命者從鄉村走向城市的危機所在。小說中通過對梁建革命史的回顧,從而引出了一個“革命之后”的“蛻變”的問題,正如韋珍所說,“一個人只有在自己沒有飯吃、沒有出路、活不下去的時候,才有奮不顧身的革命勁頭?等到他不愁吃穿了,生活環境安逸了,他聽不見生活在怎樣呼喚社會主義?他的生命就失去動力?這樣的人,能算真正的革命者?”在此,城市一方面作為現代文明對于傳統農耕文化具有消解作用,另一方面,城市作為資本主義產物對于革命所建構的無產階級政權卻具有腐蝕作用。
作者簡介:
徐剛,1981年生,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