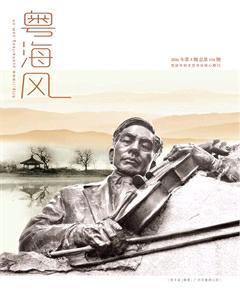讓“民間”回到民間
譚運長
對于廣東的文藝家與文化人而言,“民間”這個詞的含義,大概是無需特別說明的。這塊土地由于長期遠離中原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人們對于那種堂而皇之的所謂經(jīng)典文化,似乎并不特別熱衷,而心目中真正關注的,恰恰就是老百姓的生產(chǎn)與生活。人們不愿作許多無謂的打算,只愿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紅紅火火、美輪美奐。這,就生發(fā)出了異常宏富的民間文化寶藏。許多有為的藝術家,就從這些寶藏中,吸取無盡的營養(yǎng),由此成就了自己嚴肅、高尚,到今天已經(jīng)堪稱經(jīng)典的藝術。例如,今天人們在談論廣東的藝術時,一般總要提及廣東音樂,廣東音樂最為原始的形式,就是從酒樓、茶肆的小調(diào)以及民間婚喪嫁娶的音樂中脫胎而來的。而在廣東當代一批最著名的美術家之中,來自潮汕地區(qū)的畫家,是一個引人矚目的群體。他們的藝術營養(yǎng)是從何而來的呢?如果你拿這個問題去訪問林墉、林豐俗,去訪問方楚雄、許欽松以及其他知名或不知名的畫家,甚至別的藝術門類的藝術家,他們大概都會有一個共同的答案:來自潮汕民間的工藝美術傳統(tǒng)。在粵東大地上,幾乎每一個普通百姓都是生活藝術家,他們總會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異常精致、美麗、生動、豐富。這里的工匠,例如木匠、石匠、油漆匠、泥水匠,從來就是把自己的手藝活當作最嚴肅的藝術來追求的,真所謂是精雕細刻,精益求精,所以這里才有那么富麗堂皇、精巧繁復的木雕、石雕、漆畫、潮繡等等令人目不暇給的工藝美術。正是由于有著這樣一種民俗文化的根,潮汕藝術家從事自己的藝術活動的時候,總是那么從容不迫,比別人少了許多浮躁氣。另一方面,他們的作品從不深奧,總是充滿了某種人間煙火味。他們也從不把自己看成是高高在上的“藝術家”,他們把自己的藝術看成是一門手藝,而其本人,不過就是一個“會畫畫的大叔”。在潮汕人那里,生活的藝術化和藝術的生活化,是一個最明顯的文化標記。
有人說“廣東文化在民間”,這話顯然是有道理的。這不僅是說,這里存在著異常宏富的民間文藝、民俗文化的寶藏,而且更重要的,是這里的嚴肅文化、經(jīng)典文化,甚至是主旋律的廟堂文化,大多數(shù)情形下都是從民間文化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而正因為有了這種來自民間的源頭活水,他們的藝術顯得自然、生動,發(fā)育得較為健康。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平常所說的民間文化,并不僅僅是指那種歷史遺存,來自民間的文化創(chuàng)造力,可以說一刻也沒有停止。“民間”這個詞,其時態(tài)不是過去時,而是正在進行時。民間任何時候都在創(chuàng)造新的文化,而且,這種民間的創(chuàng)造,依然在為當下成熟的經(jīng)典文化藝術,提供無盡的營養(yǎng)。
保護民間文藝與民俗文化的真正有效的力量,還是在民間。以各種名義,所進行的保護,實際上常常都是一種發(fā)掘、利用,對其破壞性必須要有充分的意識。只有民間,才能以其獨有的經(jīng)驗,真正理解“民間”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