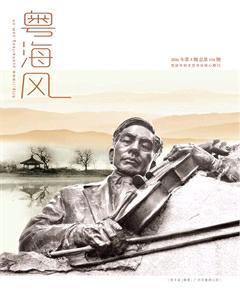文學研究的大數(shù)據(jù)與小時代
傅修海
隨著科學技術、尤其是互聯(lián)網技術的發(fā)展,人類、世界乃至宇宙的觀念已經縮微為人所眾知的思維背景和知識參照。對于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而言,現(xiàn)代化、全球化不再是撲面而來的壓力,網絡自然也不再僅僅是技術,它們都已經成了我們日常生活中朝夕以對的事實。國界、種族與地域的隔閡,已經不再是人們思考問題的邊界,無數(shù)的事情、無數(shù)的人都與我們每個人休戚相關,人類意識和世界愿景正成為人們普遍性的交流前提。
可以說,基于技術變革的網絡、基于經濟發(fā)展的全球化和現(xiàn)代化、基于人類與宇宙意識的人生與日常,這是當今世界的日常生活與宏大背景,這也是當下文學置身其間而非側身其間的語境與情境。
一、當下的文學格局
白燁先生認為當今中國是“以文學期刊為主導的傳統(tǒng)純文學,以商業(yè)出版為依托的大眾文學,以網絡媒介為平臺的新媒體文學”三分天下(白燁:《“三分天下”:當代文壇的結構性變化》,《文匯報》2009年11月1日)。此后,王曉明先生又提出當今文學“六分天下”一說(王曉明:《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國文學》,《文學評論》2011年第5期)。
事實上,如果不太計較出版介質的差異,不強求劃撥在其后面借文學討生活的人群之間的差異,無論是“三分天下”還是“六分天下”,實際上也就是紙上與網上的二元格局。而紙上與網上并非水火不相容、老死不相往來。只要有利益和需要,兩者之間的轉化可謂分分鐘的事情。
文學創(chuàng)作和出版既然尚且如此,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也概莫能外。歸根結底,不是文學變了,是人的處境變了。人的處境變了,人類精神產物的文學焉能不變?作為技術的互聯(lián)網與作為藝術的文學,以及作為專業(yè)或職業(yè)的人文學術研究,皆可謂歡喜冤家,個中原因都始“隱”于人,也必然要終“秀”于文。
因此,基于互聯(lián)網技術跨越發(fā)展導致的大數(shù)據(jù)分析,基于全球化視野下的人類普遍意識高漲的小時代來臨,文學研究的旨趣毫無疑問應該是人類之學,文學研究面對與思考的應該是人類、乃至任何生命之間普遍的困境、希望與同情。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此一說法在大數(shù)據(jù)和小時代的應有之義,必然是討論在人類普遍狀況下可以共同討論和通約思考的問題,是放觀天下,而不是停留屁股決定腦袋、在啦啦隊層面上的“唱衰”還是“唱盛”。
二、大數(shù)據(jù)視野下的文學研究
技術變革既然會改變人類的處境,技術當然能、也會影響乃至改變藝術和學術的格局,這是毋庸置疑的科技史、藝術史和學術史常識。因此,網絡技術變革帶來的“大數(shù)據(jù)”(Matthew L.Jockers:Macroanalysis:Digital Methods and Literary History,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3.4),全球化和人類意識的高漲,無疑也必然在改變著文學研究。
但大數(shù)據(jù)總歸是數(shù)據(jù),它源于電腦技術和程序的統(tǒng)計,其前提和結果都是選擇和有限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小時代,終歸目前還受制著國家、種族等疆域的區(qū)隔,它的前提是每個人更為真實和日常的地方生活。文學及其研究的價值,終究是走向個性的,當然也是基于一些人類普遍共識的個性。所以,大數(shù)據(jù)和小時代格局下的文學研究,立足點和落腳點,應該是在場的文學研究,起碼是有在場感的文學研究。
一言以蔽之,大數(shù)據(jù)與小時代的文學研究,它的價值恰恰不在于數(shù)據(jù)和時代本身,而是在數(shù)據(jù)的大氣象和深處,在時代的細部和小處。用魯迅的話說,革命低潮時期才有革命文學。網絡發(fā)達了,不等于網絡文學就發(fā)達了;報紙雜志多、小說出版多,并不等于文學及其學術就處在最好的時候。道理很簡單,這正如錢多了并不等于就是幸福來敲門。
顯然,在大數(shù)據(jù)的覆巢之下,任何研究都無法巋然不動。以文學研究而論,記憶能力和知識儲備,長期以來是制勝法寶。然而,在大數(shù)據(jù)的互聯(lián)網云技術的視域下,這種傳統(tǒng)學術研究中所追求的超常記憶和超大記憶,較之當下的信息技術平臺而言,在數(shù)量上都早已經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如果說,在以往的學術語境下,兩腳書櫥仍有可圈可點之處,那么在大數(shù)據(jù)背景下,這種圈點的價值和意義顯然被嚴重縮水。珍稀史料的價值和意義也一樣,這種由于人為秘藏而導致的學術能量不可能再風光如前。眾所周知的文獻數(shù)位化進程及其運用,已經使得很多靠珍本秘藏來獲取學術高位的研究,變得不再那么令人高山仰止。香港中文大學和臺灣政治大學共同研發(fā)的那套關于思想史文獻的數(shù)據(jù)庫,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依托海量的數(shù)據(jù)庫檢索得出的相關研究,其結論仍舊要保持謹慎的樂觀。原因很簡單,任何檢索都無非是根據(jù)有限的“關鍵詞”和機械的電腦識別技術得出的。
因于此,基于量的統(tǒng)計和分析的文學研究,事實上如果沒有個人情感投射與歷史情境分析的折沖,并不能算得上是多么高明的研究。借助大數(shù)據(jù)的技術,人們可以迅速在宏觀層面上去體味和觀察以往僅憑個人之力不可想象的歷史粗面孔。但另一方面,當我們看到許多文學研究一上來就援引各類數(shù)據(jù)庫統(tǒng)計時,對其結論和邏輯,顯然也必須要有一定的警惕和限度,因為那相當程度是與網速和處理器有關。關于這一點,可進一步參見金雯、李繩的《“大數(shù)據(jù)”分析與文學研究》(《中國圖書評論》2014年第4期)。
三、小時代里的文學研究何為?
誠然,既然有大數(shù)據(jù)的江河濤濤,就必然會有小時代的支離破碎。而且,在小時代的支離面前,任何研究也都會感到時勢的艱難。文學研究也概莫能外,所謂大話好說,細活難工。
進一步而言,從一定意義上說,文學研究面對的都是個案。然而,在全球化和人類普遍意識高漲之前,民族、國家和地域的宏大敘事比較容易形成,而且于個體和群體的沖擊力都甚大。長期以來,只要事關民族與國家,必然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潮流,人們往往也都能將諸多因果概而言之為是大時代、激流所致。
瞿秋白有句名言“時代的電流使人禁不起了”(瞿秋白:《致郭沫若》),這種電流之感,想必是很多從大時代里走過來的人的通識和揪心記憶。大時代的文學研究,自然也就得了很多的乘勢之便,與滾滾洪流同構的文學研究中,不僅有許多激蕩人心的廣場呼吁,隨波逐流的解釋和喧囂也往往是這類研究的共同面相。
然而,在互聯(lián)網技術高度發(fā)展,全球化和現(xiàn)代化程度已經蔚為常識的情境下,時代之大相較于宇宙之浩瀚而言,個體感受的迅疾、疏離反而變得更為真切。全球化已經是眼前分分秒秒的事情,個人好比互聯(lián)網上的小飛蛾,時代也反而愈發(fā)顯現(xiàn)出它的支離破碎。知音之慨轉瞬之間純粹起來,昔有高山流水的偶遇,今天多在網上尋尋覓覓,都與時代看似毫不相關。文學研究亦然。
毫無疑問,小時代里從事文學研究的宏大觀察,在大數(shù)據(jù)的縱橫捭闔面前,研究者的視域遠遠不及憑借網絡時代以數(shù)據(jù)最大限度的統(tǒng)計與分析來得直觀而富有科學色彩。文學研究之于個人的努力和探討天地,正是統(tǒng)計技術和數(shù)理分析層面無法抵達的文學細部,其間有文本體驗與個人情感探究,更有歷史現(xiàn)場與記憶的疏離比對、深度洞察。而對藝術創(chuàng)作的現(xiàn)場感、文本活動的在場感和文本經典化的歷史感的多層復合與還原,恰恰是目前信息技術與機器原理尚且無法與人類鮮活心靈同構的地方。
四、技術、藝術與學術:邊界的消融與凸顯
大數(shù)據(jù)與小時代下的文學,都不約而同地指向著個案與個性,追尋著獨創(chuàng)與質感,強調著場域與個體精神的歷史遇合與深度闡釋。當然這并非說宏觀宏大的不重要或者不見了,而是技術變革導致人的處境變了,以往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從事的宏觀體察和數(shù)據(jù)概括,網絡信息技術已經確確實實可以幫上大忙。
既然如此,人無疑應該也可以借重技術,從而把更多的寶貴精力投注于個性與個案的開創(chuàng)與發(fā)凡,關注人類普遍的困境、期待與幸福,勘探人類心靈的深處與細部,而不是挾技術自重乃至自炫,那樣只能顯出人類的機心與懶笨來。具體到文學研究來說,大數(shù)據(jù)能夠讓我們盡可能多而廣地接觸和識見材料,這自然可以幫助打開視界,敞開視域,甚至因此擁有更多重和更多元的學術權衡,乃至是如光譜分析一般的數(shù)量和層面上的掃描與分析。
與此同時,數(shù)據(jù)之大終有邊界,數(shù)理分析的精確也必須有相對而設的公約數(shù)或常態(tài)圖標的參照,其前提都基于一定數(shù)量的取樣。況且,人力本身的有限性較之電腦而言,其本身就是科學技術發(fā)展極為有限的參照和前提。文學研究倘若一味身陷于數(shù)量的比照,對于人類自身的體察和反觀將會變得極為有限和干枯,甚至墮入非人類的無聊。
總而言之,文學研究所面對的多是個案。在大數(shù)據(jù)和小時代的格局下,文學研究感性的、文本差異的、個人體驗的、風格的東西,無疑應該變得更加突出和顯要。尤其是研究者對文本個性的個人而普遍化的人類理解與同情,應該也必須變得更為重要。只有這樣,大數(shù)據(jù)、互聯(lián)網等才不僅僅是技術,而應是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世道人心的一面鏡子、一扇窗和一座高臺。小時代也不再被視為個體困窘與無助的精神象征,而是人類普遍心靈在時空距離張力下的反思、相望與相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