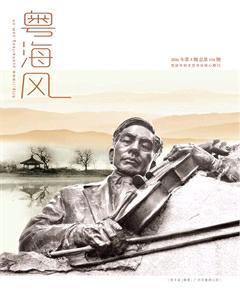“鬼臉時(shí)代”的臺(tái)灣文學(xué)生態(tài)
古遠(yuǎn)清
一位自稱(chēng)“臺(tái)灣之子”的政客擔(dān)任“總統(tǒng)”期間在接受德國(guó)《明鏡》月刊訪問(wèn)時(shí),承認(rèn)祖先來(lái)自中國(guó)福建省,并以身為“華人”為榮。誰(shuí)知德文報(bào)導(dǎo)再譯回中文時(shí),“華人”變成了“中國(guó)人”,令這位政客十分難堪。他這種變臉行為事與愿違,戲劇家馬森認(rèn)為有點(diǎn)像演荒謬劇,不能不使人感到霧煞煞。[1]
“霧煞煞”的另一表現(xiàn)是少數(shù)臺(tái)灣基本教義派自制了所謂“臺(tái)灣國(guó)護(hù)照”。這個(gè)“護(hù)照”其實(shí)是一張小紙片,貼在“中華民國(guó)護(hù)照”上。這些人天真地認(rèn)為建立新國(guó)家可以不費(fèi)吹灰之力,只用“扮鬼臉”貼一張小紙條,“臺(tái)灣獨(dú)立建國(guó)”就馬到成功。他們用這個(gè)所謂新護(hù)照在美國(guó)、新加坡闖關(guān)時(shí),海關(guān)人員便將這些“扮鬼臉”者扣壓,或留置,或訊問(wèn),甚至原機(jī)遣返。
如果說(shuō)自制所謂“臺(tái)灣國(guó)護(hù)照”屬個(gè)人行為,那“集體行為”表現(xiàn)在臺(tái)灣社會(huì)兩大政黨惡斗,政客們各懷鬼胎,對(duì)頭跟對(duì)手亂罵,江湖的毒誓一發(fā)再發(fā),陰間的菩薩跪個(gè)不停,美麗的謊話吹上了天,這充分意味著誠(chéng)信時(shí)代的結(jié)束,“霧煞煞”的現(xiàn)象使得駱以軍們感嘆:我們“都得生活在明目張膽的鬼臉之下”。
一
在臺(tái)灣,除《文訊》雜志2004年10—12月策劃過(guò)“臺(tái)灣文學(xué)新世紀(jì)”專(zhuān)輯外,鮮有“臺(tái)灣新世紀(jì)文學(xué)”的提法,而在中國(guó)內(nèi)地,“新世紀(jì)文學(xué)”成為各出版社出版系列叢書(shū)競(jìng)相打出的新旗號(hào),還成為各媒體討論的熱門(mén)話題。“大陸新世紀(jì)文學(xué)”更不似“臺(tái)灣新世紀(jì)文學(xué)”那樣有復(fù)雜的政治文學(xué)內(nèi)涵。如果說(shuō),20世紀(jì)光復(fù)后的臺(tái)灣文壇最重要的事件是“自由中國(guó)文壇”的建立與崩盤(pán),那“臺(tái)灣新世紀(jì)文學(xué)”最重要的價(jià)值取向是“中國(guó)臺(tái)灣文壇”幾乎不見(jiàn)蹤影,眾多作家不再堅(jiān)稱(chēng)或不愿稱(chēng)自己是中國(guó)人和中國(guó)作家。和90年代相比,批判性的多了,懺悔的少了;自由的多了,自律的少了;游戲之作多了,嚴(yán)肅之作少了;尤其是“中國(guó)作家”少了,“臺(tái)灣作家”多了;得獎(jiǎng)作品多了,經(jīng)得起時(shí)間篩選的名著少了;文學(xué)事件多了,作品的含金量少了。
與不愿稱(chēng)自己是中國(guó)人和中國(guó)作家的某些本土派相反,散文家、戲劇家張曉風(fēng)任何時(shí)候都堅(jiān)認(rèn)自己是中國(guó)人和中國(guó)作家,但這不等于說(shuō)她是政治的擁抱者,確切地說(shuō)是政客的批判者。在《報(bào)告總統(tǒng),我可以有兩片肺頁(yè)嗎?》中,她尖銳地攻訐那位登而輝之的變色龍執(zhí)政的12年,外加那位從“臺(tái)灣之子”變臉為“臺(tái)灣之恥”的一位政客所統(tǒng)治的8年:
20年來(lái),總統(tǒng)一職竟跟強(qiáng)盜成了同行。
這種說(shuō)法太夸張,真有“語(yǔ)不驚人死不休”的味道。盡管這樣,為了反對(duì)環(huán)境污染,為“202兵工廠”請(qǐng)命,張曉風(fēng)還向另一位藍(lán)色“總統(tǒng)”下跪,以至被媒體稱(chēng)之為“驚天一跪”。至于有些著名作家參選“立法委員”,或幫某位“總統(tǒng)”“立法委員”候選人站臺(tái)拜票,或?yàn)樗麄儗?xiě)文宣廣告,更是家常便飯。
鑒于亂象叢生的新世紀(jì)文壇出現(xiàn)了這種新質(zhì):不少作家狂熱地?fù)肀д危瑹嶂杂谒囄臑檎畏?wù),為選戰(zhàn)服務(wù),用形象的說(shuō)法是“用政治天線接受文學(xué)頻道”。也有作家對(duì)此很不以為然,不贊成這種政治與文學(xué)聯(lián)姻的做法。他們認(rèn)為臺(tái)灣文學(xué)雖然從來(lái)沒(méi)有離開(kāi)政治,用意識(shí)形態(tài)的天線去衡量也沒(méi)有錯(cuò),但創(chuàng)作臺(tái)灣文學(xué)畢竟不能只用政治天線,還應(yīng)該有審美天線、語(yǔ)言天線。這又重復(fù)了70年代臺(tái)灣文壇的兩種爭(zhēng)論:是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還是為社會(huì)而藝術(shù)?很多人不認(rèn)同把文學(xué)作為選戰(zhàn)的工具,但作家畢竟不能脫離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既然充滿矛盾和不公不義,有良心和正義感的知識(shí)分子當(dāng)然不能局限在象牙塔里,特殊情況下還要與政治同行。尤其是臺(tái)灣現(xiàn)在分藍(lán)綠兩大派,敏感的詩(shī)人紛紛加入其中,如不久前發(fā)生的一位著名詩(shī)人奮起抗?fàn)帟r(shí)鋌而走險(xiǎn),所演岀的是一出震驚全島的“行為藝術(shù)”。
詩(shī)人的社會(huì)關(guān)懷原本表現(xiàn)在國(guó)家定位、社會(huì)發(fā)展、經(jīng)濟(jì)建設(shè)、民主法制、文化教育等各個(gè)方面。當(dāng)他們感到面對(duì)強(qiáng)權(quán)作家顯得渺小,詩(shī)歌變革社會(huì)的功能是如此的脆弱時(shí),他們會(huì)以詩(shī)外的“搞怪”方式去參加反強(qiáng)權(quán)、反貪腐的活動(dòng)。猶記得2005年秋天,這位臺(tái)北詩(shī)人將嘹亮鏗鏘的詩(shī)性抗議話語(yǔ)變質(zhì)為躁郁的語(yǔ)言暴力。他以子虛烏有的“臺(tái)灣解放聯(lián)盟”名義“拍”電話威脅一位被高捷弊案盯得滿頭皰的綠營(yíng)天王。這場(chǎng)“詩(shī)人”造反風(fēng)波鬧得全島沸沸揚(yáng)揚(yáng)。就憑這荒腔走板之“詩(shī)聲”,詩(shī)人一夜之間上了全島報(bào)紙的頭條。對(duì)這一事件,不同營(yíng)壘的詩(shī)人反應(yīng)截然不同。如某綠營(yíng)的作家認(rèn)為:打匿名的恐嚇電話這一行為“是黑暗的。政治人物當(dāng)然可以批評(píng),但躲在暗處的語(yǔ)言暴力并非‘詩(shī)人作為,而毋寧是他的‘病人行為……”,而為其辯護(hù)者則認(rèn)為,不是詩(shī)人病了,而是社會(huì)病了;不是詩(shī)人瘋了,而是“天天制造問(wèn)題,天天制造謊言,逼著詩(shī)人傷痛”的政客瘋了。白靈卻以有這樣的血性朋友而自豪,他說(shuō):這位冒著腦袋被敲碎危險(xiǎn)的詩(shī)人“吐出一句血,那是他一生最紅的詩(shī)”。另一位有“詩(shī)儒”之稱(chēng)的老詩(shī)人向明,早在《詩(shī)的記憶》[2]中就預(yù)見(jiàn)過(guò):
這現(xiàn)實(shí)唯搞怪是崇
唯正常是病
唯丑陋是偶像
本來(lái),新世紀(jì)的臺(tái)灣是一個(gè)“鬼臉的時(shí)代”,君不見(jiàn)那選舉的鞭炮聲和喇叭聲破壞了寧?kù)o的氣氛,政客們又千方百計(jì)破壞言論自由,因而惹得一向?yàn)t灑的詩(shī)人也扮“鬼臉”,一向自由的詩(shī)人也瘋狂。不過(guò),雖然同情這位“造反”詩(shī)人的馬森,并不贊成這種恐嚇?biāo)说慕趿髅サ男袨閇3]。
在新世紀(jì),以本土作家為主要研究對(duì)象的學(xué)報(bào)和評(píng)論刊物接連創(chuàng)刊。臺(tái)灣文學(xué)史書(shū)寫(xiě)中的國(guó)族認(rèn)同問(wèn)題更引發(fā)激烈爭(zhēng)辯,典型的有世紀(jì)初發(fā)生的以陳芳明、陳映真為主角的“雙陳大戰(zhàn)”。
撰寫(xiě)《臺(tái)灣文學(xué)史》,被稱(chēng)為“一項(xiàng)何等迷人卻又何等危險(xiǎn)的任務(wù)”[4]。這里講的“迷人”,是因?yàn)樵诟吆啊芭_(tái)灣文學(xué)國(guó)家化”的臺(tái)灣,文學(xué)研究遠(yuǎn)遠(yuǎn)跟不上本土化的趨勢(shì),至2011年前還未出版過(guò)一本嚴(yán)格意義上的《臺(tái)灣文學(xué)史》。要是有誰(shuí)寫(xiě)出來(lái)了,就可落得一頂“開(kāi)創(chuàng)者、奠基者”的桂冠。之所以“危險(xiǎn)”,是因?yàn)樵凇杜_(tái)灣文學(xué)史》編寫(xiě)中,充滿了統(tǒng)、獨(dú)之爭(zhēng)。有人眼看大陸學(xué)者撰寫(xiě)了一部部厚厚的《臺(tái)灣文學(xué)史》及其分類(lèi)史登陸彼岸,便下決心自己寫(xiě)一本所謂“雄性”的“臺(tái)灣文學(xué)史”,這樣就有了以“臺(tái)灣意識(shí)”重新建構(gòu)的《臺(tái)灣新文學(xué)史》[5]。
這部“新文學(xué)史”在開(kāi)宗明義的第一章《臺(tái)灣新文學(xué)史的建構(gòu)與分期》中,亮出“后殖民史觀”的旗幟,認(rèn)為臺(tái)灣屬殖民地社會(huì),其第一時(shí)期為1895—1945年的日本帝國(guó)主義的統(tǒng)治時(shí)期。第二時(shí)期為1945—1987年,從國(guó)民政府接收臺(tái)灣到國(guó)民黨當(dāng)局宣布解除“戒嚴(yán)”,屬“再殖民時(shí)期”。這一時(shí)期和前一階段一樣,中國(guó)社會(huì)與臺(tái)灣社會(huì)再度產(chǎn)生了嚴(yán)重分離。第三時(shí)期為“后殖民時(shí)期”,即1987年7月“解嚴(yán)”之后。其中民進(jìn)黨于1986年建立,這是臺(tái)灣脫離中國(guó)的“復(fù)權(quán)”的一個(gè)重要標(biāo)志。這種“理論”,與李登輝講的國(guó)民黨是“外來(lái)政權(quán)”可謂異曲同工。陳芳明把中國(guó)與日本侵略者同等對(duì)待,離開(kāi)文學(xué)大講“復(fù)權(quán)”“復(fù)國(guó)”,因而受到以陳映真為代表的統(tǒng)派作家的反彈。
陳映真的文章題為《以意識(shí)形態(tài)代替科學(xué)知識(shí)的災(zāi)難》,發(fā)表在2000年7月號(hào)《聯(lián)合文學(xué)》上。面對(duì)陳映真對(duì)《臺(tái)灣新文學(xué)史的建構(gòu)與分期》的駁論,陳芳明迅捷地在同年8月號(hào)的《聯(lián)合文學(xué)》上發(fā)表《馬克思主義有那么嚴(yán)重嗎?》的反批評(píng)文章。有“戰(zhàn)神”[6]之稱(chēng)的陳映真不甘心自己所鐘愛(ài)和信仰的馬克思主義受辱,又在《聯(lián)合文學(xué)》同年9月號(hào)上發(fā)表《關(guān)于臺(tái)灣“社會(huì)性質(zhì)”的進(jìn)一步討論》,繼續(xù)批評(píng)陳芳明的“再殖民”言論。可惜當(dāng)《臺(tái)灣新文學(xué)史》問(wèn)世時(shí),陳映真因生病“失語(yǔ)”,使陳芳明不勝惆悵,失卻了一個(gè)恩怨情仇糾纏在一起的復(fù)雜記憶。
臺(tái)灣文壇之所以將這場(chǎng)從島內(nèi)燃燒到島外論爭(zhēng)稱(chēng)為“雙陳大戰(zhàn)”[7],是因?yàn)檫@兩位是臺(tái)灣知名度極高的作家、評(píng)論家,且他們均有不同的黨派背景。如陳芳明曾任民進(jìn)黨文宣部主任,陳映真曾任中國(guó)統(tǒng)一聯(lián)盟創(chuàng)會(huì)主席和勞工黨核心成員。即一個(gè)是獨(dú)派“理論家”,一位是統(tǒng)派的思想家。另一方面,他們的文章均長(zhǎng)達(dá)萬(wàn)言以上,其中陳映真的兩次反駁文章為3.4萬(wàn)和2.8萬(wàn)字。他們兩人的論爭(zhēng)發(fā)表在臺(tái)灣最大型的文學(xué)刊物上,還具有短兵相接的特點(diǎn)。這是進(jìn)入新千年后最具規(guī)模、影響極為深遠(yuǎn)的文壇上的路線之爭(zhēng),堪稱(chēng)新世紀(jì)統(tǒng)、獨(dú)兩派最豪華、最盛大的一場(chǎng)演出。
和70年代后期發(fā)生的鄉(xiāng)土文學(xué)大論戰(zhàn)一樣,這是一場(chǎng)以文學(xué)為名的意識(shí)形態(tài)前哨戰(zhàn)。在這“鬼臉時(shí)代”,“雙陳”當(dāng)然不可能去爭(zhēng)論臺(tái)灣文學(xué)史應(yīng)如何編寫(xiě)、如何分期這一類(lèi)的純學(xué)術(shù)問(wèn)題,而爭(zhēng)論的焦點(diǎn)集中在臺(tái)灣到底屬何種社會(huì)性質(zhì)、臺(tái)灣應(yīng)朝統(tǒng)一方向還是走臺(tái)獨(dú)路線這類(lèi)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問(wèn)題。
在世紀(jì)交替之際,某些人對(duì)政治上的這類(lèi)大是大非問(wèn)題毫無(wú)興趣,在精神上卻始終無(wú)法擺脫從世紀(jì)末傳染來(lái)的頹廢情調(diào),致使自殺成為臺(tái)灣文壇的一個(gè)重要景觀。據(jù)報(bào)載,臺(tái)灣每?jī)尚r(shí)就有一人自殺身亡。僅作家而論,邱妙津于1995年在巴黎自殺后,2003年又有自縊身亡的黃國(guó)峻以及于2004年讓生命時(shí)鐘關(guān)閉的《FHM男人幫》雜志總編輯袁哲生。同一年,在詩(shī)作中對(duì)生命一再提出質(zhì)疑和抗議的女詩(shī)人葉紅在上海自殺。2005年,曾獲梁實(shí)秋文學(xué)獎(jiǎng)的新銳女作家黃宜君因憂郁癥病復(fù)發(fā)自縊身亡于花蓮,得年30歲。他們提前離開(kāi)這個(gè)令人煩擾的“鬼臉”式的塵世,給文學(xué)界帶來(lái)巨大的震動(dòng),促使人們重新審視已存的文壇秩序和作家生存的意義。
抱著對(duì)生存目的、意義的懷疑和終極價(jià)值的困惑,對(duì)自身發(fā)展前途的迷茫,過(guò)于頹廢、虛無(wú)的小說(shuō)家們無(wú)法抵抗死神的誘惑,由此走上不歸路。邱妙津這顆新星正是在這種生存虛無(wú)的黑暗底色中隕落的。她1991年畢業(yè)于臺(tái)灣大學(xué)心理學(xué)系,從大學(xué)一年級(jí)開(kāi)始創(chuàng)作,數(shù)次獲獎(jiǎng)。她生命的26年,是精華的集中展示,著有短、中、長(zhǎng)篇小說(shuō)多種。
充滿才華的小說(shuō)家消失后,人們依然思念小說(shuō)家才華的閃光。邱妙津?qū)懹凇肮砟槙r(shí)代”的《鬼的狂歡》,人物充滿了精神以及肉體的困惑:“這些人物各自有各自的難題要打發(fā),卻又因?yàn)檫@些難題的虛無(wú)性格誘使他們共同表現(xiàn)了某一世界觀——放棄了深情凝視世界的眼光,不了解也不妥協(xié)。”如《臨界點(diǎn)》的主人公因生理缺陷產(chǎn)生了極度自卑心理,而有時(shí)又將自卑心理轉(zhuǎn)變?yōu)檫^(guò)分的自尊,因而在與人交往時(shí)出現(xiàn)了異乎尋常的怪癖舉動(dòng)。這種人在狂歡與死亡中徘徊,典型地表現(xiàn)了“新人類(lèi)”極其矛盾的灰色心態(tài)。
陳映真曾批評(píng)20世紀(jì)80年代后期的臺(tái)灣青年奢靡、頹廢、虛無(wú),譴責(zé)他們完全背棄了老一輩的理想主義尊嚴(yán)。其實(shí),這種頹廢、虛無(wú),在60年代存在主義風(fēng)靡臺(tái)灣時(shí)就出現(xiàn)過(guò)。不過(guò),兩者有本質(zhì)的不同:“80年代后期開(kāi)始出現(xiàn)的‘新人類(lèi)現(xiàn)象與60年代的蒼白少年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是白色恐怖政制下社會(huì)氣氛低凝中,從外面移植進(jìn)來(lái)的無(wú)可奈何;而前者卻實(shí)實(shí)在在是臺(tái)灣社會(huì)財(cái)富累積沖倒了原有道德格局,不得不然的本土現(xiàn)象。”[8]另一不同之處是“新人類(lèi)”的作品帶有濃厚的“鬼臉”色彩。如邱妙津喜愛(ài)寫(xiě)夾帶情色的個(gè)人隱私,寫(xiě)用金錢(qián)換來(lái)的官能刺激。她尤其喜好描寫(xiě)同性戀題材,在表現(xiàn)大學(xué)校園和同性酒吧中女男同志結(jié)盟時(shí)大膽展示裸體,流露出對(duì)女同志身份的絕望之情。
在輕生厭世的作家觀念中,死亡是現(xiàn)存的一種無(wú)可取代的最后可能性。和西方詩(shī)人里爾克、荷爾德林一樣,出生于小說(shuō)世家的黃國(guó)峻,從世紀(jì)末開(kāi)始就被死亡的恒久而巨大的陰影所籠罩。他說(shuō)過(guò)一句名言:“時(shí)間如此真實(shí),真實(shí)如此短暫。”他只活了34歲,可留下的作品不少,僅短篇小說(shuō)集就有三種,另還有來(lái)不及出版的長(zhǎng)篇《水門(mén)的洞口》。他的作品風(fēng)格,類(lèi)似 “翻譯體”,用詞造句不像其父黃春明那樣本土化。他眼中的“男島”“女島”中的情欲世界,與中華文明相悖,甚至在英美文化中也難見(jiàn)其蹤影。黃氏作品中的洋腔洋調(diào),據(jù)說(shuō)是為了“制造某種‘疏離的美學(xué)”[9],這種美學(xué)是臺(tái)灣文壇在世紀(jì)交替時(shí)極富探討價(jià)值的一種現(xiàn)象。
黃國(guó)峻生命之火猝然熄滅時(shí),袁哲生曾寫(xiě)過(guò)悼文《偏遠(yuǎn)的哭聲》[10]。想不到過(guò)了一年,以外省的第二代之姿挑戰(zhàn)河洛話鄉(xiāng)土?xí)鴮?xiě)的這位優(yōu)異小說(shuō)家,不再“留得春光過(guò)小年”[11]而接過(guò)黃國(guó)峻的“棒子”,又用自己的高貴生命去燭照生存的虛無(wú)。他的自殺再次昭示了生命的悲涼,同時(shí)意味著小說(shuō)家形象的永遠(yuǎn)完成。正因?yàn)樵谟邢薜臅r(shí)空里猝逝,所以這幾顆突然隕滅的耀眼之星,留給人們的將是永恒的思念。
與“鬼臉時(shí)代”的政治生態(tài)有關(guān)的是新世紀(jì)以來(lái)和“中國(guó)文學(xué)系”平行的“臺(tái)灣文學(xué)系”“臺(tái)灣文學(xué)研究所”在許多大學(xué)如雨后春筍誕生。可在幾十所大學(xué)“臺(tái)灣文學(xué)系”和“臺(tái)灣文學(xué)研究所”的碩士班和博士班中,由于“中國(guó)文學(xué)系”所帶來(lái)的“中國(guó)意識(shí)”在高校根深蒂固,“臺(tái)語(yǔ)”多數(shù)人視為中國(guó)內(nèi)地方言,故幾乎沒(méi)有一所大學(xué)加考 “臺(tái)灣母語(yǔ)”,研究所更不會(huì)考什么“臺(tái)灣語(yǔ)言”,使得一位本土人士感嘆:“‘臺(tái)文還是淪為‘中文的附庸,中文系的地盤(pán)。”怎么推毀也推毀不掉。這就難怪有學(xué)者說(shuō):“目前臺(tái)灣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一直是被‘非學(xué)術(shù)論述所壟斷。”[12]的確,臺(tái)灣文學(xué)系建立多了,有時(shí)會(huì)適得其反:比如大量的原中文系教師改行加入后,他們把中國(guó)文學(xué)帶到臺(tái)灣文學(xué)系教學(xué)中,或進(jìn)行潛移默化的滲透,使臺(tái)灣文學(xué)系未能達(dá)到臺(tái)灣文學(xué)與中國(guó)文學(xué)分離的目的。哪怕是某綠營(yíng)名人主持的某大學(xué)臺(tái)文所,獨(dú)尊漢語(yǔ)而不見(jiàn)臺(tái)語(yǔ),以致招來(lái)“制造臺(tái)灣文學(xué)生態(tài)災(zāi)難”[13]的批判。可見(jiàn)臺(tái)灣文學(xué)系、所,不僅充滿中國(guó)意識(shí)與臺(tái)灣意識(shí)的對(duì)立,而且淺綠與深綠派在如何看待臺(tái)灣文學(xué)用何種語(yǔ)言寫(xiě)作上,也是暗潮洶涌,鬧個(gè)不停,以至“轉(zhuǎn)系生一年比一年多,對(duì)臺(tái)文系出路不看好”,即使是被視為臺(tái)灣文學(xué)系重鎮(zhèn)的成功大學(xué),學(xué)生也抱怨學(xué)習(xí)4年沒(méi)有真正學(xué)到本領(lǐng),“讓我拿出來(lái)告訴所有人‘我讀成大臺(tái)文系的東西?” [14]
在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上,對(duì)臺(tái)灣因統(tǒng)、獨(dú)斗爭(zhēng)產(chǎn)生的政治亂象反映極得力的是黃凡。他在2003年出版的《躁郁的國(guó)家》,共有十三章,每章伊始,即有一生致力于反體制的黎耀南寫(xiě)給“總統(tǒng)”的信。這些信件涉及統(tǒng)獨(dú)斗爭(zhēng)、朝野爭(zhēng)斗、經(jīng)濟(jì)問(wèn)題、選舉不公、權(quán)力角逐。作品毫不諱言說(shuō)政客得了躁郁癥,此癥“傳染”給全社會(huì),因此整個(gè)“國(guó)家”成了躁郁之“國(guó)”,然后從躁郁走向瘋狂。這一預(yù)言已被后來(lái)的政黨輪替出現(xiàn)的黑金橫行、黃鐘毀棄、道德淪喪 等眾多奇詭現(xiàn)象所證實(shí)。黃凡的另一長(zhǎng)篇《大學(xué)之賊》,通過(guò)高等學(xué)府充滿人事權(quán)利斗爭(zhēng)的黑色喜劇,諷刺了當(dāng)今臺(tái)灣社會(huì)存在的種種問(wèn)題。
和黃凡的《躁郁的國(guó)家》相呼應(yīng),張啟疆2006年發(fā)表的短篇小說(shuō)《哈羅!總統(tǒng)先生》,不僅讓讀者看到臺(tái)灣的政治本質(zhì)就是一出騙術(shù)或一場(chǎng)夢(mèng)幻,而且還通過(guò)“博愛(ài)特區(qū)”“管制區(qū)”“隔離區(qū)”和“不分區(qū)”,讓大家看到“鬼臉”時(shí)代的種種瘋狂行為。作者以“嘲諷冷冽的筆法”取代過(guò)去“含蓄影射手法”,使“小說(shuō)反政治”的力量得到強(qiáng)化。原以科幻小說(shuō)飲譽(yù)文壇的黃海,于2004年推出新作《永康街共和國(guó)》,寫(xiě)社區(qū)公投時(shí),全區(qū)人民一致通過(guò)社區(qū)獨(dú)立的議題,其中所寫(xiě)的黃、黑、綠之色獅子旗 ,表現(xiàn)了民眾普遍希望過(guò)一種沒(méi)有黑道襲擊、色情入侵和環(huán)境污染的和諧社會(huì)。
和黃凡的創(chuàng)作走不同路向的是年輕作者。這是一個(gè)心中只有“小我”唯獨(dú)沒(méi)有“大我”的世代。他們注重的不是社會(huì)問(wèn)題或政治亂象,而是自己的肚臍眼或隱私行為。表現(xiàn)在題材上,不是情欲開(kāi)放、同性愛(ài)戀,就是雌雄一體的崇拜。在表現(xiàn)手法上,不是嗜好獨(dú)語(yǔ),就是用拼貼方式。社會(huì)描寫(xiě)淡化,情節(jié)不連貫和不可信,人物塑造膚淺,主題生澀得叫人難以下咽 。
當(dāng)然,也有不扮“鬼臉”或抵御“鬼臉時(shí)代”的作家。這里不妨引用一位女教授在《自我的追尋——我的臺(tái)灣文學(xué)研究》[15]中的一段敘述:某年春天,她碰巧和一位本土學(xué)者教授走在街上。已是黃昏時(shí)分,陽(yáng)光留在地上的蔭很長(zhǎng)很傾斜,到了麗水街口繞過(guò)十字路,停在紅綠燈前的本土教授忽然問(wèn)她:
“你是哪一國(guó)人?”
“我第一是中國(guó)人,第二是臺(tái)灣人。”
本土教授用力地看了女教授一眼:
“我第一是臺(tái)灣人,我第二是臺(tái)灣人,我第三還是臺(tái)灣人。”
這樣的話暗示著什么,使連名字都帶有中國(guó)文化即《紅樓夢(mèng)》烙印的女教授大吃一驚:“我的五臟六腑大地震,四分五裂。我出身貧苦,賴師友幫助,從小到大,一路讀的第一志愿,我是那種‘活活潑潑的好學(xué)生,堂堂正正的中國(guó)人。”她就讀的高中就在“總統(tǒng)府”旁邊,每天走過(guò)廣場(chǎng),向飄揚(yáng)有“中華”印記的藍(lán)色旗幟致敬。她不解:我們既然吃的是米飯,用的是筷子,過(guò)的是中秋,寫(xiě)的是中文,“為什么如此而我們不是中國(guó)人?我困惑著,不知道怎樣提問(wèn)題,又感到與這位本土學(xué)者未熟悉到可以隨意地問(wèn),所以就茫茫然回嘉義了。”
抵御“鬼臉時(shí)代”的作品也不少,如洪范書(shū)店推出六冊(cè)《陳映真小說(shuō)集》,其中《歸鄉(xiāng)》《夜霧》《忠孝公園》,是陳氏停筆十多年后的新作。在這三個(gè)中篇里,陳映真持續(xù)發(fā)掘人的靈魂和書(shū)寫(xiě)被扭曲的意識(shí),尤其是作品中所高揚(yáng)的反臺(tái)獨(dú)的愛(ài)國(guó)主義精神,令人肅然起敬。這些作品,是時(shí)代的靈魂之鏡,可惜這個(gè)時(shí)代的政客已越來(lái)越怕看到鏡中自己的“鬼臉”真面目。在出版方面,位于臺(tái)南的臺(tái)灣文學(xué)館出版了《2007臺(tái)灣作家作品目錄》《臺(tái)灣現(xiàn)當(dāng)代作家評(píng)論資料目錄》《臺(tái)灣現(xiàn)當(dāng)代作家研究資料匯編》《臺(tái)灣文學(xué)史長(zhǎng)篇》等一系列套書(shū),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當(dāng)年由軍方出資的黎明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國(guó)新文學(xué)叢刊》《中華文化百科全書(shū)》《中華通史》等叢書(shū)的規(guī)模。這一方面是由于該館資源豐富,另一方面與前任館長(zhǎng)立志要將臺(tái)灣文學(xué)館辦成全球的臺(tái)灣文學(xué)研究中心的理念有關(guān)。
二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文壇“鬼臉時(shí)代”的來(lái)臨?答案是有部分作家和刊物被政治綁架。如2015年出版的某文學(xué)雜志秋季號(hào),竟為臺(tái)灣一位政客寫(xiě)的《直銷(xiāo)臺(tái)獨(dú)——“臺(tái)灣獨(dú)立建國(guó)”道路的探索》做廣告:除有很大的書(shū)影外,還配發(fā)了該刊總編輯為此書(shū)寫(xiě)的序言。極富諷刺意味的是,這本書(shū)的作者大力張揚(yáng)臺(tái)灣人的主體性,還有什么“臺(tái)灣族魂”,可給自己起了一點(diǎn)都不“臺(tái)灣”的洋筆名“奧斯定”。這本書(shū)的“創(chuàng)意”還真不少,如作者把臺(tái)獨(dú)當(dāng)成貨物銷(xiāo)售,而且不是“傳銷(xiāo)”而是“直銷(xiāo)”。可臺(tái)獨(dú)這東西并不是什么營(yíng)養(yǎng)豐富的木耳,而是精神鴉片,吸食后會(huì)忘記自己是中國(guó)人。該刊如此賞識(shí)《直銷(xiāo)臺(tái)獨(dú)——“臺(tái)灣獨(dú)立建國(guó)”道路的探索》,只能解釋為該雜志堅(jiān)持自己不是中國(guó)人的立場(chǎng)所致。當(dāng)人們讀到這種“直銷(xiāo)臺(tái)獨(dú)”的論述時(shí),懷疑所看的不是文學(xué)雜志,而是一本政論刊物呢。
同在南部出版的還有同一色彩的某詩(shī)刊。多年前我訪臺(tái)時(shí),承他們的盛情邀請(qǐng)出席了這家詩(shī)刊的酒會(huì),可與會(huì)者全部說(shuō)“臺(tái)語(yǔ)”即閩南話,我這位中國(guó)內(nèi)地客家人總算聽(tīng)懂了“建立臺(tái)灣共和國(guó)”這一句。前幾年我還在這家詩(shī)刊上發(fā)表專(zhuān)談詩(shī)歌不涉及政治的文章,可該雜志竟把我的論文放在“國(guó)際交流”專(zhuān)欄,中國(guó)內(nèi)地詩(shī)作則放在“海外來(lái)稿”,這正說(shuō)明他們離開(kāi)文學(xué)立場(chǎng)在以政治畫(huà)線。
為什么會(huì)一再出現(xiàn)濃墨重彩宣揚(yáng)“直銷(xiāo)臺(tái)獨(dú)”這種文學(xué)雜志?從大的方面來(lái)講,這是因?yàn)殡S著政權(quán)的更替,新世紀(jì)的臺(tái)灣文壇,不再有“警總”那樣的政治勢(shì)力明目張膽的干預(yù),但仍逃不脫藍(lán)綠意識(shí)形態(tài)的操控。在20世紀(jì),文壇是以外省作家為主,發(fā)展到新世紀(jì),本土作家已從邊緣向中心過(guò)渡,“臺(tái)北文學(xué)”包辦文壇的傳統(tǒng)結(jié)構(gòu)模式,在本土思潮洶涌而來(lái)的情勢(shì)下,發(fā)生了明顯的裂變。當(dāng)下,“臺(tái)灣”的稱(chēng)謂普遍取代了“中國(guó)”,“中、臺(tái)文學(xué)的關(guān)系,猶如英、美文學(xué)之間的關(guān)系” [16]的主張由微弱到增強(qiáng),號(hào)稱(chēng)可以“母語(yǔ)建國(guó)”[17]的“臺(tái)語(yǔ)文學(xué)”正在加足馬力向藍(lán)營(yíng)文學(xué)刊物進(jìn)軍。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繁榮興盛,則廣泛而深刻地影響著文壇的權(quán)力組成,這使得文學(xué)的傳播手段發(fā)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正是在外來(lái)因素的誘導(dǎo)與內(nèi)部求變的兩種合力作用下,文壇的結(jié)構(gòu)及時(shí)作了相應(yīng)的調(diào)整。且不說(shuō)以純文學(xué)為主的大報(bào)副刊早就在向文化方面轉(zhuǎn)型,就是純文學(xué)雜志也注重大眾文學(xué)的需求,更不敢小視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存在。
物欲橫流,鄉(xiāng)愿當(dāng)?shù)溃t能隱退的臺(tái)灣社會(huì)很有娛樂(lè)性,其文化的變化也越來(lái)越有趣。這是一個(gè)別的地區(qū)難以比擬的快速變化的島嶼。政治上由解除戒嚴(yán)到最高領(lǐng)導(dǎo)人直選,去年直選時(shí)藍(lán)營(yíng)發(fā)生“換柱風(fēng)波”,其變化之大之快速已不須多言;而政治帶動(dòng)的社會(huì)變遷與解放,也可用令人咋舌來(lái)形容。比如兩蔣時(shí)代是“強(qiáng)‘國(guó)家弱社會(huì)” ,而后來(lái)是“強(qiáng)社會(huì)弱‘國(guó)家”。原先是“國(guó)治輿論”,后來(lái)是“輿論治國(guó)”。在文壇上,也有這種風(fēng)水輪流轉(zhuǎn)的現(xiàn)象:在20世紀(jì)后半葉,《聯(lián)合報(bào)》《中國(guó)時(shí)報(bào)》的副刊幾乎就是文壇的代名詞。誰(shuí)要當(dāng)作家,就要在這兩張大報(bào)的副刊上亮相或得獎(jiǎng),可現(xiàn)在的獎(jiǎng)項(xiàng)越來(lái)越多。由于文學(xué)的出路不斷在延長(zhǎng),傳統(tǒng)進(jìn)入文壇的模式不斷被解構(gòu),再加上政治勢(shì)力與黨派競(jìng)爭(zhēng)的背后支撐,導(dǎo)致臺(tái)灣新世紀(jì)文壇分化為兩頭小中間大的“統(tǒng)派文壇”“本土派華語(yǔ)文壇”“臺(tái)語(yǔ)文壇”,或如郭楓在《兩岸文學(xué)的自由創(chuàng)作與獨(dú)立評(píng)論——從莫言獲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wù)勂稹穂18]一文中所說(shuō)的“藍(lán)營(yíng)主流文壇”“綠營(yíng)文壇”和號(hào)稱(chēng)不藍(lán)不綠的第三勢(shì)力。
區(qū)塊中心在臺(tái)北的藍(lán)營(yíng)文壇,其實(shí)并無(wú)社址,它和區(qū)塊中心在高雄的綠營(yíng)文壇一樣,都是一種隱性存在。南北對(duì)峙的文學(xué)社團(tuán),不以純文學(xué)著稱(chēng)的多半按照自己所信仰的黨的政治路線發(fā)展。如果說(shuō)在新世紀(jì)發(fā)起成立“搶救國(guó)文教育聯(lián)盟”的余光中,是藍(lán)營(yíng)文壇的盟主;那在葉石濤去世后,鐘肇政和李喬則是“南方文學(xué)集團(tuán)”的靈魂人物。至于文壇第三勢(shì)力,號(hào)稱(chēng)“超越黨派背景,杜絕政商利益,站在全民立場(chǎng)為臺(tái)灣社會(huì)整體進(jìn)步發(fā)聲”。既然不討好官方,又不要財(cái)團(tuán)支撐,這注定了它是一個(gè)弱勢(shì)群體。別看這一群作家居于邊緣地位,可活動(dòng)能力不可小視。可在第三勢(shì)力很難立腳的臺(tái)灣(統(tǒng)獨(dú)斗爭(zhēng)從不停歇,藍(lán)綠對(duì)峙難于淡化,想走第三條道路的施明德被罵為“中國(guó)豬”而落淚),他們要自外于黨政集體力量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堅(jiān)持自己的文學(xué)理想談何容易。
隨著本土勢(shì)力的強(qiáng)大與綠營(yíng)對(duì)藍(lán)營(yíng)的滲透,藍(lán)綠兩派文化結(jié)構(gòu)在新世紀(jì)重新洗牌。遠(yuǎn)在1999年,國(guó)民黨中央主席 李登輝提出“兩國(guó)論”,深藍(lán)的《中央日?qǐng)?bào)》堅(jiān)決不貫徹,其主張只好由綠油油的《自由時(shí)報(bào)》宣揚(yáng),有道是:《中央日?qǐng)?bào)》很“自由”,而《自由時(shí)報(bào)》卻很“中央”。而在新世紀(jì)高揚(yáng)中國(guó)性的《聯(lián)合報(bào)》很“中國(guó)”,稱(chēng)對(duì)岸為中國(guó)的《中國(guó)時(shí)報(bào)》倒很“聯(lián)合”(與去中化思潮“聯(lián)合”)。這種互文性也表現(xiàn)在文學(xué)雜志上,如早先號(hào)稱(chēng)胸懷世界、立足中國(guó)、扎根臺(tái)灣的《聯(lián)合文學(xué)》和在新世紀(jì)“派生”出的《印刻文學(xué)·生活志》,綠營(yíng)人士常常將他們視為藍(lán)色雜志,可這兩家刋物的編輯委員會(huì),竟然都有“臺(tái)獨(dú)文學(xué)宗師”葉石濤的名字。當(dāng)然,這兩家雜志這樣做,無(wú)非是說(shuō)明自己不是什么藍(lán)營(yíng)刊物:選稿時(shí)不分藍(lán)綠,只看好壞。可內(nèi)行人都知道,這編委名單象征意義遠(yuǎn)大于實(shí)際意義,如葉石濤已去世七年,可他的名字在兩家刊物的編委名單中,一直不加黑框保留到現(xiàn)在。
這充分說(shuō)明文化現(xiàn)象的復(fù)雜性。的確,什么問(wèn)題都不能簡(jiǎn)單化。從總體上看,藍(lán)綠文壇對(duì)峙是從群體上說(shuō);從個(gè)人來(lái)說(shuō),政治立場(chǎng)不同不妨礙他們彼此間的交流乃至成為朋友。舉例來(lái)說(shuō),臺(tái)北一家十分長(zhǎng)壽的藍(lán)營(yíng)詩(shī)刋,誰(shuí)也未曾料到其主編竟是民進(jìn)黨人士。還有“中華民國(guó)新詩(shī)學(xué)會(huì)”監(jiān)事會(huì)有深綠的《番薯詩(shī)刊》社長(zhǎng)參與,會(huì)議期間他們只談詩(shī)與生活,無(wú)關(guān)政治。這正說(shuō)明藍(lán)綠兩個(gè)詩(shī)派在新世紀(jì)的對(duì)峙已由顯性轉(zhuǎn)為隱性,熱戰(zhàn)變?yōu)槔鋺?zhàn),由對(duì)抗變成交叉。認(rèn)為“愛(ài)中國(guó)/真危險(xiǎn)”的“番薯”社長(zhǎng)居然在有“中華”兩字的文學(xué)組織任職,由此也可見(jiàn)外省作家與本土作家并非井水不犯河水,有時(shí)在媒介之間還會(huì)出現(xiàn)互動(dòng)的現(xiàn)象,如原為國(guó)民黨文工會(huì)刊物、現(xiàn)改制為民辦的《文訊》,盡管沒(méi)有也不可能被“綠化”,但也刊用了一些綠營(yíng)作家的稿件,且有越來(lái)越多的趨勢(shì)。而綠營(yíng)刊物《鹽分地帶文學(xué)》,其刊名竟是深藍(lán)人士陳奇祿所題。專(zhuān)出本土?xí)拇簳煶霭嫔绯霭娴亩噙_(dá)58本的臺(tái)灣詩(shī)人叢書(shū),也有少量的藍(lán)營(yíng)作家如余光中、向明、張默“混”了進(jìn)來(lái)。這當(dāng)然是由于資源分配問(wèn)題妥協(xié)的結(jié)果。此外,還有南方一位老教授寫(xiě)了一部文學(xué)史投給北部一家老牌藍(lán)營(yíng)出版社,出乎意料的是該社發(fā)行人看到書(shū)名有“中國(guó)”二字立刻感到不爽,擔(dān)心會(huì)影響銷(xiāo)路,建議他去掉“中國(guó)”二字。這種種現(xiàn)象,均說(shuō)明藍(lán)綠文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出現(xiàn)了交叉重疊這一新情況。
新世紀(jì)以來(lái),臺(tái)灣出版業(yè)競(jìng)爭(zhēng)厲害。如前所述,從《聯(lián)合文學(xué)》總編輯位子上卸任的那位掌門(mén)人,另辦《INK印刻文學(xué)生活雜志》和同名的出版公司,與《聯(lián)合文學(xué)》和聯(lián)合文學(xué)出版社成犄角之勢(shì)。他們?cè)诎抵休^量,“印刻”潛力大,大有后來(lái)居上之勢(shì)。出版社無(wú)論是北部的“東大”“三民”“麥田”,還是南部的“春暉”,不管有多么強(qiáng)的主觀性、偏狹性、利益性,都為了各自的利益和出版理念在“鬼臉時(shí)代”中苦撐、苦戰(zhàn)。出版業(yè)畢竟無(wú)法與政治切割,編輯們均不可能生活在世外桃源中。在這種情況下,臺(tái)灣的一些出版社也和文學(xué)雜志一樣,都暗藏有自己“挺馬”或“打馬”的傾向。但他們不管有什么政治顏色,是稱(chēng)馬英九為“總統(tǒng)”或罵其為“馬統(tǒng)”,都不會(huì)公開(kāi)打出旗號(hào),都會(huì)狡黠地偽裝自己的意識(shí)形態(tài)、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預(yù)設(shè)立場(chǎng)、感情偏好、人際網(wǎng)絡(luò)。只要是好作品且有銷(xiāo)路誠(chéng)然都愿意出版,但個(gè)別作品政治顏色太濃如深綠色作品,北部的藍(lán)營(yíng)出版社便會(huì)婉拒,如楊青矗號(hào)稱(chēng)“以文學(xué)為美麗島歷史為見(jiàn)證”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美麗島進(jìn)行曲》,盡管獲得了“國(guó)家文藝基金會(huì)”的創(chuàng)作補(bǔ)貼,“國(guó)藝會(huì)”也中介了北部的一家知名出版社協(xié)助出版,但該出版社負(fù)責(zé)人看完文稿后,覺(jué)得此書(shū)的內(nèi)容太復(fù)雜,它涉及一連串自己無(wú)法贊同的綠營(yíng)選舉運(yùn)動(dòng)、勞工運(yùn)動(dòng)、逮捕刑求、審判辯論、林家血案、國(guó)際人權(quán)救援,因而只好將作品打回票[19]。
新世紀(jì)的臺(tái)灣文壇就這樣被“鬼臉時(shí)代”的陰霾所籠罩。這個(gè)由藍(lán)綠外加雜色的三大勢(shì)力組成的文壇,其原因當(dāng)然是政治的,同時(shí)也是經(jīng)濟(jì)的、文化的、文學(xué)的。是政治生態(tài)的險(xiǎn)惡、意識(shí)形態(tài)爭(zhēng)斗的劇烈、財(cái)閥霸道收買(mǎi)人心以及文人相輕相斗造成的,這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作為一位中國(guó)內(nèi)地的臺(tái)灣文學(xué)研究者,我們所關(guān)心的不是三大勢(shì)力之外的陳映真?zhèn)兊募t色文學(xué)能否壯大,或誰(shuí)的勢(shì)力大,誰(shuí)對(duì)中國(guó)內(nèi)地作家開(kāi)放的園地多,而是從文學(xué)出發(fā)看其能否真正超越藍(lán)綠,產(chǎn)生的作品是否優(yōu)秀,是否經(jīng)得起時(shí)代的篩選。我們從隔岸觀察,當(dāng)代臺(tái)灣作家的確是幸運(yùn)的。盡管當(dāng)前 “文壇一片晦暗前途低迷”,但臺(tái)灣的美麗和富足,這是鐵的事實(shí)。他們的最高領(lǐng)導(dǎo)人有遠(yuǎn)見(jiàn),竟然主張政治為藝文服務(wù),可惜這只是一張空頭支票,當(dāng)下臺(tái)灣作家仍然是出書(shū)難、辦刊難、辦會(huì)難、辦團(tuán)體難。詩(shī)刋更可憐,實(shí)行的是“六十年一貫制”無(wú)潤(rùn)筆費(fèi)[20]。
臺(tái)灣作家到中國(guó)內(nèi)地交流時(shí),常常炫耀他們的創(chuàng)作自由和出版自由度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大陸。不過(guò),據(jù)內(nèi)行人士觀察,其自由并不是無(wú)邊,且不說(shuō)在戒嚴(yán)時(shí)期連吃水果都要考慮政治,如老師教導(dǎo)學(xué)生切楊桃不能橫著切以防變成五角星,單說(shuō)解嚴(yán)后至當(dāng)下臺(tái)北均無(wú)“八路”公共汽車(chē),市民們從20世紀(jì)50年代至新世紀(jì)均不享有坐八路乃至四路車(chē)的自由。純?yōu)槊癖娫旄5慕煌ㄐ袠I(yè)居然有政黨的黑手在操控,那文壇也難逃各方權(quán)勢(shì)的脅迫。這種無(wú)“八路”的奇怪現(xiàn)象反映在創(chuàng)作上,便是不少作家和報(bào)刋在不同程度上受政黨、意識(shí)形態(tài)或受商業(yè)的宰制,另一令中國(guó)內(nèi)地同行驚詫的潛規(guī)則是寫(xiě)論文時(shí),最好不要寫(xiě)出作家的籍貫是中國(guó)某省[21]。這種封閉癥和“獨(dú)立病”,是外人很難了解的“臺(tái)灣特色之痛”,它一時(shí)難于治愈。
“誰(shuí)來(lái)揭破臺(tái)灣文學(xué)自由的假面?” [22]如果真的有人能“揭破”,或有唐文標(biāo)式的人物再世,或曰在臺(tái)灣真的有人能治這種“獨(dú)立病”,中國(guó)內(nèi)地乃至整個(gè)中國(guó)文壇當(dāng)然受益。應(yīng)該看到,病毒的發(fā)源地來(lái)自無(wú)限膨脹的臺(tái)灣意識(shí)。這種病毒的強(qiáng)大,已被某詩(shī)人提出的“寧愛(ài)臺(tái)灣草笠,不戴中國(guó)皇冠”[23]的口號(hào)和一位“堅(jiān)貞的臺(tái)灣主義者”所書(shū)寫(xiě)的“臺(tái)灣共和國(guó)的描述” [24]等種種“病情”所證實(shí)。如能迷途知返,將臺(tái)灣意識(shí)與中國(guó)意識(shí)聯(lián)結(jié),便找到了良藥。服用它,何樂(lè)而不為?但不管能否做到,有創(chuàng)作才能的臺(tái)灣作家,都應(yīng)擺脫國(guó)族認(rèn)同問(wèn)題的困境,把握住時(shí)代前進(jìn)的方向,即使在“鬼臉時(shí)代”也一定能創(chuàng)作出無(wú)愧于新世紀(jì)這一偉大時(shí)代的作品。
注釋?zhuān)?/p>
[1]馬森:《華人乎?中國(guó)人乎?人民霧煞煞》,臺(tái)北,《文訊》,2000年12月。
[2]向明:《詩(shī)人也瘋狂》,臺(tái)北,《中央日?qǐng)?bào)》網(wǎng)絡(luò)版,2006年11月17日。
[3]馬森:《詩(shī)人變流氓》,《世界日?qǐng)?bào)》,2005年11月15日。
[4] [7]楊宗翰:《文學(xué)史的未來(lái)/未來(lái)的文學(xué)史》,臺(tái)北,《文訊》,2001年1 月號(hào),第50頁(yè)。
[5]陳芳明的《臺(tái)灣新文學(xué)史》出書(shū)前在《聯(lián)合文學(xué)》連載過(guò),單行本于2011年由臺(tái)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公司出版。
[6] 陳允元等:《〈臺(tái)灣新文學(xué)史〉關(guān)鍵詞101》 ,臺(tái)北,《聯(lián)合文學(xué)》 2012年第2期。
[8]楊照:《文學(xué)的原象·新人類(lèi)的感官世界》,臺(tái)北,聯(lián)合文學(xué)出版社,1995年版。
[9]李?yuàn)]學(xué):《疏離的美學(xué)》,臺(tái)北,《聯(lián)合文學(xué)》,2003年8月號(hào)。
[10]袁哲生:《偏遠(yuǎn)的哭聲》,臺(tái)北,《聯(lián)合文學(xué)》,2003年8月號(hào)。
[11]袁哲生:《偏遠(yuǎn)的哭聲》,臺(tái)北,《聯(lián)合文學(xué)》,2003年7月號(hào)。
[12]應(yīng)鳳凰:《從〈臺(tái)灣文學(xué)評(píng)論〉創(chuàng)刊號(hào)說(shuō)起》,臺(tái)北,《文訊》,2001年9月。
[13]蔣為文:《陳芳明們,不要制造臺(tái)灣文學(xué)生態(tài)災(zāi)難》,見(jiàn)《臺(tái)灣文學(xué)藝術(shù)獨(dú)立聯(lián)盟電子報(bào)》,2001年6月15日。
[14]臺(tái)文筆會(huì)編輯:《蔣為文抗議黃春明的真相:臺(tái)灣作家ai/oi用臺(tái)灣語(yǔ)文創(chuàng)作 》,亞細(xì)亞國(guó)際傳播社,2011年,第105頁(yè)。
[15]高雄:《文學(xué)臺(tái)灣》2002年冬季號(hào),總第44期,第26~27頁(yè)。
[16]林衡哲:《漫談我對(duì)臺(tái)灣文化與臺(tái)灣文學(xué)的看法》,臺(tái)北,《臺(tái)灣文藝》,1986年5月,第55頁(yè)。
[17]方耀乾:《臺(tái)語(yǔ)文學(xué)發(fā)展簡(jiǎn)史》,見(jiàn)臺(tái)語(yǔ)kap客語(yǔ)現(xiàn)代文學(xué)專(zhuān)題網(wǎng)站。
[18] 郭楓:《西岸文學(xué)的自由創(chuàng)作與獨(dú)立評(píng)論——從莫言獲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wù)勂稹罚_(tái)北,《新地文學(xué)》,2012年12月。
[19]周復(fù)儀:《楊青矗——以文學(xué)為美麗島歷史為見(jiàn)證》,臺(tái)北,《聯(lián)合文學(xué)》,2009年12月號(hào),第77頁(yè)。
[20]于2014年10月復(fù)刊的《秋水》,曾說(shuō)有稿酬,據(jù)詩(shī)友說(shuō)未兌現(xiàn)。
[21]如《臺(tái)灣文學(xué)評(píng)論》曾發(fā)表過(guò)一位青年學(xué)者高麗敏《傳承與發(fā)揚(yáng)——論鐘肇政作品〈濁流三部曲〉〈臺(tái)灣人三部曲〉中的客家文風(fēng)》,在“前言”中云:“鐘肇政,原籍廣東,1925年出生于桃園縣。”一位作家讀了后“不覺(jué)心頭一酸”,因而投書(shū)《臺(tái)灣文學(xué)評(píng)論》質(zhì)疑《鐘肇政原籍廣東嗎?》,認(rèn)為高女士這種寫(xiě)法犯了“軟骨癥”,是在向中國(guó)示好乃至“投降”,并感慨道:“非把臺(tái)灣人無(wú)限上綱到中國(guó)人,不能顯示其存在?以鐘肇政先生臺(tái)灣意識(shí)的堅(jiān)定,硬把他定位為‘原籍廣東,想來(lái)鐘老恐怕會(huì)啼笑皆非或黯然神傷吧?”
[22]郭楓:《誰(shuí)來(lái)揭破臺(tái)灣文學(xué)自由的假面》,臺(tái)北,《新地》,2015年12月。
[23]李敏勇:《寧愛(ài)臺(tái)灣草笠,不戴中國(guó)皇冠》,《笠》,1987年6月。
[24]李喬:《我的心靈簡(jiǎn)史——文化臺(tái)獨(dú)筆記》,臺(tái)北,望春風(fēng)出版社,2010年,第200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