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悝、克二人說”駁議
高培華
由春秋至戰國初期,新型士階層崛起步伐顯著加快。庶民得名師教誨,全憑個人學識和能力輔佐明主建功立業而位至諸侯卿相者,大致是從李悝開始的。中國古代的改革家能像李悝這樣既大功告成又穩保身家性命的實屬罕見。這無疑是得益于子夏和魏文侯在魏國造成的濃郁的儒家文化氛圍。
李悝其人學界熟知。這里,著重弄清李克與李悝究竟是兩個人,還是一個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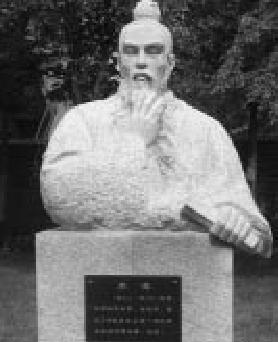
《史記·貨殖列傳》記“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平準書》記“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強君”,《孟子荀卿列傳》說李悝“盡地力之教”,《漢書·食貨志》謂李悝“盡地力之教”,《藝文志》記儒家“《李克》七篇”班固自注“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記法家“《李子》三十二篇”班固自注“名悝,相魏文侯”。如此則李克、李悝均為魏文侯相,都實行“盡地力之教”,分明是一個人。但是,《漢書·古今人表》又記李悝與段干木、田子方等并列“上下”(三等),記李克與魏文侯、魏成子等并列“中上”(四等),顯然是兩個人。
清代崔適《史記探源》認為李克即是李悝:“悝、克一聲之轉,古書通用。”錢穆先生在《先秦諸子系年》中贊成崔說。郭沫若也講:
說者多以為(李克)即是李悝的異名,我看是很正確的。因為悝、克本一聲之轉,二人時代相同,地位相同,思想相同,而李悝盡地力之教,在《史記·貨殖列傳》及《平準書》則說“李克務盡地力”。儒家中既有李克,法家中又有李悝者,也就如儒家中既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雜家中又有“《公孫尼》一篇”。《古今人表》中把李悝與李克分為二人,那應該是班固的錯誤了。
現代學界對于崔、錢、郭觀點有贊同者、有反對者。反對者以楊寬先生論述最詳:
《史記·貨殖列傳》《史記·平準書》“李克”當為“李悝”之誤。《漢書·古今人表》列李悝于第三等,李克為第四等,作為兩人,是不錯的。李悝是法家,而李克乃子夏弟子,是儒家。《漢書·藝文志》有《李子》三十二篇列于法家,說是“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又有《李克》七篇列于儒家,說是“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李悝初為上地守,曾為秦所敗,又曾大敗秦人,見《韓非子·內儲說上》和《外儲說左上》,后為魏文侯相。李克是魏文侯時所屬中山之相。《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記翟黃對田子方說:“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史記·魏世家》記翟璜對李克說:“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另《說苑·臣術篇》同。《呂氏春秋·適威篇》載:“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于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高注以為是武侯分封于中山時。《淮南子·道應篇》作“魏武侯問于李”,高注:“李克,武侯之相。”也是指武侯分封于中山時的相。戰國史料上未見有李克為魏文侯相之說,《漢書·藝文志》說李克“為魏文侯相”,當是“為魏武侯相”之誤。《呂氏春秋》《韓非子》等書記李悝和李克兩人事,區別清楚,不相混淆,兩人的主張也不相同。《韓非子·難二篇》說:“李克(今本誤作“李兌”,從孫詒讓說改正)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克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于義,謂之窕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子姑免矣!”韓非曾發表很多議論,駁斥李克之說,認為“人事”“天功”都能夠使得“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并且指出李克之說是“無術之言也”。如果李克即是李悝的話,李悝主張“盡地力”,正是極力鼓吹通過“人事”謀求“入多”的,不可能發表這樣的見解。同時韓非的評論也不對頭了。
筆者贊同崔、錢、郭的觀點;在此對楊寬先生上面的論述駁議如下:
第一,《史記·貨殖列傳》《史記·平準書》兩處記“李克務盡地力”,并非偶爾誤記,可以互證;《漢書·藝文志》記李克“為魏文侯相”,可與《淮南子·泰族訓》“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互證。楊先生謂《史記》這兩處李克,均“當為‘李悝之誤”,于理難以說得通。偶爾一誤說得過去,兩處記述相同,豈能輕易否定?又謂《漢書》“李克‘為魏文侯相當是‘為魏武侯相之誤”,也缺乏根據。楊先生說李克只是中山相,沒有擔任過魏文侯相,證據只是《呂氏春秋》等記武侯封于中山李克為相,“戰國史料上未見有李克為魏文侯相之說”。這不足以否定《漢書》記李克“為魏文侯相”。因為子夏弟子的時代,正是顧炎武所謂《左傳》之后“史文闕軼,考古者為之茫昧”的一百三十三年間,此間人和事,今傳“戰國史料上未見”者實在太多,正需要兼采漢代史家記述來彌補。從《史記·魏世家》記李克深得魏文侯信任的情況來看,《淮南子·泰族訓》“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的記載,與《漢書·藝文志》記李克“為魏文侯相”都是可信的。李克先為中山相,以后又為魏文侯相,是完全可能的。兩者并不互相排斥。
第二,楊先生強調“李悝是法家,而李克乃子夏弟子,是儒家”,顯系受到當時過度夸大“儒法斗爭”之影響。其《戰國史》作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1980年出版。當時學界對于儒、法兩家的認識界限分明。《戰國史》難以像《先秦諸子系年》那樣揭示“法源于儒”的歷史事實,難以像《十批判書》那樣正視子夏門下政事弟子亦儒亦法的身份,可以理解。
第三,楊先生所引《韓非子·難二篇》李克言論,實不足以證明李克與李悝主張不同。李克“語言辨,聽之說,不度于義,謂之窕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云云,是其任中山相時針對“苦陘令上計而入多”,向年輕的中山君所講,故有“子姑免矣”之語。上計,指戰國、秦、漢時期地方官進京上計簿,報告本地當年人民戶口、錢糧收入、盜賊、獄訟等事項,類似當今官員的年終述職;窕言,《文選》注引作“膠言”,《廣雅·釋詁》云:“膠,欺也。”《方言》云:“膠,詐也。”王先慎曰:“窕,本為空虛不充滿之言,引申之凡虛假不實者,通謂之窕;‘窕言者,虛言不可信以為實。下文‘窕貨者,虛貨不可恃以為富也。”由此可知,“苦陘令上計而入多”,即上報虛假不實的收入數字。這既是李克發現的問題,也是韓非記李克言論之前陳述的事實。李克所謂“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是說單純農業種植收入是有限的(至今仍然是這樣),超過限度的上計收入數字,是虛假不可恃的“窕貨”;而不是說“無山林澤谷之利”絕對不能多收入,亦更非反對通過“人事”以謀求“入多”。韓非于此對李克的問難,顯系誤解。李克之語,只是就事實向中山君講述“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的道理,是在治理中山過程中輔導其君,盡其為臣而又為傅的職責。李克所講的道理,應當是君子為政——用人做到知人善任,理財做到量入為出的基本前提,并沒有什么錯。《韓非子》《史記》都記翟璜曰:“臣薦李克而中山治。”可見李克治中山是十分成功而大獲好評的!李克及時發現苦陘縣令年終上計“入多”,說明其精通地方政務,熟悉轄區各地經濟條件,上計之前已對該縣農業收入有一個基本估算,故能輔導中山君既“不聽窕言”,又“不受窕貨”。這和《漢書·食貨志》記李悝“盡地力之教”,在對“地方百里”農民收支進行匡算的基礎上平抑糧價,避免發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的情況,以保持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做法,本是高度一致的。正因為李克精于理財,既不聽信虛報“入多”數字而加重賦斂,也不過高估計財力而重用虛報者,才能夠富民、足食進而強兵,一旦發生災荒饑饉也能有備無患,這才取得“中山治”的效果。所以,仔細審視此則材料,不僅不能證明李克、李悝不同,反而讓人更加相信李克即是李悝。
弄清楚悝、克本是一個人,其生平就比較清楚了:他早年學于子夏,出任中山相之前還曾經任上地守,率軍與秦戰而互有勝負。《韓非子》記載: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射也。
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于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這說明子夏設教,在其“哭子失明”前也像孔子一樣有武藝傳授,孔門再傳弟子仍然是文武兼備的。李克學成出仕,由上地守、中山相,直至魏國相,其相中山是相魏國的準備,治魏是治中山的擴大。至于李克的歷史性政績,主要有兩項:一是“盡地力之教”以富民強國,二是撰次《法經》以治國安民。對此以往論者多有論述,此不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