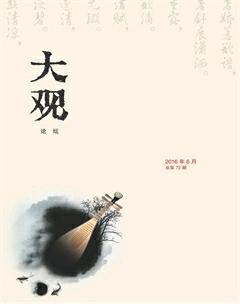頭巾之殤
李云鵬+沈志興
摘要:在政治小說《雪》中帕慕克以歷史畫卷般的大手筆生動勾勒出了土耳其社會中以凱末爾世俗主義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沖突為主干的各種沖突;而這幅畫卷又不乏細密畫般的細膩與精致,書中帕慕克塑造了不少生活在沖突夾縫里活靈活現的女性形象,而圍繞她們頭巾的佩戴與否則是各種沖突的焦點。帕慕克讓婦女們發出了源于自己內心的呼喊,本文則從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角度出發,對包括女性形象的審視、女性精神追求的思考以及女性社會問題的溯源這幾個角度去傾聽她們的呼喊,并在此基礎上探索伊斯蘭文化背景下土耳其女性文學批評的非西方式話語權體系的建構問題。
關鍵詞:《雪》;帕慕克;土耳其;女性主義批評
《雪》如同一幅歷史畫卷繪畫大師帕慕克以大手筆生動勾勒出了土耳其現代社會中的各種沖突。小說的主要故事情節是圍繞上世紀90年代初發生在土耳其東部小城卡爾斯的一場軍事政變展開的;主要沖突則是在政變的發動者凱末爾世俗主義者戲劇演員蘇納伊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神藍之間。在這個顯性的沖突下又蘊含著東方與西方的沖突、現代與傳統的對撞、愛與恨的糾纏以及生與死的掙扎。小說也正是在各種沖突中表現出作者帕慕克對文化、宗教、社會、人性以及愛情的思考。而值得一提的是這幅畫卷又不乏細密畫般的細膩與精致,帕慕克在小說中塑造了不少活靈活現的女性形象,執著勇敢的卡迪菲、美麗熱忱的伊珮珂、善良敏感的韓黛以及那些在痛苦中掙扎的宗教女學生等等,她們個性鮮明,在社會的夾縫中執著地追尋著自我,而她們頭巾的佩戴與否則是多種沖突的焦點。這既是對土耳其現當代社會中婦女問題的現實聚焦,又是對在這樣一個社會背景下女性人生價值追求的哲學思考。
一、卡、卡爾斯、雪(Ka、Kars、kar)
小說的主人公是卡,故事情節發生在土耳其東南部的一座小城卡爾斯。小說主人公的名字、小城的名字及“雪”在土耳其文中非常相似(分別為Ka、Kars、kar)。帕慕克這樣的安排似乎是有意在三者間構造出相互映射的隱喻關系,從而在敘事的迷宮中引導讀者步步深入去探尋人物身份的特質與小說主題的精髓。卡爾斯是一個典型的城市,它曾被俄國殖民統治,凱末爾的世俗主義思想、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想、甚至包括社會主義思想在這里都有一定的影響,庫爾德民族主義者也在此活動頻繁……這些注定了卡爾斯要卷入政治沖突的漩渦之中,注定要在身份的茫然中完成自我的救贖。就像是當代的土耳其要陷入對自己身份撕裂的痛苦之中。用拉康的“三角結構”理論去看待,現實中的土耳其社會是“真實界”,小說中的卡爾斯是“想象界”,而“象征界”究竟是什么帕慕克并沒有給讀者答案,他構造了一個智力解讀的故事情節迷宮,讓讀者隨著主人公卡的客觀言行去給出自己的答案,這也是小說的魅力所在。
從帕慕克早期作品《白色城堡》、《我的名字叫紅》和《黑書》再到這部小說,帕慕克以一名作家的時代責任感思索著在西方文化入侵的背景下土耳其民族傳統文化的未來。其中每部小說都有所側重,本部小說中帕慕克以卡這個人物去探求土耳其政治社會的未來,并以婦女頭巾的去留與否以及卡爾斯女孩們的自殺事件為線索來思索未來土耳其社會中婦女的角色。筆者認為小說中帕慕克的主張并非是要涇渭分明地指出是要選擇西方亦或是東方;是要選擇世俗亦或是伊斯蘭,與其說在身份撕裂的痛苦中掙扎不如在這種文化的雜糅中去領悟這種文化的獨特魅力并去探尋人性的真諦。莫言先生曾經和帕慕克對此有過交流與探索,他后來意味深長地說到政治觀點相左、宗教信仰不同的人之間的最佳狀態應該是像漢字“人”一樣相互支撐。
這部小說中最不可或缺一個要素就是雪,小說中的雪可以從藝術手法與文本內涵兩個維度去認知。從藝術手法上去看待,小說的敘述中雪會時不時地出現,或大或小,隨著故事的情節或是展現出雪的晶瑩純潔,這多是表現主人公對愛情的幻想;或是展現出雪的冰冷蕭瑟,這多是烘托死亡的氣息;亦或是雪的寂靜安詳,這給讀者提供無限的遐想。其實小說的敘事手法本身就像是一片放大了的雪花,雪花的核心是卡,向外延伸的觸角有愛情、天堂、回憶、頭巾、自殺等等,這些觸角又會向外延伸這就又會衍生出新的觸角諸如戲劇、政變之夜、軍人、邏輯、星星等等,比起第一層的觸角這些內容更為具體。第二層的觸角又會衍生出第三層的觸角,以及后面的第四層第五層等等。所有這些不同層面的觸角連同卡這個核心恰似像是從顯微鏡下觀察到的一片精致的雪花。值得一提的是女孩們的自殺、與伊珮珂的愛情、卡迪菲是否摘去頭巾等等女性主義因素應該處于核心的觸角層面,因為它們或是直接揭示主題,或是把情節推向高潮。
從文本內涵來看,小說中的雪是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的。廣義層面的雪是卡爾斯下了四天四夜的大雪,莫言先生讀完本書曾經發出感嘆《好大一場雪》,這場大雪將卡爾斯與世隔絕,而卡爾斯的這場大雪下掩蓋了太多的東西,皚皚的白雪下政變、自殺、仇殺、陰謀、監聽等等在滋生,好大一場雪,表面看它讓卡爾斯變得潔白肅穆而實際上它讓卡爾斯一部分人陷入瘋狂也讓另一部分人感到冰冷。狹義層面看雪則是一個個晶瑩而又特征明顯的個體,不同經歷的人生看到的是不同的雪花。這在本書的第24節中《我,卡——六角形的雪花》中有較為詳細的闡釋,對于“雪”卡也曾專門作詩《雪》,他還將自己所創作的十九首詩放于一片雪花圖形的位置。如果說廣義層面的雪表現了卡爾斯乃至土耳其社會的一些方面,那么狹義的雪則是對卡內心世界的智力解讀。
二、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小說一開始就給我們交代了這樣一個社會背景——在卡爾斯有許多女孩自殺,主人公卡來此也是以調查女孩們自殺的名義來的。事件最初是由兩年前一個來自巴特曼的少女自殺而開始的。隨她之后的是這個女孩的妹妹,她被老師懷疑不是處女,因而與她訂婚的男方家庭也悔婚了,女孩身邊的家人也給她了不小的壓力,后來女孩喝了一瓶安眠藥靜靜地離開了人世,但最后的尸檢報告顯示這個女孩是個處女。帕慕克這樣寫道“關于自殺像瘟疫一樣的說法開始出現了”。另有典型是那些戴頭巾的女孩,學校不讓佩戴頭巾的女孩去上課,并會因為缺課超過一定的數量而開除她們,警察也會在校門口抓她們。父母親人不會給她們理解更多的時候給她們的是指責。女孩們的離世也沒有任何的征兆,一切如常在寧靜中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面對她們眼前這個雜亂喧囂的世界,面對她們本不該承受的壓力,她們選擇的是一種靈魂的解脫。endprint
女孩們在她們的年齡承受了太多她們生命中本不應該承受的重量。她們的年齡本不應該卷入過多的社會壓力,本不應該在政治斗爭的漩渦中掙扎。她們只想做簡單純粹的自己,可這絕非意味著對現實的妥協,小說中的她們絕不是脆弱的,無論是校門口凜冽寒風中的抗議,無論是面對家人冷嘲熱諷時的忍辱負重,也無論是監獄里警察的威脅拷打,她們展現出超乎尋常的執著與堅韌。如果生命不能在最美的時刻怒放,那么不如選擇凋零。可惜的是卡爾斯下了好大的一場雪,這場雪冰冷而無聲,漫長而蕭瑟,它壓垮了太多本應該怒放的花蕾。
三、帕慕克眼中的理想女孩
帕慕克的《雪》中塑造了一位個性鮮明的女性形象—卡迪菲。卡迪菲的身世不同尋常,她的父親曾經是一名共產主義者,她的姐姐被卡認為是卡爾斯最美麗的女人。卡迪菲也非常漂亮,她曾經生活在伊斯坦布爾并已經成為了一個非常成功的模特,也拍過不少的大尺度很西方化的廣告,而恰恰是這樣一個少女來到了卡爾斯之后,沒過多長時間竟然成為了佩戴頭巾的穆斯林女孩的領袖。這其中轉變之大,看似不合情理而實際上則是帕慕克的一個妙筆。可以看為兩個原因,其一是卡迪菲是一個個性獨立且自尊心強的女孩,她對卡爾斯戴頭巾的女孩心生同情并決心加入他們為了尊嚴的抗爭,這是少女的“叛逆”;其二則是卡迪菲對于卡爾斯伊斯蘭宗教領袖神藍的愛慕之情,這則是少女的“懷春”。卡迪菲可以視為帕慕克理想中的土耳其現代女性的一個縮影,她們在土耳其社會中各種思潮各種勢力的夾縫中艱難地生活著,但她們卻并不向任何一方妥協,她們獨立、自尊、勇敢,這也并不意味著她們不能融入土耳其社會,而是一種積極并且帶有抗爭性質的生活態度。
圍繞卡迪菲是否愿意在《卡爾斯的悲劇》這樣一場整個卡爾斯人都非常關注的戲劇中去掉頭巾,小說更是被一步步推向高潮。小說中后半部分卡迪菲作為戴頭巾女孩的領袖,同世俗主義者領袖蘇納伊達成協議,只要她在舞臺上摘下頭巾,蘇納伊將釋放已被捕的神藍。最終的結果也是小說的高潮,即卡迪菲明知神藍已被釋放卻依舊堅持要取下了頭巾,之后她將蘇納伊在舞臺上槍殺。這看似出乎意料卻在情理之中,卡迪菲內心所追求的既不是伊斯蘭,也并非是世俗,她所追求的是真正的自我。卡迪菲的結局是具有諷刺意義的,她出獄后嫁給了一個小她四歲的法澤爾并過著平淡清苦的生活,這樣的安排多少體現出了帕慕克對于當下土耳其社會婦女問題的無奈與悲觀。
四、去的掉的頭巾,去不掉的心結
佩戴頭巾是穆斯林婦女的標志,在《古蘭經》第24章里有關于女性著頭巾及黑袍非常詳細的敘述。伊斯蘭教看來佩戴頭巾是女性貞潔的象征,它可以使女性免遭騷擾與侵犯,可以使社會避免由女人的性所帶來的危險;它亦強調男女應該有不同的社會分工,男性應該在公共領域,而女性更應該在私人領域,至于那些拋頭露面的工作包括接受現代教育對女性是沒有必要的。由婦女佩戴頭巾的風波自從土耳其之父凱末爾在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上建立起現代土耳其共和國時至今日已經延續了將近百年。凱末爾以他的“ 六大原則”(Alt Oku)為出發點,對土耳其進行了完全西方化的改革。這其中凱末爾于1925年宣布女性的頭巾、黑袍和男人們的費茲帽、纏頭等一同被廢除,1926年凱末爾宣布廢除一夫多妻制。在凱末爾的眼中這些都是愚昧與野蠻的象征。在1930年頒布的以瑞士憲法為藍本的《民法》中凱末爾進一步賦予了女性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凱末爾的一系列大刀破斧的西化改革對于土耳其婦女的解放無疑有著重大的積極意義,但是實際并沒有凱末爾想像中的那么簡單、理想。對于一個已經信奉伊斯蘭教近千年的民族來講,讓婦女們一下子放棄她們曾經視為神圣的東西恐怕是不現實的。頭巾摘下來很快很容易可是心結要解開來卻很漫長很困難。這尤其體現在土耳其的東部南部地區,凱末爾的改革遇到了相當的阻力,廣大農村地區婦女們的生活和以前并沒有太大的的改變,就是在伊斯坦布爾這樣的城市也能看到有許多纏頭巾的婦女。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伊斯蘭教的復興,土耳其社會中佩戴頭巾的婦女數量進一步增加。1980年土耳其軍人政變之后,政府曾發布對公職人員的《服飾法》禁止婦女戴頭巾;1983年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員會禁止戴頭巾的女大學生聽課或考試;隨后1984年土耳其國窖安全委員會聲稱佩戴頭巾的女學生是共和國的敵人應被開除。1988年土耳其議會曾通過允許女大學生戴頭巾的決議,但被總統及憲法委員會否決。此后土耳其社會中關于婦女佩戴頭巾問題的爭論一直不斷,尤其是針對大學生佩戴頭巾,這部小說的創作背景也正是基于此。
五、對土耳其女性文學批評建構的一點思考
帕慕克在小說中委婉表達出了對土耳其婦女問題現狀的不滿,在他眼中土耳其婦女問題的解決恐怕不會是凱末爾眼中土耳其婦女們如同西方婦女一樣身穿性感緊致的職業裝穿梭于都市中的各行各業,這只是凱末爾的一廂情愿;也不會是伊斯蘭教中的頭戴圍巾、身穿黑袍,在家里相夫教子、戰戰兢兢。帕慕克認為它應該是基于土耳其傳統文化,并融合著現代化的理想觀念。而這里面最重要是對婦女的尊重,不得不說的是在土耳其,尤其是東南部地區“榮譽謀殺(honor killing)”還很盛行。在此基礎之上則是讓她們建立起自己的話語權。如果只是把婦女問題看為是政治的一個衍生品,那么土耳其婦女問題將無從解決,這又必將會影響土耳其社會的全面平衡發展以及國家現代化的進程。
帕慕克的《雪》以一種略帶悲觀的態度審視著東西方文化沖突、各種政治勢力角逐背景下土耳其社會的未來,在這部小說中帕慕克尤其關注到了長期在社會夾縫中生存的土耳其女性。他成功塑造了諸如卡迪菲、戴頭巾的女學生、伊珮珂等個性鮮明的女性形象。他還思索了造就她們這些命運的政治、社會、文化因素,委婉表達出了他內心對于土耳其婦女問題現狀的不滿。但從人物命運結果的安排來看帕慕克對此卻又悲觀與無奈。藝術手法上帕慕克注意到了對女性主體形象的個性化、差異化、內在化的塑造,不僅關注社會意義上的女性性別群體,還注重挖掘女性個體的有意識、潛意識甚至無意識的心理空間,讓這部歷史的恢宏畫卷不乏細密畫般的細膩與精致,這亦代表著西方女性批評的發展方向。endprint
基于此,筆者最后想談一下自己對于土耳其女性文學批評建構的一些想法。長期以來西方社會一直將自己的文化視為具有普世性的文化,并戴一種有色的眼鏡看待其他文化。對于土耳其婦女包括眾多海灣婦女社會地位的的建構與精神需求的探索更多是在一種西方話語權體系下完成的,這里面當然也包括文學批評。但事實上這些理論可能會有些“水土不服”。如今在包括土耳其在內的眾多伊斯蘭國家的社會中不難發現許多婦女頭戴頭巾并遵守著伊斯蘭教的傳統但卻有著非常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她們可以流利地使用英語,在這個資訊發達的時代很好地獨立學習工作;再比如小說中卡迪菲的命運選擇,這些西方視角下看似矛盾的現象卻有著它內在的和諧。事實上伊斯蘭社會有著自己近一千四百年的歷史積淀,形成了自己特定的文化,并在不斷地進行實踐與調整,這種文化注定是與西方文化不同的,但即使在今天看來它同樣閃耀著自己獨到的光芒。她們真正需要什么樣的權利,到底有什么樣的精神追求,繼而什么樣的文學批評范式才是最合適的,這些都值得進一步的思考。而在這個建構的過程中西方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里必然有值得借鑒的地方,但絕非拿來就能用這么簡單。不同的歷史文化積淀以及不同的社會發展狀態乃至不同的民族性格都會導致土耳其的女性文學批評有其自己的獨到之處。
【參考文獻】
[1][土]奧爾罕·帕慕克.雪[M].沈志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153-160.
[3][法]雅克·拉康.拉康選集[M].褚孝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18-26.
[4][土]奧爾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紅[M].沈志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莫言.好大一場雪——<雪>賞析[J].東方文學研究通訊,2008(02).
[6]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52.
[7]哈全安.土耳其通史[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165-182.
作者簡介:
李云鵬,男,漢族,洛陽外國語學院亞非語系教員,碩士研究生學歷。研究方向:土耳其語言文學。
沈志興,男,漢族,洛陽外國語學院亞非語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學歷。研究方向:土耳其語言文學。(帕慕克小說《雪》、《我的名字叫紅》、《寂靜的房子》等作品中文版的譯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