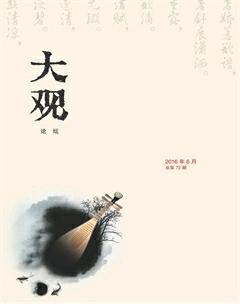淺談竹笛的藝術發展
何想成
竹笛作為我國最早出現的民族樂器之一,至少已經有七千多年的歷史。但真正具有現代竹笛形制的,還是在唐宋元以來,伴隨著戲劇的發展,竹笛被廣泛地運用到各個地方劇種中,承擔主奏或領奏的角色,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竹笛藝術魅力的真正挖掘和展現,還是近50年的事情。從1949年建國至今,竹笛的藝術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9—1956年,這是我國竹笛獨奏音樂的開始階段。在這一階段,出現了一批以馮子存、劉管樂、陸春齡、趙松庭為代表的竹笛音樂的開拓者,他們使竹笛由一種伴奏樂器變為獨奏樂器,由幕后走上舞臺,由民間走向專業。但是由于生活背景、地域的差異,形成了以他們為代表的南(陸春齡、趙松庭)、北(馮子存、劉管樂)派演奏風格。在演奏上,北方以吐、滑、垛、花等舌頭上的技術為主,并大都用梆笛演奏,曲調高亢,明亮。南方以顫、疊、震、打等手指上得技術為主,并大都采用曲笛演奏,曲調抒情,柔美。當時的演奏還沒有涉及到很復雜的技巧。他們所演奏的曲目,大多是民間流傳的戲曲曲牌或根據戲曲伴奏移植、改編而成的,具有鮮明的地方風格,濃郁的生活氣息,真正創作的笛子獨奏曲在這一階段還沒有出現。
第二階段,1956—1979年,以趙松庭《早晨》的創作為標志,是我國竹笛音樂的大發展階段。可以說,《早晨》的創作,揭開了我國竹笛獨奏音樂的創作史,它開始了我國竹笛音樂由單純地演奏民間音樂轉化為演奏創作音樂的階段。它吸收了北派笛子中歷、滑、吐、垛和飛指顫音等演奏技法,打破了南北不相融的局面。還借鑒了嗩吶的循環換氣技巧,3/4節拍及主音五聲調式轉換的運用,半音的出現等突破了之前笛曲的創作手法和笛子演奏風格的單一性,使樂曲很有新意。和它以前的民間竹笛獨奏曲相比,不論是在音樂形象、節奏節拍、強弱對比等方面,都有極大的創新。
第三階段,從1979年以后中國竹笛走向了一個繁榮發展的階段,也是竹笛藝術的飛躍與提升階段。竹笛音樂的創作、教育、演奏技術都提高到一個規范化、系統化的層次。而且隨著一批以外國民間音樂為素材的“外國樂曲”,各國家、地區的音樂元素被廣泛地運用到竹笛音樂中,如《野蜂飛舞》、《流浪者之歌》、《羅西尼主題變奏曲》等外國作品都被笛子演奏家們移植并演奏,這給笛子的表現形式,演奏技法創造了更多的可能性。因此在竹笛獨奏音樂的創作中,單一的南、北派風格的笛曲已經逐漸被多風格、多地域的笛曲所代替,并且創作出了《蒼》、《神曲》、《楚魂》、《愁空山》、《楚辭后奏曲》、《陌上花開》、《鷹之戀》、《梆笛協奏曲》等等大量現代的新型作品。這些作品大大豐富了竹笛的藝術表現力。笛子協奏曲《蒼》是這一階段的一首具有典型代表的現代作品之一。
作品《蒼》的創作之初衷是盡可能的開發笛子的演奏技巧及運用新的音樂語言。在笛子的技術上、音域上、區域上、演奏手法上都有很大的拓展和創新。
在創作方面,就其創作內涵,光曲名本身就可以理解為多層含義。樂曲主要以表現蒼勁、蒼涼、蒼茫為主。而從為學分析的角度來講,它還會體現蒼白、蒼松、蒼老、蒼天、蒼郁等等的意思。笛曲《蒼》究竟定位到其中的哪種意向呢?都是亦都不是。曲作者楊青曾表示:演奏者心理想著何意就為何意。因此,演奏者在表演時可以根據自己的體會進行二度創作,使樂曲的表現形式突破傳統笛曲的單一而更加多元化。樂曲以湖南民謠為素材,是一部運用傳統民間素材與現代的作曲技法相結合的作品,主要采用了對稱性以及復調性手法。作品的曲式結構為復三部曲式結構{引子﹢第一部分(樂隊A樂段﹢笛子B樂段)﹢第二部分快板﹢華彩﹢A再現}。引子部分,作者一開始就采用了和聲疊置,短促有力,引出了笛子的散板;華彩部分,作者將笛子的技術運用到了極致,笛子達到三個八度的超高音、氣吐音與笛聲相結合、笛喉雙音等等。而且基本上笛子所有的半音都用上了,再現部分,主題動機發展了三次,每次的感情色彩都不一樣。作曲家在全曲的創作中大量借鑒西方創作手法,結合中國湖南的民間音調,使樂曲風格獨特、新穎,既有濃厚的民族民間風味,又融合了西方的音樂元素。
在演奏方面,作品《蒼》的諸多超高音對演奏者來說無疑是一種挑戰,它將笛子的音域拓展到三個八度,大大豐富了樂曲的藝術表現力。在樂曲進行中,出現獨奏與伴奏進行復調對位的演奏,給人感覺耳目一新。在華彩部分出現的超多半音,氣吐音與笛聲相結合的演奏以及喉音與旋律的雙音進行等都為笛子增添了新的藝術表現形式。
《蒼》這首作品的成功,不僅因為動機從民族、民間出發,使音樂語言親切流暢,現代作曲技法的運用使音樂具有創造性,還因為演奏者們可以從樂曲中提高演奏技術,豐富演奏手法,更能從其中提高藝術的表現。《蒼》的個性十分鮮明,豪放粗狂,情感豐富,充滿詩意而且各部分對比十分強烈。因此《蒼》是演奏家和聽眾非常喜愛的一部作品,同時也為民族音樂的創作添上了絢爛的一筆,是一部具有時代精神的作品。
我們只有首先超越傳統,才能獲得無限發展的可能性。隨著竹笛藝術的不斷發展,為了使笛子也能精確的演奏十二平均律,因此在竹笛的形制也進行了有益的改革,出現了八孔笛、十孔笛,甚至出現了模仿西洋管樂長笛的加鍵笛等。民族樂器只有在不斷克服自身不足的基礎上自我完善,才能真正有能力,有實力與世界音樂接軌。音樂作品與其他文學一樣,須建筑于“民族性”之上不能強以西樂代庖,也絕非枝枝節節從西洋音樂搬點知識進來所能奏效。笛子演奏具有中國特色的作品是我們的目的,這是我們民族情感中不能舍棄的。
從1949年到現在,中國竹笛表演藝術由民間到專業,由單一到多元,這50年的發展其速度與變化,在竹笛音樂發展上是史無前例的。這些成果與前一輩的竹笛演奏家、教育家、作曲家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展望外來,我個人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世界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滲透,竹笛的藝術發展也要與時俱進,跟國際接軌。
任何一門藝術的發展與成熟,需要幾代人的努力,竹笛演奏在中國已延續了幾千年,在它身上積累了深厚的文化內涵與底蘊。在保留其精華的前提下,將這門藝術發展到一個更高的階段,使這一特色鮮明的樂器發揮初更大的魅力,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