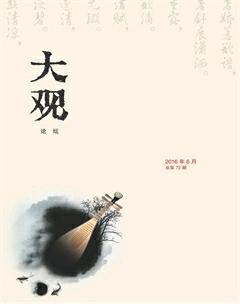淺析唐代的飲食文化
馬瑞祾
摘要:唐朝為中國歷史上最為繁盛的朝代之一,其飲食文化也頗有特色。唐朝國力強盛,經(jīng)濟發(fā)達(dá),文化繁榮,對外交往頻繁,宗教信仰自由,所以,唐朝的飲食文化十分興盛。在揚州、長安、洛陽、廣州等大城市里,“街店之內(nèi),百種飲食,異常珍滿。”不同地區(qū)、不同國家的水陸珍饌,應(yīng)有盡有。由于統(tǒng)治者的推崇,道教對于唐朝的飲食文化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唐朝的飲食也出現(xiàn)了。唐朝飲食文化與外國飲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呈現(xiàn)出一幅豐富多彩的圖景,奠定了中華民族傳統(tǒng)飲食生活模式的基礎(chǔ)。
關(guān)鍵詞:唐代;飲食文化;道教;風(fēng)尚
一、唐代飲食文化魅力
當(dāng)雄才大略的唐太宗開啟“貞觀之治”以后,唐王朝的鼎盛時期開始了。富裕風(fēng)流、無憂無慮的生活環(huán)境,開放流暢的中外文化交流,自由開明的仕進(jìn)方式,自由自在的言論條件,使整個社會充斥著一種恢宏自豪、開朗奔放的氣氛。在這種寬松優(yōu)越的文化發(fā)展環(huán)境下,唐人的自信心和創(chuàng)造力,很快便在沒有意識形態(tài)束縛的飲食文化領(lǐng)域得到了酣暢淋漓的自由發(fā)揮。“無問貧富之家,教女不以針縷績紡為功,但躬厄廚、勤刀機而已,善釀釀姐鮮者,得為大好女矣。……故偶民爭婚聘者相與語日:‘我女裁袍補襖,即灼然不會,若修治水蛇黃鱔,即一條必勝一條矣。”[1]崇尚烹調(diào)技藝的民俗民風(fēng),帶來了發(fā)達(dá)的飲食文化,即使安史之亂以后的揚州城,依然是“街店之內(nèi),百種飲食,異常珍滿。”而唐朝的飲食文化魅力就在于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脫俗的藝術(shù)造型,眾所周知“民以食為天”。我國自古以來就重視烹調(diào)技藝,故飲食之考究、烹調(diào)技術(shù)之高超,很早便聞名世界。飲食文化發(fā)展到唐朝,人們已不再單一追求飲食的食用功效,而是在保持飲食的主體功能的同時,更加注重飲食的藝術(shù)欣賞功能和養(yǎng)生保健功能。所以,唐朝的飲食造形十分優(yōu)美,不僅色、香、味俱佳,而且具有很高的藝術(shù)欣賞價值,令人賞心悅目,食欲大增。同時唐朝也是一個透明度較高的社會,人們的思想開放,衣著開放,生活開放,所以,唐人的飲食制作,也極力追求一種冰清玉潔的透明效果。唐人的飲食質(zhì)量高低、烹調(diào)技術(shù)的好壞,其光潔透明的程度乃是一個重要標(biāo)準(zhǔn)。故唐人的高級饌食,習(xí)慣稱為“饌玉”;肉白如雪的生魚片,習(xí)慣稱為“玉魷”;檔次較高的美酒,習(xí)慣稱為“玉液”。李白在《將進(jìn)酒》一文中寫到“鐘鼓饌玉不足貴 但愿長醉不復(fù)醒。”里的“饌玉”即是指珍美如玉的食品。第二是出神入化的烹調(diào)技藝,中國古代烹調(diào)菜肴的方法極多,炯、煮、燒、烤、烙,燙、炸、蒸、脯、腌,這些方法在秦漢時期已差不多全部出現(xiàn),而這些烹調(diào)方法的技術(shù)改進(jìn)、內(nèi)在質(zhì)量提高,則是在隋唐時期完成的。以最常見的膾為例,也許更能說明從秦漢至隋唐烹調(diào)技藝的不斷深進(jìn)。膾是細(xì)切的魚、肉。春秋時期,孔子《論語·鄉(xiāng)黨》已提出“食不厭精,膾不厭細(xì)”的主張。由于自由流暢的國際交流,世界各國人民的飲食精華都被介紹到了大唐帝國,唐人在廣泛借鑒他人烹調(diào)技藝的同時,也改進(jìn)或更新了傳統(tǒng)的烹調(diào)方法。作為面食文化的發(fā)展中心,四川的面食加工技術(shù)真可謂一枝獨秀。第三是食療兼顧的奇妙功效,由于統(tǒng)治者的推崇,道教對唐代飲食文化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而道教“羽化升仙,長生不死”的養(yǎng)生理念使唐朝的飲食文化帶上了濃厚的養(yǎng)生色彩,食治也成為去病強身的一種優(yōu)先選擇。食治表現(xiàn)在飲食文化上,其一是藥膳業(yè)的發(fā)達(dá),其二是藥酒的數(shù)量品種大量增加,其三是注重探索飲食規(guī)律。唐人用來食治的藥膳有兩種:一種是給沒有病的人強身、美容、保健的藥膳,它由純粹的糧食、蔬菜、水果、肉酪等食物構(gòu)成。寬松的文化發(fā)展環(huán)境帶給人類的決不僅僅是廣闊的思維空間,而且包括自信心、想象力和思維靈感,這便是唐朝飲食文化光彩魅力的源泉。
二、飲食文化繁榮發(fā)展的原因
眾所周知,一個民族飲食生活習(xí)慣的形成,有其社會根源和歷史根源。在中國古代社會,由于各民族的歷史背景、地理環(huán)境、社會文化及飲食原料的不同,各民族的飲食習(xí)慣就有明顯的差異。唐朝飲食文化快速發(fā)展,歸因為以下三點:一、經(jīng)濟繁榮,為飲食文化發(fā)展尊定基礎(chǔ);經(jīng)濟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唐朝時期,國家統(tǒng)一、強盛,交通發(fā)達(dá),陸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比較暢通,多個因素促進(jìn)了唐代經(jīng)濟的飛速發(fā)展。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統(tǒng)治者始終堅持較為寬松的統(tǒng)治政策,國內(nèi)各民族交往密切,互通有無,國外同日本、印度、西域等地區(qū)經(jīng)濟交往頻繁,使得唐朝經(jīng)濟空前的繁榮。二、文化昌盛,推動飲食文化的發(fā)展;唐朝時期,中國文化輝煌燦爛,士民階層興起,唐朝統(tǒng)治者推行開明、兼容的文化政策,國內(nèi)唐詩的快速發(fā)展與壯大、繪畫科技等方面取得進(jìn)步、各民族間文化交流、融合。國外頻繁的交往,在文化上吸收外來的優(yōu)秀成分以及繼承發(fā)揚了歷代的傳統(tǒng)文化,使得唐朝的飲食文化更進(jìn)一步繁榮。三、民族大融合,飲食文化兼容并蓄;唐朝統(tǒng)治者“胡同為一家”的理念使得生活在內(nèi)地的華夏民族,盡管在飲食上有鮮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但由于中華文化強大的包容性,不同民族間的文化不斷交融,飲食文化也不例外。同時,還反映了一個民族的飲食習(xí)俗,是植根于該民族的自然環(huán)境和飲食原料之中的,受一定的經(jīng)濟狀況所制約。
三、道教對唐代飲食的影響
唐朝建立后,統(tǒng)治者因為自己姓李,于是將老子李耳追命為李唐王朝的始祖,倍加推崇道教,使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極大的發(fā)展,成為僅次于佛教的重要宗派。因此,一些道教的習(xí)俗風(fēng)靡了全國,道教對唐代的飲食也有了深刻的影響。表現(xiàn)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魚、肉在飲食中受到多方限制;道教的教規(guī)對信徒的日常飲食有嚴(yán)格的約束,禁食葷腥是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唐朝統(tǒng)治者為了追尊道教,將道教的禁忌推行全國,使全國百姓都以此為約束。734年十月特下令“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宜禁斷宰殺漁獵”。這樣,大唐的百姓即使不信教,也必須遵循此制,前后食素三天。道教經(jīng)典中認(rèn)為龍多為鯉魚轉(zhuǎn)化而來,神圣不可侵犯,食之者將遭遇大禍,加之“鯉”與“李”諧音,唐代統(tǒng)治者于是嚴(yán)禁捕殺食用鯉魚。731 年正月唐玄宗下令“禁捕鯉魚”[2],凡捕得鯉魚者必須放生,街市有販賣鯉魚者杖六十[3]。推而廣之,唐代統(tǒng)治者更是制定出一系列條例,限制釣魚食用,將禁食鯉魚推廣到限食一切魚蝦。因此,在唐代魚類經(jīng)常成為難入肴饌的珍稀。第二,道教名詞在菜肴中頻繁出現(xiàn);道教名詞頻繁地出現(xiàn)在飲食、菜肴之中的情況在唐代前基本沒有,然而在唐代的菜譜中卻經(jīng)常出現(xiàn),形成一種時尚。用道教名詞命名食品、菜肴大體可分為如下三類:直接稱之為道人的,如 “菊道人”;用“神仙”、“仙人”命名,如 “玉桂仙君”、“仙人鸞”、“八仙盤”、“神仙粥” 等等;用道教傳說或典故命名。道教講求長生不死,所謂仙,按照《釋名·釋長幼》的解釋是“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按照這一說法,唐人食品、菜肴中便產(chǎn)生了許多以“長生”、“長命”來命名的肴饌,如“長生粥”、“長命面”等等。第三,道教節(jié)日及節(jié)日飲食習(xí)慣引入民間;由于統(tǒng)治者對道教的推崇,道教節(jié)日在唐代頗為流行,節(jié)日的飲食習(xí)俗也被帶入了民間。道教將上元、中元和下元分別作為天官、地官和水官大帝的生日,稱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唐代統(tǒng)治者將三元節(jié)進(jìn)一步推廣,下令民間百姓也必須遵守三元日食素并且禁捕殺漁獵的規(guī)定。今天上元節(jié)即元宵節(jié)吃元宵的習(xí)俗在唐代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第四,道教養(yǎng)生食品深入人心,道教講求養(yǎng)生,這個部分上文也有提到,道教煉制并服食丹藥是其修煉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平時的飲食也特別講求營養(yǎng)。受這種道家飲食習(xí)慣的影響,唐代人無論是炊飯、烹茶、釀酒都喜歡在其中放入一些草藥及營養(yǎng)價值較高的物品。這成為唐代飲食文化的一大特點。
四、飲茶與飲酒風(fēng)尚
提及唐朝的飲食,除了日常吃的食物外,兩種飲品也是唐朝最具特色的的飲食文化代表。首先談的是唐朝的茶文化,茶神陸羽撰寫的《茶經(jīng)》就是唐代茶文化的代表,唐朝茶文化的形成與當(dāng)時的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相關(guān)。唐朝疆域廣闊,注重對外交往,長安是當(dāng)時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國茶文化正是在這種大氣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形成還與當(dāng)時佛教、科舉制度、詩風(fēng)、貢茶有關(guān)。唐朝陸羽自成一套的茶學(xué)、茶藝、茶道思想,及其所著《茶經(jīng)》,是一個劃時代的標(biāo)志。《茶經(jīng)》非僅述茶,而是把諸家精華及詩人的氣質(zhì)和藝術(shù)思想滲透其中,奠定了中國茶文化的理論基礎(chǔ)。唐朝是以僧人、道士、文人為主的茶文化。佛教文化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中國佛教二千多年來的歷程,佛教中國化的歷程。它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哲學(xué)、倫理、文學(xué)、藝術(shù)和茶文化等廣泛領(lǐng)域。唐朝佛教尤其是禪宗對飲茶風(fēng)尚的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1.促進(jìn)了茶葉生產(chǎn)的大發(fā)展。我國寺院多建造在深山幽谷森林繁茂,云霧繚繞,雨量充沛,土層深厚最適宜茶樹生長的山區(qū)。而且我國是茶的原產(chǎn)地,崇山峻嶺原有大量野生茶樹,為僧侶開辟新茶園創(chuàng)造了條件,故素有“天下名山僧侶多”,“自古高山出好茶”的諺語。寺院廣種茶樹,也促進(jìn)了民間茶園的發(fā)展。2.推動了茶葉技術(shù)的進(jìn)步。劉禹錫貶朗州司馬時,親眼看到西山寺僧人創(chuàng)造了一個茶葉新品種,寫了一首贊美詩:“山僧后檐茶數(shù)叢,春來映竹抽新茸……斯須炒成滿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新芽連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傾余”。陸羽創(chuàng)造的是蒸青餅茶,社會上飲用的也都是這種茶,而西山寺僧人則創(chuàng)造了炒青散茶,佐證常德是我國炒青綠茶的發(fā)祥地。3.皎然率先提出了“茶道”這個詞。他不但專攻佛經(jīng),而且對茶文化造詣很深,有許多獨特的見解,“茶道”一詞就是他在《飲茶歌誚崔石使君》一詩中創(chuàng)造性的率先提出,詩曰:“……熟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三飲”神韻相連,層層深入扣緊,把禪宗“靜心”、“自悟”的宗旨以“滌昏寐”、“清我神”、“便得道”貫穿到茶道之中,是詩化了的茶道。茶中有道,悟茶也悟道,把飲茶從技藝欣賞提高到精神享受,我認(rèn)為佛教對茶道的影響,主要是禪宗思想的影響。皎然把茶道與佛理結(jié)合起來,是他的一大貢獻(xiàn)。唐代不僅在內(nèi)地飲茶成風(fēng),而且迅速向周邊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傳播,“自中地,流于塞外”。殊不知唐代文人嗜酒特甚,有關(guān)詩文也特別多,因此唐代的“酒文化”是別具一格的。就中唐初的王績,算得是一個先鋒。王績長期棄官在鄉(xiāng),縱酒自適,他所作待文多以嗜酒為題材,其中有一篇《醉鄉(xiāng)記》,將歷來的嗜酒文人稱作酒仙,以為榜樣。文中道:“……阮嗣宗、陶淵明等十?dāng)?shù)人并游于醉鄉(xiāng),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云。嗟乎,醉鄉(xiāng)氏之俗,豈古華召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得游焉。”大凡把酷好飲酒且替飲酒的人稱之為“酒仙”。自從有了“酒仙”的美稱之后,酒仙便層出不窮。唐代中期就有“酒八仙”之說,稱嗜酒的賀知章、李適之、崔宗之、蘇晉、李白、張旭、焦遂八人為“酒仙”。八仙中嗜酒最著名的當(dāng)然是李白。李白愛酒,他的酒詩也相當(dāng)多,其中有許多名篇,《月下獨酌》就是佳作之一,還有那一曲千古絕唱《將進(jìn)酒》,雖說從某種程度是宣揚了一種及時行樂的消極情緒,但實際上也是詩人心靈深處回蕩著的一曲痛苦悲歌:“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fù)回。君不見堂明鏡悲白發(fā),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fù)來。……”李白把自己的愁悶痛楚,恨不得都消釋在酒中,沒有酒就不會有他的佳作,也就不會有他的生活。他的《把酒問月》詩,表達(dá)的正是一種寄情于酒的愿望:“所愿當(dāng)歌對清酒,月光長照金樽里。”還有那首《客中行》,也表達(dá)了詩人同樣的心境。傳說李白最終因酒而死,那是在他大醉之后,下到采石磯大江中捉月,結(jié)果被江水吞沒了生命。唐代文人飲酒,極重花前月下之酌,李白的《月下獨酌》即其一例。這實際上是詩人孤獨寂寞境遇的寫照,不僅在“月下”,而且為“獨酌”,沉悶的心緒因酒而消散,隨月而飄去。當(dāng)然,也難免會有“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的時候,那就很難得到解脫了。這是一門我們所獨有的與眾不同的文學(xué),十分了不起。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值得驕傲的過去!
唐朝因為其繁榮強盛的國力致使了文化極度的絢爛,飲食文化作為文化范疇的一種自然也具有其獨特的魅力。唐朝的飲食文化不僅如此,還有許多需要去挖掘,這就是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源遠(yuǎn)流長魅力的所在了吧!
【參考文獻(xiàn)】
[1]房千里.投荒雜錄[普通古籍]:一卷[M].上海:國學(xué)扶輪社,1915.
[2]劉昫.舊唐書·玄宗紀(jì)上[M].北京:中華書局,1975
[3]段成式.酉陽雜俎校箋(套裝1-4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