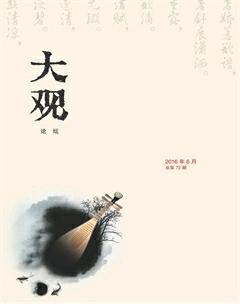奇觀與儀式
呂航
摘要:隨著越來越多節目的出現,原先在社會生活中不被人們所關注的點和面被節目制作者發掘出來,在迎合觀眾收視特點的同時,也在積極引導、體現當下社會的價值觀,以期達到“奇觀”效應。傳承了上千年的傳統技藝作為我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集民族文化、精神價值、宗教信仰、身份認同等多種元素于一身,《傳承者》將這些上千年的傳統技藝進行聚合,將眾多散點聚合成一個具有“奇觀”效應的媒介儀式。
關鍵詞:真人秀;奇觀
道格拉斯·凱爾納在其著作《媒體奇觀》中對“奇觀”一詞進行了闡釋,所謂:“奇觀”,指那些能體現當代社會基本價值觀、引導個人適應現代生活方式、并將當代社會中的沖突和解決方式戲劇化的媒體文化現象,包括媒體制造的各種豪華場面、體育比賽和政治場面等。”在消費主義盛行的今天,節目同質化現象日趨嚴重,要制作一檔成功的娛樂節目,首要的就是突破既有的題材,能滿足觀眾的好奇心。題材選擇要足夠吸引眼球,足夠與觀眾的生活經驗和閱讀經驗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是成功的電視節目亙古不變的生存法則。成功電視節目的題材必須足夠“奇觀”,足夠吸引觀眾眼球,。
一、對于觀眾的思維引導
《傳承者》采用闖關模式層層選拔技藝傳承人,以綜藝節目的形式,令“高冷”的傳統文化更具有“人氣”和吸引力,“另類”的競爭賽制既與傳統文化傳播節目相區分,更充滿緊張刺激的氣氛,令觀眾在“玩”中學習,令傳統文化在“潛移默化”間得到傳承。
《傳承者》以最接地氣的形式賦予了傳統文化全新的外衣,讓枯燥的文化內涵以娛樂化、競技化的形式展現給大眾,既易于傳播,更符合青年人的胃口。如今很多千年技藝面臨繼承尷尬,古老的手藝后繼無人,傳統技藝要想在現今社會得到生存與發展,不能只靠政策“扶”,還要根據自身特點進行適應現代社會消費特點進行改造以“自救”,有消費才會有市場,有市場才會有傳承,《傳承者》恰好為瀕臨失傳千年古技法提供了一個進行宣傳和改造的自救平臺:一是通過競技的形式使得節目更有看點,使得傳統技藝被更多人關注;二是通過現場表演的形式使得節目傳承者對技藝進行主觀能動地改造,使得節目更加符合現今人們的審美、消費需求;三是通過四位導師和十位青年團的現場討論、辯論,將傳統技藝的改進放在現今社會語境下,為其找出路、謀發展,更是拔高了節目的社會、文化內涵。
二、對于奇觀題材的追求
首先是項目奇觀。以2015年12月18日晚那一期中的《敖魯古雅》為例。《敖魯古雅》是鄂溫克族使鹿部落的一首經典民歌。鄂溫克族是東北亞地區的一個民族,使鹿部落是鄂溫克族一個部落,以 “馴鹿文化”聞名中外。鄂溫克族沒有文字,所以他們喜歡用歌聲書法心中的喜怒哀樂,民歌幾乎是鄂溫克族文化的唯一載體。部落94歲的女老酋長瑪利亞.索是知道鄂溫克族民歌最多的人。這期節目中,她為傳播鄂溫克族傳統文化來到了現場,老額娘親自現場演唱一首使鹿部落民歌,對在場所有人表達了祝福。政府早在十多年前就在山下建立了定居點,但索老額娘為了鄂溫克族的馴鹿文化至今仍居住在四面透風、寒冷潮濕的“撮羅子”里保持著原始的“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習慣。像這樣感人肺腑的傳承故事,《傳承者》的舞臺上還有很多很多。
其次是包裝奇觀。《傳承者》節目顛覆了傳統“達人秀”式的單一評判方式,用青年團與導師團爭鳴探討的形式營造了前所未有的創新形態,制造了代表年齡跨度的全新代際話語場。文化類節目本就是各種文化思想交流和碰撞的舞臺,《傳承者》的語態中既有體現主流意識的文化自覺,也有體現青年人思維敏捷、熱衷商榷、個性獨特的文化放松,可謂多元差異。
最后是視覺奇觀。《傳承者》是北京衛視聯合能量傳播打造的一檔“綜藝大片”,現場轉播技術、燈光、音響效果、舞美都是一流水準。以舞美為例,開場布局無數藍色燈柱與紅色布景呼應,絢爛無比,每個節目都是現代技術與古代藝術的結合,讓觀眾在觀看節目的同時感受到濃郁的傳統文化氣息。
三、對于儀式和觀眾自身身份認同的構建
傳承了上千年的傳統技藝作為我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集民族文化、精神價值、宗教信仰、身份認同等多種元素于一身。《傳承者》將這些上千年的傳統技藝進行聚合,將眾多散點聚合成一個具有“奇觀”效應的媒介儀式。
“儀式作為最能體現人類本質特征的行為方式與符號表述,在人類生活中占據著極為重要的位置。”儀式伴隨著人類的發展而不斷地進行演變與變遷,古代的巫術、舞蹈、祭祀等儀式形態喻示了人們在落后的生產生活條件下為求生存而尋找精神寄托的強烈愿望和表達;古代的生產生活方式隨著時代的發展不能適應人們生產生活的需要,因而逐漸消失甚至失傳,成為傳統技藝,成為一種包含著它所處年代映射、承載著對家園對過去的儀式成為人們的精神寄托。而在人們進入后現代社會以來,電視發揮了重要的社會功能,曾經“分化的個體”“孤獨的個人”通過電視節目找到了相互聯系的紐帶,投射了共同的精神情感與價值信仰,找到了社會群體的認同,加深了身份、民族的歸屬性。涂爾干認為:“有必要按時定期的強化和確認集體情感和集體意義,只有這種情感和意識才能使社會獲得統一性和人格性。這種精神的重鑄只有通過聚合、聚集和聚會等手段才能實現,在這些場合個體被緊密結合起來,進而加深他們的共同情感,于是就產生了儀式。”在《傳承者》節目中,各民族、各種傳統技藝集中展現,讓各民族、各年齡段的觀眾在集體欣賞的同時領略傳統文化的魅力,并感受群體意識,民族精神。節目經過精心策劃、編排和制作,讓種種傳統技法集合成了儀式化的媒介事件,在吸引觀眾注意的同時也激發了觀眾的想象力和參與欲望,而競爭的賽制也讓節目本身具有的懸念性加劇了“儀式化”的表演性,聚合了廣大觀眾,凸顯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意義。
四、結語
隨著時代的發展,傳統技藝所包含的傳統生產生活方式已經與現代大眾漸行漸遠,傳統技藝更像是“熟悉的陌生人”,存活在老一輩的記憶中,《傳承者》將種種具有儀式性的傳統技藝集合起來,形成更大規模的儀式效應,喚醒傳統技藝乃至傳統文化中民族的認知和個人身份的認同,同時也將瀕臨滅絕的傳統技藝以現代化的視角進行分析和展望,不僅讓其“活下去”,還要推動其“走出去”。
【參考文獻】
[1]楊建.奇觀視野下真人秀的消費主義解讀[J].傳媒觀察,2016(03).
[2]謝耕耘.真人秀節目:理論、形態和創新[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3]李立.媒體奇觀的文化密碼——真人秀電視節目的游戲規則研究[D].四川大學,2008.
[4]許金磚,李懷仙.奇觀與欲望——從傳媒文化角度解讀明星跳水節目[J].現代視聽,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