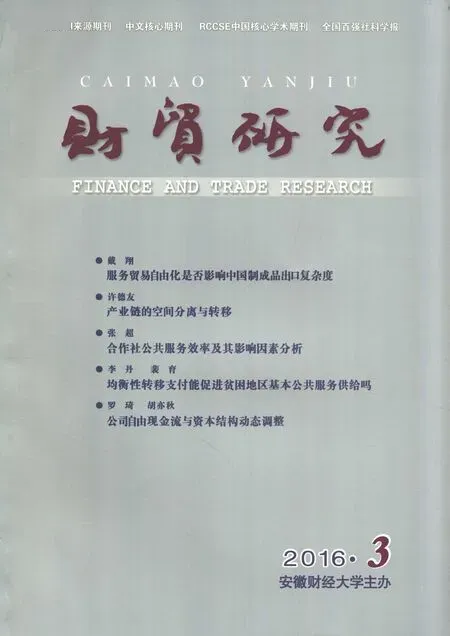企業融資約束、退出與資源誤配
黎日榮
(暨南大學 經濟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2; 浙江樹人大學 浙江省現代服務業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15)
?
企業融資約束、退出與資源誤配
黎日榮
(暨南大學 經濟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2; 浙江樹人大學 浙江省現代服務業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15)
摘要:在理論模型分析的基礎上,得出融資約束通過兩個渠道增加企業的退出風險:一是流動性約束;二是使用外部資金需要支付融資成本,這會提高企業退出的臨界生產率,從而提高企業的退出風險。信貸市場效率的提高使得企業融資成本降低,迫使低生產率企業退出市場。進一步,使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進行的實證檢驗表明:融資約束確實增加了企業的退出風險;隨著融資約束程度的增加,企業的退出風險加速遞增;信貸市場效率的提高增加了低生產率企業的退出風險,隨著生產率的上升,企業的退出風險顯著下降。因此,信貸市場效率提高會優化經濟中的資源配置。
關鍵詞:融資約束;生產率;企業退出;資源誤配
一、引言及相關文獻回顧
Melitz(2003)通過生產率的異質性解釋企業退出及出口行為的差異性,認為生產率最高的企業進入出口市場,生產率次之的企業僅在國內銷售,生產率最低的企業退出市場,并且隨著高生產率企業的進入和低生產率企業的退出,資源將得到優化配置。然而,Melitz(2003)并沒有考慮企業融資約束的差異,在考慮融資約束后,企業退出并非唯一依生產率次序,融資約束同樣會產生影響。由于融資約束,退出企業并非是生產率最低的,這破壞了市場經濟的優勝劣汰機制,使“創造性毀滅”作用無法有效發揮,經濟中存在資源誤置。此現象在金融市場改革和發展滯后于產品市場的中國更為典型(Huang,2010)。
中國的金融體系以銀行為基礎,而國有銀行又占據著信貸資源的大部分,通過對歷年《中國金融年鑒》的數據統計可得,1998—2004年工行、中行、建行和農行四大國有銀行的貸款占全國貸款的57.3%。國有銀行在信貸資金配置時會優先考慮國有企業,導致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Boyreau-Debray et al.,2005)。Dollar et al. (2007)、Riedel et al.(2007)均發現,私營企業投資資金主要來自留存收益、家庭或朋友借款,只有很少部分來自銀行信貸。Song et al.(2011)指出,國有企業的投資資金中有多于30%來源于銀行信貸,而私營企業的這一比例少于10%。由此,私營企業普遍面臨融資約束的困境。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中國有75%的非金融上市企業將融資約束視為企業發展的主要障礙,在被調查的80個國家中比例最高(Claessens et al.,2006)。同時,本文對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1998—2006年的數據統計也表明,全部樣本企業的年平均退出比率為16.3%,其中,國有企業為22.8%,規模以上非國有企業為15.2%,規模以下非國有企業將有更高的退出比率*從本文的表1可以看出,小企業的退出概率遠比大企業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著重考察的問題為:融資約束是否會影響企業的退出行為?融資約束通過什么機制影響企業的退出行為?融資約束是否會導致經濟中的資源誤置?
研究企業退出行為的實證文獻并不多見。Disney et al.(2003)分析了企業規模、年齡對英國工業企業退出的影響。Falck(2007)研究了區域條件、產業特征以及企業層面的規模、成長率、研發等對德國私營部門新生企業生存概率的影響。Yang et al.(2012)考察了改革對中國遼寧省機電制造企業退出的影響。Lee et al.(2015)探討了商業周期對美國企業進入與退出的影響。Eslava et al.(2013)分析了貿易自由化對哥倫比亞企業退出的影響。簡澤等(2013)分析了銀行部門的市場化對中國企業退出的影響。馬光榮等(2014)分析了地區金融契約效率對中國企業退出的影響。簡澤等(2013)、馬光榮等(2014)的研究均聚焦于金融部門的市場化進程對企業退出行為的影響。但總體來看,目前鮮有文獻深入微觀層面考察企業融資約束對企業退出的影響,尤其是針對中國工業企業的分析。
本文的貢獻主要在于:一是分析融資約束對企業退出的影響機制,認為一方面企業使用外部資金需要支付融資成本,這會提高企業退出的臨界生產率,增加企業退出的風險;另一方面當企業面臨流動性約束時,金融市場摩擦可能使企業無法及時融入生產成本,這也會增加企業退出的風險。二是提煉了融資約束、企業退出與資源配置的幾個典型事實,發現退出企業普遍面臨嚴重的融資約束,退出企業遠非是生產率最低的,市場機制將通過減少低生產率企業的市場份額使資源得到優化配置。三是使用中國微觀企業數據檢驗了融資約束、信貸市場效率對企業退出的影響,發現融資約束確實增加了企業退出的風險,并且隨著融資約束程度的增加企業退出風險加速遞增;信貸市場效率提高增加了低生產率企業的退出風險,隨著生產率的提高,企業退出風險顯著降低,因此,信貸市場效率的提高將顯著減少經濟中的資源誤配。
二、理論模型
(一)企業生產問題


(1)
Vc(x)為繼續生產的價值,它是最大化各期分紅的現值之和;Ve(x0)為企業退出市場的價值。其中:
(2)

(3)

于是有:
(4)

(二)企業退出決策
假定當企業退出市場時,企業家在下一期有概率為σ的可能性創辦一個新企業。由式(2)知,Vc(x)關于k、b、cf為連續可微函數。于是假定新創辦企業的值函數為Vc(0,0,0,w0),其中,w0為新創辦企業的初始生產率,由企業家的才能決定,對既定的企業家,w0、x0為既定。企業退出市場的值函數為:
(5)
企業依以下順序作出決策:在期初,有比例為λ的企業由于外生性沖擊退出市場,所有剩余的企業確認當期的生產率沖擊w,狀態為x的企業在期末決定是否退出市場。若退出,它的債務清零,同時企業家失去企業;若繼續生產,企業選擇一個貸款和資本投入量,以及投入固定生產成本進入到下一期。滿足以下兩個條件中的任一條均導致企業退出市場:
條件一:企業退出的價值大于留在市場的價值,即:
Ve(x0)>Vc(x)
(6)
由式(2)知,Vc(x)關于貸款利率R′為單調減函數,由式(4)知,R′為生產率的單調減函數;再結合式(2)中的生產率可知,Vc(x)是生產率w的單調增函數。式(6)左右兩邊相等時將產生企業退出的臨界生產率w*,生產率低于該值的企業退出市場。我們稱在融資約束下企業生產率低于臨界生產率而退出市場的約束為盈利性約束。
條件二:式(3)所表示的非負分紅約束沒有得到滿足,即:
g(x)<0
(7)
由g(x)的表達式可知,即使企業當前利潤達不到非負分紅條件,企業依然可以通過增加外部融資(增加b′)獲得流動性來滿足非負分紅條件。故式(7)可以看作是企業的流動性約束。當企業的流動性沒有得到滿足時,企業被迫退出市場,即使企業的生產率大于臨界生產率。
由于Vc(x)是g(x)的單調增函數,所以無論是通過盈利性約束還是流動性約束,企業生產率、資本存量、負債和貸款固定成本對企業退出的影響機制都是一樣的。生產率通過兩個渠道影響企業的利潤:一是生產率越高邊際成本越低,企業的利潤就越高;二是企業的生產率越高,企業獲利的可能性就越高,在銀行看來企業退出的風險就越小,企業貸款利率就越小,融資成本就越小,利潤就越高。企業的利潤越高,企業的價值和流動性就越高,退出風險就越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說1:企業的生產率與企業的退出風險負相關。
由式(4)知,貸款利率R′是貸款固定成本cb的單調增函數,于是Vc(x)、g(x)是cb的單調減函數,信貸市場越有效率,貸款固定成本就越小,企業的融資成本就越小,利潤就越大,退出風險就越小。然而必須注意到,這種作用僅僅發生在高效率的企業。隨著金融市場摩擦減少,銀行收集企業的信息越來越方便,其只需花費很少的固定成本就能甄別出低效率高風險的企業,從而對這類企業設定更高的貸款利率,提高了低效率企業的融資成本,增加了它的退出風險。在實證中我們使用信貸市場效率作為貸款固定成本的代理變量。于是,本文提出:
假說2:信貸市場效率提高會增加低效率企業的退出風險,隨著生產率提高,企業退出風險將顯著下降。

假說3:企業的負債資產率與企業的退出風險正相關。
Arellano et al.(2012)證明,在既定的金融發展水平、企業規模和生產率條件下,企業的貸款額存在一個上界,并非企業愿意接受更高的貸款利率,就一定能得到更多的貸款*具體證明過程,此處不作復述,可參考Arellano et al.(2012)。。原因在于,在既定企業規模和生產率以及貸款有限責任條件下,當貸款規模增加到一定程度時,企業的違約風險會加速增加,銀行預期到這種風險時,也會迅速提高貸款利率,從而使企業的融資成本加速增加,進一步提高了企業的退出風險。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在既定的資本存量規模k下,隨著負債b增加,企業的退出風險將加速遞增。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說4:企業的負債資產率對企業退出風險的影響并非線性的,而是隨著負債資產率的上升,退出風險加速遞增。
三、計量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一)計量模型設定
生存分析方法被廣泛應用于企業退出行為研究(Agarwal et al.,2001;Disney et al.,2003;Falck,2007;Yang et al.,2012),本文的實證分析亦采用此法。生存分析的核心概念為風險函數h(z),其表示在給定個體存活到時間z的條件下,事件發生在時間z的瞬時概率。本文所關注的風險事件為企業退出市場,把企業依然存留在市場定義為存活。盡管企業退出事件可以發生在連續時間的任何時刻,但我們所使用的工業企業數據是以1年為間隔單位度量的,本文的處理與Esteve-Pérez et al.(2013)類似,使用離散時間風險模型。具體地,令L表示企業存活在市場上的時間長度,L取值為一系列正整數z=1,2,3……。一個企業在市場上可能有完整的持續時間段(記為ci=1),也可能是右刪失的(記為ci=0),其中,i表示某個特定的持續時間段。企業在市場上的生存函數可定義為:
(8)

(9)
令yik表示企業退出市場的二值變量,當企業退出時取值1,否則取值0。當企業在第Li期退出時,此時ci=1,對于k=Li,yik=1,而對于k (10) 該表達式與二值被解釋變量回歸模型的對數似然函數是一樣的,因此包含時變量的離散時間風險模型可以用二值被解釋變量模型估計。本文與Esteve-Pérez et al.(2013)、毛其淋等(2013a)的做法類似,假定離散時間風險率hik服從互補雙對數(complementary log-log)分布,采用cloglog生存模型進行估計,模型設定為: c log log(1-hit)=β0+β1ln DAR+β2ln tfp+Xβ+φt+vt+vi+εit (11) 模型的被解釋變量為企業是否退出市場的虛擬變量,用Exit表示,當企業在第t期退出時,Exit=1,否則Exit=0。對于企業退出狀態的確認,本文的做法與Disney et al.(2003)、毛其淋等(2013b)相似,如果企業在第t-1期存在,第t期及之后均不存在,則確認企業在第t-1期退出市場*值得注意的是,在非國有工業數據庫只包括規模以上(銷售收入在500萬元及以上)的企業,有些退出工業數據庫的非國有企業有可能是由規模以上變為規模以下,而非直接退出市場,該數據庫提供的信息無法把它們有效識別,按已有文獻通常的做法(余淼杰,2010;李平 等,2012),我們依然把它視為退出市場;另外我們的分析表明企業規模萎縮是企業退出前的顯著征兆。。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企業融資約束。在實證分析中,負債資產率被廣泛用作融資約束的度量(Whited,1992;Harrison et al.,2003;Héricourt et al.,2009),該比率一方面反映了企業對外部資金的依賴程度,比率越高表明企業越依賴外部資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企業的融資能力,比率越高意味著企業可用的相對抵押品就越少,企業的融資能力就越弱。本文用負債總額與固定資產凈值的比率(取對數)ln DAR作為企業融資約束的代理變量,這也與本文的理論推導一致。使用OP法(Olley et al.,1996)估算全要素生產率(取對數)ln tfpop。式(11)中,X為控制變量,其中,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具體包括:企業規模,用資產總額的對數值ln asset度量;企業年齡(取對數)ln age;企業的資本密集度K intensity;國有企業虛擬變量SOEs。二位碼行業層面的控制變量包括:國內競爭度,用赫芬達爾指數HHI來度量;對外開放度openness,用行業的出口交貨值除以行業的工業增加值度量*工業數據庫缺少2004年的口出交貨值,我們用2003年和2005年的openness的均值作為2004年的openness。。i為企業標識,vt和vi分別表示年份特定效應和企業個體效應。hit表示企業i在時間t所面臨的退出風險。φt為基準風險率*我們把基準風險函數的形式設定為持續時間的自然對數ln t,出于節省篇幅,本文未報告該函數的回歸系數。。εit為隨機干擾項。 (二)數據說明 本文使用國家統計局1998—2007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二位碼為13—37、38—42共29個行業的數據,并依據Feenstra et al. (2011)的方法對其中不合理的觀測值進行剔除,最后使用1998—2006年共9年的數據*只使用1998—2006年數據,是因為2007年數據僅用于識別企業在2006年是否退出。。工業數據庫中每個企業都有自己的法人代碼,可以依此識別企業的退出狀況。然而,考慮到企業在樣本期內發生重組、所有權變更等活動,可能存在導致企業變更法人代碼,而實際沒有退出市場的情形。因此,簡單使用企業代碼識別企業退出狀況會高估退出概率,并不準確。本文借鑒Brandt et al.(2012)的方法,使用企業代碼、企業名稱、法人名稱、城市代碼、行業代碼、電話號碼以及它們的組合進行反復匹配以增加成功匹配的企業,降低企業的退出比率。本文計算出1998—2006年間,企業各年的平均退出比率在11%~23.7%之間,平均退出比率為16.3%,比毛其淋等(2013b)、李平等(2012)所得的退出比率稍低。表1是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數據統計說明:本表統一的時間跨度為1998—2006年。本文把國有企業之外的企業統一歸為非國有企業;把全部樣本按資本密集度以升序的形式排序, 25百分位之前的樣本定義為勞動密集企業, 75百分位之后的樣本定義為資本密集企業;同樣按總資產以升序的形式排序,25百分位之前的樣本定義為小企業,75百分位之后的樣本定義為大企業;把出口交貨值大于0的企業定義為出口企業,小于等于0的企業定義為非出口企業,工業數據庫缺少2004年出口交貨值,故對出口企業和非出口企業僅統計了1998—2003年和2005年、2006年共8年的均值。,從中可以初步看出,國有企業的平均退出比率比非國有企業高,非出口企業的平均退出比率比出口企業高,勞動密集企業的平均退出比率比資本密集企業高,小企業的平均退出比率比大企業高很多。 表1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三)融資約束、企業退出與資源配置的典型事實 本文首先考察企業在退出以及退出前的市場份額、生產率(ln tfpop)以及所受融資約束程度(ln DAR)的變化趨勢,因此對退出企業的這三個指標分別進行統計,結果見表2、表3和表4。統計方法如下:用企業的銷售收入計算企業的相對市場份額,如在表2中1999年退出的企業在1998年的相對市場份額為62%,其是用1999年退出的企業在1998年的平均銷售收入除以1998年全部企業的平均銷售收入計算而得。這表明1999年退出的企業在1998年的平均銷售收入僅為1998年全部企業平均銷售收入的62%。表3和表4中的相對生產率以及相對負債資產率計算方法與表2相同。由表2可以看出,企業在退出前相對市場份額存在明顯的萎縮趨勢;從表3可知,企業在退出前相對生產率存在明顯的下降趨勢。 表2 企業退出前的相對市場份額變化 (單位:%) 表3 企業退出前的相對生產率變化 (單位:%) 由此可得,企業在退出前存在明顯的衰退征兆。這也進一步驗證了Hopenhayn (1992)和Melitz(2003)的觀點,低生產率企業的規模將不斷萎縮,直至退出市場。由統計結果不難得知,企業在退出前其市場份額和生產率均有下降趨勢,這表明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上是有效率的,其通過減少低生產率企業的市場份額使資源配置得到優化。 表4 企業退出前的融資約束程度變化 (單位:%) 表5 融資約束與資源誤配 從表4可看出,企業在退出前融資約束緊度總體呈上升趨勢,盡管在1999年、2000年和2003年這一趨勢并不明顯。此外,除2003年退出的企業之外,退出企業在退出當年和退出前的兩三年平均融資約束緊度均比總體企業高,尤其是在退出當年明顯。這表明融資約束很可能是企業退出的原因之一。 表5列示了退出企業樣本組和最低生產率企業樣本組的生產率(ln tfpop)和融資約束(ln DAR)的均值。用于計算均值的樣本的選取辦法如下:1998年退出企業為19512家,這些企業組成退出企業樣本組;我們再選取1998年生產率最低的19512家企業組成最低生產率樣本組,其他年份的統計方法相同。總體上看,退出樣本組的生產率均值為1.74,比最低生產率樣本組的1.499要高出16.1%;退出樣本組的融資約束均值為0.636,要比最低生產率樣本組的0.54和全部企業樣本組的0.584分別高出17.8%和8.9%。由此可知,退出企業普遍面臨很高的融資約束,這進一步表明融資約束可能是企業退出的一個原因,同時退出企業遠非是生產率最低的企業。表5的結果表明,融資約束可能會導致高生產率企業退出,低生產率企業得以保留,從而造成經濟總體上的資源誤配。下文通過對數據回歸分析它們的因果關系。 四、融資約束與企業退出 (一)基準回歸結果 通過對式(11)模型的估計,可以得到表6的基準回歸結果,其中回歸系數已全部轉化為幾率比形式,系數大于1表明自變量和因變量存在正相關關系,小于1為負相關關系。從結果可見,ρ系數的P值均為0,表明該模型應該考慮企業個體異質性*由于樣本數據含有非時變變量,本文采用隨機效應處理企業個體異質性。。從回歸方程(1)可以看出,ln tfpop的系數為0.3379,這與Yang et al.(2012)、Eslava et al.(2013)所得的結果一致。這表明生產率ln tfpop提高1單位,企業退出風險會降低66.21%(0.3379-1=-0.6621),市場競爭總體上迫使低生產率企業退出市場。ln DAR的系數為1.057,表明融資約束ln DAR增加1單位會導致企業退出風險增加5.7%(1.057-1=0.057)。以上結果進一步證實假說1和假說3。其他變量對企業退出風險大多也有顯著的影響,但這不是本文關注的變量。 表6 融資約束與企業退出 注:括號內為穩健性z值;*、**、***分別表示顯著性水平為0.1、0.05、0.01;ρ為企業不可觀測異質性方差占總誤差方差的比例,對應括號內數值是它的P值;結果中“<1.0001”是指大于1小于1.0001,“>0.999”是指小于1大于0.999。 為了考擦融資約束是否對負債資產率不同的企業存在不同的影響,我們在回歸方程(2)中添加交叉項ln DAR×ln DAR。ln DAR和ln DAR×ln DAR的系數均大于1,表明對負債資產率高的企業,當融資約束增加1單位,企業退出風險增加更多。這也就意味著,隨著融資約束程度的增加,企業退出風險加速遞增,假說4進一步得以驗證。在方程(3)中,添加了融資約束與國有企業虛擬變量的交叉項ln DAR×SOEs。ln DAR和ln DAR×SOEs的系數均大于1,這表明融資約束對國有企業退出的影響更大。原因可能是,與非國有企業只包含規模以上企業相比,國有企業包含了所有規模的企業。小企業固定資產較少,能提供的有效抵押品也較少,融資成本較高,其退出風險受融資約束的影響更大,現實中由于融資困難資金鏈斷裂而破產的企業相當多,尤其是中小企業。在回歸方程(4)中,添加了融資約束與資本密集度的交叉項ln DAR×K intensity,然而該系數并不顯著。這表明融資約束對資本密集度不同企業的退出風險并沒有顯著差異的影響。在方程(5)*由于工業數據庫缺少2004年的出口交貨值,所以該回歸方程剔除了2004年的數據,僅使用剩下的8年數據。中,添加了融資約束與出口虛擬變量的交叉項ln DAR×Export,當企業出口交貨值大于零時Export取值1,否則取值0。結果顯示,ln DAR的系數大于1,ln DAR×Export的系數小于1。這表明融資約束對出口企業的退出風險影響更小。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出口企業很多為外資企業,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跨國企業在中國的分公司,這些企業容易從國外母公司獲得成本低廉的資金(李志遠 等,2013),不易受流動性約束;另一方面,進入出口市場的企業是生產率高的企業(Melitz,2003),高生產率有利于企業獲得低成本資金,拓展海外市場,增加利潤,降低退出風險。 本部分的實證分析結果與理論預測一致,即生產率與企業退出風險負相關,融資約束與企業退出風險正相關,并且隨著融資約束緊度的增加,企業退出風險加速遞增。 (二)穩健性分析 上文使用cloglog模型(假定風險率hik服從互補雙對數分布)對企業退出風險進行回歸,為了減少風險率設定對回歸結果的影響,我們再使用probit模型(假定風險率hik服從正態分布)和logit模型(假定風險率hik服從logistic分布)對企業退出風險進行回歸,并且分別考慮企業個體異質性和不考慮個體異質性兩種情況,所得結果均與表2中的方程(1)近似,這表明前文的結果是相當穩健的。限于篇幅,穩健性檢驗的結果不再詳細列出。 五、信貸市場效率與企業退出 (一)基準回歸結果 本文第二部分的理論分析認為,信貸市場效率的提高通過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從而降低高效率企業的退出風險,增加低效率企業的退出風險,使經濟中的資源得到優化配置。本部分實證檢驗這一假說,我們使用信貸市場競爭指數作為信貸市場效率的代理變量,構造方法如下:先計算某省份某年非國有銀行貸款占該省總貸款的比例*與《中國金融年鑒》劃分類似,本文把工行、中行、建行和農行劃分為國有銀行,其他銀行為非國有銀行,非國有銀行的貸款總額為省份的貸款總額減國有銀行在該省貸款總額的差,數據來自歷年《中國金融年鑒》。,再借鑒樊綱等(2011)的市場化指數編制方法,將其編制成以1998年為基年的指數形式,以使該指標在縱向和橫向更具可比性。地區信貸市場競爭指數FEIij的公式為: (12) 其中,i、j分別表示年份和省份,Rij表示省份j在i年非國有銀行的貸款占該省總貸款的比例,R1998,min為1998年非國有銀行貸款占比最小的省份的貸款占比,同理R1998,max為最大的貸款占比。使用非國有銀行在地區信貸中的份額作為信貸市場效率的理由有:一是在非國有銀行中股份制銀行資產所占的比例最大,周逢民等(2010)、王兵等(2011)、丁忠明等(2011)均發現,股份制銀行比大型國有銀行更有效率,因此非國有銀行貸款占比越高,表明市場越有效率;二是非國有銀行貸款占比越大,表明四大國有銀行的壟斷地位越不明顯,市場競爭就越充分,效率就越高;三是本文統計了1998—2006年四大國有銀行的平均存貸比率為72%,同期全國平均存貸比率為74.7%*數據來自歷年《中國金融年鑒》,因缺失2005、2006年工行的存貸款數據,故國有銀行存貸比統計中,2005、2006年不包含工行的數據。,由此也可知四大國有銀行的效率低于全國金融機構的平均水平。與第四部分的基準回歸一樣,這部分也使用去除企業個體異質性的cloglog模型進行回歸,除地區信貸市場競爭指數FEI外,回歸中的其他變量均與上文相同,結果見表7*由于缺失2005、2006年工行和中行分地區的貸款數據,故在回歸方程(1)、(2)、(5)和(6)中,本文僅使用1998—2004年的數據。。 值得注意的是,表7中方程(1)、(2)、(3)、(4)的回歸結果均轉化為幾率比形式。從回歸方程(1)可以看出,地區信貸市場效率FEI每增加1單位,企業退出的風險增加1.9%。在方程(2)中添加了信貸市場效率FEI與企業生產率的交叉項FEI_ tfp,發現信貸市場效率FEI每增加1單位,企業的退出風險會增加6.6%,但隨著企業生產率ln tfpop每增加1單位,其退出風險會下降2.6%,這一結果與馬光榮等(2014)近似。可見,信貸市場效率提高主要增加了低生產率企業的退出風險,可能是因為隨著信貸市場競爭趨于激烈,銀行在信貸資金發放時更注重風險和收益,使原來一部分低效率但可以通過超經濟聯系在信貸市場上得到低成本資金的企業失去了融資優勢,從而增加其退出風險。信貸市場效率提升通過增加低生產率企業的退出風險,降低高生產率企業的退出風險,使資源從低生產率企業向高生產率企業流動,提高了經濟中資源配置的效率。這進一步驗證了假說2。 表7 信貸市場效率與資源重置 注:括號內為穩健性z值;*、**、***分別表示顯著性水平為0.1、0.05、0.01;ρ為企業不可觀測異質性方差占總誤差方差的比例,對應括號內數值是它的P值;結果中“<1.001”是指大于1小于1.001,“>0.999”是指小于1大于0.999。 (二)穩健性分析 表7的回歸方程(1)、(2)并沒有考慮內生性問題,當有更高退出風險的企業更傾向于選擇信貸市場效率低的地區時,企業退出與金融市場發展便存在內生性。為此,本文使用信貸市場效率指數滯后兩年的數據作為信貸市場效率的工具變量,并通過Cragg-Donald檢驗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我們使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對基準方程(1)、(2)進行回歸,結果分別見方程(5)、(6)。從中可見,在控制內生性后,得到的結果依然近似,信貸市場效率的提高增加了低生產率企業的退出風險,隨著生產率提高,企業退出風險顯著下降。同時,本文使用信貸資金分配市場化指數作為信貸市場效率FEI的代理變量進行穩健性分析。信貸資金分配市場化指數構造方法為,先計算某省份某年分配給非國有企業的信貸資金占總信貸資金的比例,再使用式(12)把這一比例編制成指數形式。信貸資金分配市場化指數來源于樊綱等(2011)編制的《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11年報告》,數據觀測期為1998—2006年。非國有企業在信貸市場普遍受到歧視的情況下,這一指數越大表明銀行在分配信貸資金時越具有市場化特征。回歸結果見方程(3)、(4),可以看出:信貸資金分配市場化指數FEI提高1單位,企業總體退出風險下降3.9%,可能的原因是隨著信貸資金分配的市場化,大量私營企業的融資環境得到改善,從而降低了私營企業的退出風險;信貸資金分配市場化同樣提高了低生產率企業的退出風險,隨著生產率提高,企業的退出風險會顯著下降,我們得到與基準方程(1)、(2)類似的結果。綜上,在控制內生性以及使用不同的信貸市場效率指標后,均得出一致的結果,這表明研究結論是穩健的。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理論分析指出,融資約束通過兩個渠道影響企業的退出風險:一是通過流動性約束直接迫使企業退出市場;二是企業使用外部資金需要支付融資成本,這需要企業有更高的生產率以產生利潤來彌補這部分成本,從而提高企業退出市場的臨界生產率,增加企業的退出風險。進一步,使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對理論假說進行檢驗,發現企業的生產率提高會降低企業的退出風險;融資約束會增加企業的退出風險,這種影響在國有企業中較大,在出口企業中相對較小;并且隨著企業融資約束程度的增加,企業的退出風險會加速遞增。實證分析還表明,信貸市場效率提高會增加低生產率企業的退出風險,但隨著企業生產率的提高,企業的退出風險將顯著下降,因此信貸市場效率提高通過促使資源從低效率企業向高效率企業流動,顯著提高經濟中的資源配置效率。 基于以上結論,本文認為,應加速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鼓勵股份制商業銀行發展和積極引進外資銀行,通過增加銀行業的競爭來提升信貸市場的配置效率,為企業提供一個公平和有效的融資平臺,提高企業融資的便利性和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使高效率的企業能順利獲取發展所需的資金,從而在競爭中迫使低效率企業退出市場。這將有助于進一步優化資源配置效率。 參考文獻: 丁忠明,張琛. 2011. 基于DEA方法下商業銀行效率的實證研究[J]. 管理世界(3):172-173. 樊綱,王小魯,朱恒鵬. 2011. 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11年報告[M].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簡澤,干春暉,余典范. 2013. 銀行部門的市場化、信貸配置與工業重構[J]. 經濟研究(5):112-127. 李平,簡澤,江飛濤. 2012. 進入退出、競爭與中國工業部門的生產率:開放競爭作為一個效率增進過程[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9):3-21. 李志遠,余淼杰. 2013. 生產率、信貸約束與企業出口:基于中國企業層面的分析[J]. 經濟研究(6):85-99. 馬光榮,李力行. 2014. 金融契約效率、企業退出與資源誤置[J]. 世界經濟(10):77-101. 毛其淋,盛斌. 2013a. 貿易自由化、企業異質性與出口動態:來自中國微觀企業數據的證據[J]. 管理世界(3):48-67. 毛其淋,盛斌. 2013b. 中國制造業企業的進入退出與生產率動態演化[J]. 經濟研究(4):16-29. 王兵,朱寧. 2011. 不良貸款約束下的中國上市商業銀行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研究:基于SBM方向性距離函數的實證分析[J]. 金融研究(1):110-130. 余淼杰. 2010. 中國的貿易自由化與制造業企業生產率[J]. 經濟研究(12):97-110. 周逢民,張會元,周海,等. 2010. 基于兩階段關聯DEA模型的我國商業銀行效率評價[J]. 金融研究(11):169-179. AGARWAL R, AUDRETSCH D B. 2001. Does entry size matter? The impact of the life cycle and technology on firm survival [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49(1):21-42. ARELLANO C, BAI Y, ZHANG J. 2012 .Firm dynamic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9(6):533-549. BOYREAU-DEBRAY G, WEI S J. 2005. Pitfalls of a state-dominated financial system: the case of China [R]. NBER Working Papers, No.11214. BRANDT L, BIESEBROECK J V, ZHANG Y. 2012.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7(2):339-351. BUERA F J, KABOSKI J, SHIN Y. 2011. Finance and development:a tale of two sector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5):1964-2002. CLAESSENS S, TZIOUMIS K. 2006. Measuring firms′ access to finance [R]. World Bank. DISNEY R, HASKEL J, HEDEN Y. 2003. Entry,exit and establishmet survival in UK manufacturing [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51(1):91-112. DOLLAR D, WEI S J. 2007. Das (Wasted) kapital: firm ownership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in China [R]. NBER Working Papers, No.13103. ESLAVA M, HALTIWNGER J, KUGLER A, et al. 2013. Trade and market selection:evidence from manufacturing plants in Colombia [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6(1):135-158. ESTEVE-PéREZ S, REQUENA-SILVENTE F, PALLARDO-LOPEZ V. 2013. The duration of firm-destination export relationships: evidence from Spain, 1997—2006 [J]. Economic lnquiry, 51(1):159-180. FALCK O. 2007. Survival chances of new businesses: do regional conditions matter [J]. Applied Economics, 39(16):2039-2048. FEENSTRA R, LI Z, YU M. 2011. Exports and credit constraints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R]. NBER Working Papers, No.16940. HARRISON A E, MCMILLAN M S. 2003. Does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ffect domestic credit constraint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1(1):73-100. HéRICOURT J, PONCET S. 2009. FDI and credit constraints:firm level evidence in China [J]. Economic Systems, 33(1):1-21. HOPENHAYN H A. 1992. Entry, exit, and firm dynamics in long run equilibrium [J]. Econometrica, 60(5):1127-1150. HUANG Y P. 2010. China′s great ascendancy and structural risks:consequences of asymmetric market liberalization [J].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24(1):65-85. JENKINS S P. 1995. Easy estimation methods for discrete-time duration models [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7(1):129-136. JENKINS S P. 2005. Survival analysis [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University of Essex,Colchester,UK. LEE Y, MUKOYAMA T. 2015. Entry, exit, and plant-level dynamics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77:20-27. MELITZ M.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J]. Econometrica, 71(6):1695-1725. MIDRIGAN V, XU D Y. 2014. Finance and mis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plant-level dat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2):422-458. MOLL B. 2014. Productivity losses from financial frictions: can self-financing undo capital misalloc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10):3186-3221. OLLEY S, PAKES A. 1996. The dynam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ndustry [J]. Econometrica, 64(6):1263-1297. RIEDEL J, JING J, CAO J. 2007. Overview of economic reforms and outcomes [M]// How China grows: investment, finance, and reform. [S 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ONG Z H, STORESLETTEN K, ZILIBOTTI F. 2011. Growing like Chin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1):196-233. WHITED T. 1992.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J]. Journal of Finance, 47(4):1425-1460. YANG Q G, TEMPLE P. 2012. Reform and competitive selection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firm exits [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3(3):286-299. (責任編輯張建軍) Credit Constraints, Exit and Resources Misallocation LI RiRong (College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Research Center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of Zhejiang Province,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5) Abstract:By building a theoretical model, the paper argues credit constraints increases the risk of exit in two ways. One is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d the other is financing cost which will enhance the critical productivity of exit, and thus increasing the risk of exit. Improvement of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market will reduce financing cost, thereby, force low productivity firms to exi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s provided with Chinese industrial firm-level data.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Credit constraints really increase the risk of exit; (2) The risk of exit increases accelerately with the enhancing of credit constraints; (3) Increasing of financial market efficiency enhances the exit hazard of low productivity enterprises. However, with productivity increasing, the exit risk declines significantly. So to enhance financial market efficiency will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Keywords:credit constraints; productivity; exit; resources misallocation 收稿日期:2015-10-25 作者簡介:黎日榮(1979--),男,廣東湛江人,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浙江樹人大學浙江省現代服務業研究中心講師。 基金項目:本文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異質性出口企業對宏觀產出波動的影響研究”(71273116)資助。 中圖分類號:F2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6260(2016)03-0126-12 * 感謝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彭國華教授提供的修改意見,當然文責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