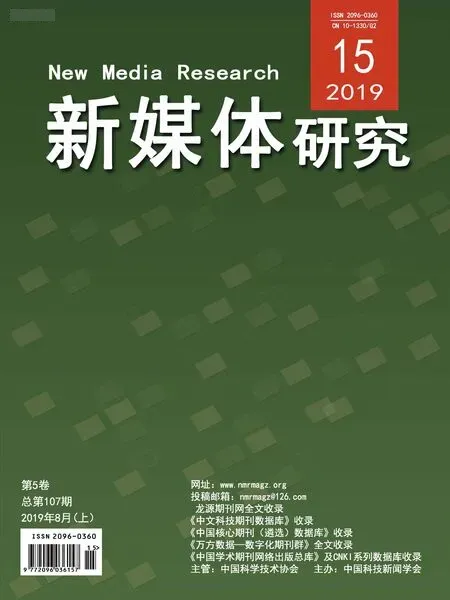基于傳播學視角思考微信社交平臺的紅包狂歡
蔣慧珺,高 雪渤海大學文學院新聞系,遼寧錦州 121000
基于傳播學視角思考微信社交平臺的紅包狂歡
蔣慧珺,高雪
渤海大學文學院新聞系,遼寧錦州121000
互聯網時代,移動媒體的發展為網民提供了日漸廣泛的社交平臺。得益于最大社交平臺之一的微信傳播的獨特優勢,微信紅包以其驚人的傳播速度與廣泛的影響力在網民的日常生活中掀起一場爭搶紅包的狂歡活動。文章從傳者、受者、微信平臺自身三個角度探討網民使用微信紅包的動機,借此分析這一狂歡背后所引發的正、負效應。
微信紅包;人際關系;正負效應
微信紅包自2014年1月27日由騰訊公司推出以來,以驚人的傳播速度從微信平臺的附屬應用逐漸轉變為吸引用戶黏性的主打功能。無論是春節聯歡晚會的爭搶活動還是平日里基于朋友圈內的娛樂消閑,微信以其強大的滲透力和影響力吸附了大量用戶。2016年2月13日,微信公布了猴年春節期間(除夕到初五)的紅包整體數據,微信紅包春節總收發次數達321億次。總計有5.16億人采用收發微信紅包的方式參與春節狂歡。相較于2015年春節6天32.7億次的收發數量增長了近10倍[1]。微信紅包基于微信5.2版本運行,背后是騰訊財付通運營的名為“新年紅包”公眾號,可以實現收發紅包、瀏覽收發記錄和提現等主要功能[2]。微信紅包采用綁定儲蓄卡的支付方式,選擇拼手氣紅包或者普通紅包中的一種,設定好總金額和紅包個數之后即可以向對方發出。微信紅包一對一、一對多的傳播模式主要基于社會人際關系網絡中的熟人關系,并日漸趨于弱關系網,這一搶一發、你來我往的狂歡背后的誘因值得探究。
1 微信紅包圈的形成動機
1.1傳者角度:紅包發起人——維系人際是主流
首先,微信作為目前最大的社交平臺之一,其主要功能依舊在于人際交往,尤其是維系熟人之間的關系鏈。由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發布的2015年中國社交應用用戶行為研究報告選擇微博、微信和陌陌三個代表性應用進行分析并得出結果:“和朋友互動,增進和朋友之間的感情”提及率為80.3%。某一微信用戶在群聊中主動發起金額不等的微信紅包供他人爭搶來加強熟人之間的溝通交流,維系彼此之間的情感。微信平臺的人際關系根據其日常互動頻率、信任度主要可以分為長期好友、階段性好友和臨時好友三種。長期好友主要由親戚、朋友和同事組成。階段性好友主要基于工作關系,由日常客戶和合作伙伴組成。臨時好友通常基于LBS服務技術支持下“附近的人”“漂流瓶”等與陌生人的社交功能。網絡時代,各大社交軟件打破了時空限制,為網民打造了便捷的社交平臺,由此網民的人際交往不再局限在基于地緣關系下的近距離真實社交,網絡中的虛擬社交異軍突起,逐漸成為主流。一個金額不等的紅包可以維系親戚、朋友、同事之間穩定的熟人關系,加強與初識客戶、伙伴之間的互動,參與臨時的短暫社交,尋求弱關系向強關系發展的機遇。
1.2受者角度:紅包群成員——娛樂消閑與自我確認
微信紅包由起初處于支付目的逐漸附上娛樂化色彩,全民哄搶春節聯歡晚會紅包更是一場網絡狂歡。隨著手機網民數量的直線上升,微信用戶可以隨時隨地參與紅包收發活動。快節奏的現代生活衍生出的各色壓力急需排解的渠道,微信紅包的出現為上班族、學生族提供了這一契機。首先,微信紅包與金錢掛鉤,無論是一分錢還是兩百元的不等金額總能激起群成員的爭搶欲望,參與爭搶活動可以有效減輕其日常生活中的壓力與負面情緒。其次,爭搶的刺激行為有助于群成員短時間逃離社會責任,忘卻日常生活中的煩惱,從而帶來精神上的愉悅。對于閑置人員而言,微信紅包活動也是無聊生活的一味添加劑,搶收行為在長期參與下逐漸形成習慣。出于慣性心理,群成員的搶收行為在潛意識支配下自發進行。另外,微信紅包群由大量熟人組成,基于自我確認的心理,個人渴望在親戚、朋友、同事之間證明自我,獲得認可。拼手氣紅包一經傳者發出,全員哄搶,最終微信會發布搶紅包手氣排行榜,其中手氣最佳者最易獲得群成員的集體關注,無論出于贊揚還是出于嫉妒對其關注度和認可度都
有一定提升。
1.3媒介工具:微信平臺打造哄搶優勢
微信產品定位社交,作為支付手段的微信紅包在締造人際關系網絡方面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微信紅包在功能涉及方面遵循簡易原則,設計便利、玩法簡單。微信用戶只需綁定一張銀行卡,接著將銀行卡內的錢塞入紅包,選擇個數、人員即可將紅包成功發出。而搶紅包者只需輕輕一點,便可參與爭搶活動。微信紅包還精確掌握了用戶的心理運用“搶”字命名這一收發紅包行為,減少了參與者的抗拒心理,并將用戶逐漸引向一場哄搶的網絡狂歡之中。這一無技術要求、職業限制等老少皆宜的娛樂活動必然贏得廣大用戶的一致認可和集體參與。此外,微信紅包的提現功能對于現實生活中由各商家發起的日趨成熟的微信支付手段相互捆綁,促使更多的微信用戶選擇功能簡易、使用便捷的微信紅包進行購物消費。
2 微信紅包爭搶狂歡背后的正、負效應
2.1微信紅包的正面效應
集團內部的獎勵措施經過春節紅包的宣傳擴散最終普及到億萬網民的工作生活當中經歷了短短2年的時間。羅杰斯提出:“……接受者認為有較多的相對優越性、兼容性、可試驗性、可觀察性以及更少復雜性的創新比其他創新更快被人們采用”[3],相較于支付寶紅包,微博紅包具有較少的不確定性,建立在熟人關系鏈之上的人際交往、群體交往與添加了競技元素的娛樂活動相聯結更容易掀起網民之間的爭搶狂歡。寄存于虛擬世界的微信紅包不再受限于紅包收發雙方的時間、距離,符合人們求新、求異,對新鮮事物的好奇心理,這一依賴互聯技術的新型收發方式一經推廣,相較于傳統紅包所需的人力、物力、時間必然以驚人的速度在網民之間蔓延,激發全民參與的熱情。
依托微信紅包的人際交往形成一定規模。高壓、快節奏的現代生活剝奪了人們現實生活中人際交往的權利,人們鮮少有機會與異地的親戚、朋友進行溝通,微信紅包的出現為此提供了一種簡單、靈活的交流方式,小型的紅包演變成了一種情感寄托,鞏固了熟人之間的感情基礎,加強了普通朋友之間的情感紐帶,間接朋友的相互加入也為社會人際關系網絡的擴大提供了契機。
微信紅包自身附帶的娛樂屬性是掀起全民狂歡的第一要素。你來我往的互動收發方式,手氣排行,財富的積累都為參與者提供了消遣和娛樂,幫助人們暫時遠離日常生活的壓力和負擔,從而帶來情緒上的釋放。由逐漸龐大的微信群聊成員組成的紅包圈形成了群體傳播機制,成員受到群體的感染不由自主參與其中,共享狂歡。
2.2微信紅包的負面效應
2.2.1娛樂消閑走向娛樂至死
微信紅包自流行以來占據了用戶的大量時間,人們不僅在茶余飯后,甚至在工作、學習忙碌的同時爭分奪秒參與紅包爭搶的狂歡。拉扎斯菲爾德和默頓認為,現代大眾傳播具有負面功能的“麻醉作用”,微信紅包的爭搶狂歡對用戶的影響再次證明這一結論。微信紅包一經推出占據了眾多群聊成員的大量時間,更多的時間、精力不再付諸于實踐當中,而是在源源不斷的通俗娛樂中逐漸失去社會行動的能力、深度思考的能力。近年來,微信紅包再出新花樣,部分不法分子利用微信紅包“聚眾賭博”。2016年1月貴州省警方破獲全省首例微信“搶紅包”新型網絡賭博案件,打掉2個微信賭博團伙,涉案金額高達數千萬元,共有來自貴州、浙江、云南、廣東等地的100余名人員參賭[4]。微信群中由擲篩子、猜拳為熱點的紅包發放行為逐漸演變為涉及眾多人員參與的巨額賭博,微信紅包背后疏解心情的消閑娛樂開始趨向于觸碰社會道德底線的娛樂至死。
2.2.2微信紅包為暗箱交易提供支付手段
由于技術的漏洞,網民媒介素養的亟待提高,互聯網空間安全問題一直以來都被政府視為重要議題多次加以討論。近期,百度云盤、115網盤、360網盤等資源泄露問題嚴重,百度云會員將百度云的資源當作買賣商品,所出售的資源涉及視頻、音頻、電子書等,類似《羋月傳》《歡樂頌》視頻資源在衛視播完前已經泄露并被網友廣泛傳播的例子很多。國家的嚴打以及百度貼吧吧務的審查、刪帖致使這類投機分子另謀出路,首先,在百度貼吧開設資源帖,留下微信號互加好友,然后,通過微信紅包付款進行資源交易。萬能的朋友圈充斥著大量進行資源交易和商品推廣的陌生人,而投機取巧、版權意識薄弱的網民在這一相對自由的虛擬環境中進行著多次傳播作業,云存儲和人際社交的結合開始為資源泄露、版權入侵、詐騙錢財等問題買單。
2.2.3擴大人際網絡走向粉碎強關系鏈
在網絡社區中,用戶基于滿足個人的精神和心理需求、交流與增進情感、擴大人際交往圈等目的參與互動。微信的社交功能模糊了現實和虛擬人際關系網絡的界限,微信紅包的普及維系了日常的人際聯系和采用新型的方式傳達的節日問候,但擴大人際交往背后的一系列問題不容小覷。微信紅包圈的成員由親戚、朋友、同事等熟人的自發和自愿加入演變為被動參與。介于人情之下的被動加入是一
種“強制性”人際關系的建構,群成員在“捆綁式”群組中已經失去了主動選擇權,“消息免打擾”“屏蔽群消息”功能的上線并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大面積的信息干擾。微信好友開始從“搶紅包”轉為利用各種緣由向他人“討紅包”。春節紅包、端午紅包、六一紅包甚至是網絡購物拼團紅包都成為部分用戶討要紅包的有利借口。微信公眾號的推出也普及了各大機構集團以網絡投票的方式進行各項評選評優活動,成員個體利用微信紅包與人情關系相結合的方式說服其他成員參與投票,網絡投票成為社會人際關系的角逐,也因此失去了公平的原則。而對被迫參與投票的其他成員而言,屢見不鮮的問卷調查、網絡投票極易引起他們的厭煩心理,建立于長期、穩定的熟人基礎上的人際關系網絡分崩離析。
3 結束語
從春節聯歡晚會的附屬福利到日常生活的趣味調劑,微信紅包歷經2年時間在網絡空間掀起了全民狂歡。在互聯網提供技術支持、微信社交軟件提供互動平臺的條件下,微信用戶出于交流溝通、消遣娛樂、逃避心理、自我確認等心理參與紅包爭搶活動,這場網絡狂歡活躍了人際交往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效應。滔滔不絕的表層娛樂剝奪了廣大用戶參與社會實踐、仔細思考的機會,惡性賭博事件此起彼伏。資源泄露、版權入侵問題日趨嚴重,微信紅包在其中難逃其責。人情關系網絡下“強制性”問卷填寫、網絡投票與微信紅包相捆綁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長期建立的穩定的熟人關系網絡。微信紅包連接支付手段的一系列便捷設置忽視了網絡安全的重要性,從長遠考慮,微信紅包在保護個人信息、完善功能設置、凈化網絡環境方面均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1]張長樂.微信社區化網絡人際傳播的建構[D].合肥:安徽大學,2013.
[2]顏萌萌.淺談社交媒體傳播功能化傾向[J].新聞研究導刊,2015(10):5-6.
[3]馮娟.基于網絡社會關系結構的傳播策略研究——從“微信紅包”談起[J].東南傳播,2014(4):80-82.
G2
A
2096-0360(2016)15-0015-02
蔣慧珺,研究生在讀,新聞學專業。
高雪,研究生在讀,傳播學專業。